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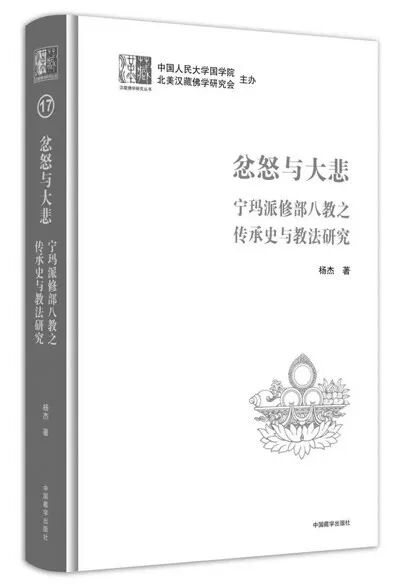
《忿怒与大悲——宁玛派修部八教之传承史与教法研究》,杨杰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即出
千呼万唤始出来,杨杰博士的大作《忿怒与大悲——宁玛派修部八教之传承史与教法研究》终于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可喜可贺,可赞可叹!虽然它有点姗姗来迟,但凡属名山之作,皆值得我们耐心等待。杨杰这部著作的基础是他十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其实,它在当时或就已经达到了可以出版的学术水准。或是出于对学术和教法的双重敬畏,或是出于对职业和人生之理想境界的执着和不懈的追求,他硬是将之束之高阁,貌似置之不问,实则一头潜入法海深处,凝然安住,细细打磨。十余年间,悬梁刺股不足以譬喻其意志之坚定,手不释卷不足以比拟其学业之精进,面壁十年图破壁,于今所求所愿,悉皆圆满,所修所习,皆得自在!这部《忿怒与大悲》虽非杨杰学术之全部,却足够典型地显现了他这些年来所习之道果和所得之成就,它的出版是他研究藏传佛教之学术生涯的第一座里程碑。十年磨一剑,出鞘露锋芒,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于博士毕业之后这十余年间,杨杰一如既往地潜心于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教法与实践,专注于翻译、注解宁玛派等各派上师们的经典著作,以历代“摩诃啰拶咓”(大译师)为楷模,译笔不辍,至今译注的藏文佛教经典著作已逾百余万字。他对宁玛派的历史、教法和宗教实践都有极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无疑是当今世界宁玛派研究之顶级青年学者。他几乎以一己之力,编纂了一部百余万字的巨著——《大圆满与如来藏——宁玛派人物、教法和历史研究》,汇集国际宁玛派研究之精粹于一册,为宁玛派之历史和教法的研究、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杨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十分热心于学术授受,他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这一特殊的学术平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来自北京各大高校和学术、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爱好藏语文与藏传佛教的学生们,开设了许多程度不同、题材各异的藏文佛教文献阅读和研究课程,倾注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培养了一批批有志于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的青年学术人才。
当然,杨杰未忘初心,对宁玛派修部八教的研究始终予以最深切的关心。十余年间,他不断扩充乃至穷尽对相关藏文资料之搜集整理,力求全面把握修部八教传承的历史,把修部八教的教法和修习放置于整个宁玛派,乃至整个印藏佛学的学修体系和历史语境之中,作细致入微的考察和研究,并及时吸收国际学界的最新成果,绝对不落人后,与时俱进,保证自己的研究与世界学术之最新动向同步前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文字表述简单明了,如行云流水,起承转合皆恰到好处,几臻完美;而他的义理阐发则甚深广大,智慧方便双运,遂令学术和宗教圆融无碍,相得益彰。无疑,《忿怒与大悲》是近年所见藏传佛教研究作品中一部难得的上乘之作,我有幸先睹为快,不胜欣喜,故于此略赘数言,以作庄严庆赞!
藏传佛教之“旧译密咒”,或曰宁玛派,与“新译密咒”形成对照,二者乃藏传佛教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也是藏传佛教研究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国际学界对宁玛派的研究开始较早,也已经有了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宁玛派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于已在西方世界流传甚广的“大圆满法”的研究,和对被认为是宁玛派祖师之莲花生大士的研究之上。成果最突出的是利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展开的有关“大圆满法”、莲花生崇拜,以及早期摩诃瑜伽流传的历史和它与中土禅宗之关系的研究,如杰出的藏族学者卡尔梅·桑木丹教授的名著《大圆满——藏传佛教的一个哲学与禅修教法》(The Great Perfection: A Philosophical and Meditative Teaching in Tibetan Buddhism)等。但是,对于藏传佛教后弘期正式开始之后,宁玛派传统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学界至今缺乏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品。而宁玛派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显然接受和吸纳了很多西藏本土及汉地传统的宗教元素和实践内容,凸显出藏传佛教之本土化的典型特征。是故,对旧译密咒之文本和教法传统之形成与发展过程连同其修习实践展开深入的研究,同时把它们与新译密咒的文本和实践作细致的比较分析,无疑将揭示藏传佛教有别于印度佛教的、自主创新的本土化特质,由此有力推动汉藏佛教比较研究及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的进步。《忿怒与大悲》正是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忿怒与大悲》以藏传佛教宁玛派摩诃瑜伽之修部的核心内容——修部八教(sgrub sde bka’brgyad)为研究对象,作者首先通过全面梳理与其相关的藏文佛教历史文献,完整地反映宁玛派所传修部八教教法之起源与传承史,并通过对其中重要的叙事材料的解读,阐明修部八教对以莲花生为核心的持明崇拜构建所发挥的根本性与决定性作用;其次,作者结合宁玛派传统中关于修部八教的权威释论,对其修习所蕴含的哲学义理加以系统阐发,其中也包括对这一摩诃瑜伽修习系统所体现的阿底瑜伽大圆满见所作的分析。通过作者对修部八教之修习系统的深入考察,它无疑可以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英国学者Robert Mayer和Cathy Cantwell夫妇等人对敦煌早期摩诃瑜伽文书的研究成果形成衔接与互补,由此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对宁玛派摩诃瑜伽密教传统的学术研究。与此同时,由于以忿怒尊修习为核心的修部八教正是集中体现影响了整个藏传佛教的莲花生崇拜、摩诃瑜伽颇具争议之诛灭法(sgrol ba)的载体,也是佛教传统在西藏吸收、转化本土宗教元素的典型,因此,作者针对修部八教展开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新译密咒与旧译密咒的争论以及藏传佛教的本土化等重要问题。
笔者对宁玛派的研究涉及不深,早年曾受谈锡永上师(1935—2024)鼓励,翻译过宁玛派摩诃瑜伽续部之根本续《秘密藏续》及其最重要的释论之一、米庞嘉措(Mi pham rgya mtsho, 1846-1912)所造之《光明藏》,与宁玛派和宁玛派研究结下了很深的缘分。今天,当我细读杨杰博士这部《忿怒与大悲》时,深知他对宁玛派的研究成就已远远超越了我自己对宁玛派之历史和教法的粗浅认知,但我乐见其成,私意更愿将这本优秀的学术著作视为当年我与宁玛派所结之善缘相续不断、绵延增上而结出的一个希有硕果。在此,我郑重地将它推荐给关心藏传佛教的学界和教界的广大读者朋友们。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5年9月17日第19版)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京(2022)000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