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吕红亮,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
【摘要】在全球史前考古学中,青藏高原无疑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单元,“青藏高原史前考古”也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近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取得惊人进展。文章依据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对拓殖青藏高原、续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青藏高原东部的粟作猎人、早期金属时代的定居点和墓葬等重大问题做了简要评述,并提出:人类进入青藏高原的时间不晚于距今16万年前,而且可能通过不止一条路线;至少从距今10000—8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青藏高原就被狩猎采集者长期占据;从距今3000年前开始,随着大麦和牦牛的驯化,人口流动性逐渐增加,牧业大规模扩展到高原边缘,青藏高原出现了长距离贸易网络、巨型定居点和社会分层。
【关键词】新时代;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狩猎采集;金属时代
一、前言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由于高海拔、低氧气和低生物产量,传统上被认为是人类生存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之一。人类何时、从何处进入青藏高原并长期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进而在7世纪左右发展出在欧亚大陆具有深远政治、军事和宗教文化影响的地方政权,仍然是世界考古学中理解最不充分的问题之一。由于考古研究起步较晚和环境给田野工作带来的挑战,青藏高原地区的考古记录仍然非常稀少。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显著进步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参与到青藏高原地区的田野考古中。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力量日益壮大,区外诸多考古研究机构也积极参与其中,田野覆盖面和研究深度显著提升,许多激动人心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重要研究成果也频繁见于国际刊物,为我们理解青藏高原早期文明历程提供了诸多新见解。尽管已有若干中外学者就近期青藏高原史前考古领域提供了综述性回顾,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视角偏差。基于此,本文将对新时代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研究的进展作最新回顾。
二、拓殖青藏高原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对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兴起,学者们注意到了青藏高原上早期人类活动的线索。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西藏自治区就记录了200多个石器地点,其中最高海拔达到5200米。然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地表采集,石器组合年代一直存在争议。在过去的十年中,考古学家在青藏高原进行了更广泛的实地调查,发掘并确认了一些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而提供了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第一批证据。
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是距今16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将高原上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到了中更新世,也提示出丹尼索瓦人可能是最早出现在青藏高原的人类。尽管化石已经失去了其考古背景,但研究人员已证实,这块化石来自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3280米的甘加盆地的白石崖洞。在此处的发掘工作还揭示出,该遗址牵涉多个古代人类占据时期。研究人员对化石中的碳酸盐结核进行了光释光(OSL)测年,结果约为16万年。根据化石的形态和从臼齿中提取的古蛋白质鉴定,这些化石被归属为丹尼索瓦人。随后的沉积物DNA分析也证实了丹尼索瓦人的归属正确。尽管从沉积物中提取的DNA的地层年龄(4.5万年)与化石本身的地层年龄(16万年)不同,但这项研究表明,丹尼索瓦人至少在16万—4.5万年前在白石崖洞活动,这是对丹尼索瓦人地理范围的一个重大更新。然而,由于对牙齿属性的分类存在争议,以及该遗址的人工制品尚未公布,因此无法推测该遗址在人类占领的区域系统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这些人群可能主要在周围的低地地区活动,他们可能只在高海拔地区短暂停留。
另一个重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为尼阿底遗址。2013—2018年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发掘。该遗址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色林错湖盆地,海拔高达4600米,自然环境条件恶劣,气候干燥寒冷,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该遗址揭露出了3个地层,深度近1.7米。根据石器组合、地层堆积和年代学数据,发掘者认为第3层是最早和最主要的原生堆积,而第1和第2层是第3层被扰动的结果。结合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万—3万年。3个地层中总共出土3683件石器,其中只有336件石器来自第3层,占总数不到10%。所有的石器都是用遗址附近山坡上暴露的黑板岩制作的。对一些考古学家而言,这看起来比白石崖的考古证据更令人信服。尼阿底遗址石器工业中最受人瞩目的是石叶技术,这与青藏高原上常见的细石叶技术明显不同。研究人员认为,尼阿底石叶技术与高原东北侧的水洞沟、阿尔泰山的喀拉博姆(Kara Bom)等遗址发现的石叶工业相似。然而,尼阿底遗址位于青藏高原腹地,与上述遗址相距甚远,且被高原北部的山脉和沙漠隔开,很难考虑它们之间的长距离迁移。此外,尼阿底遗址的石叶工业主要是采用棱柱形石叶技术,台面的预制非常有限,与典型的IUP工业组合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其技术来源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
三、续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
现有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在末次冰期最盛期(LGM,27—19 ka BP)之后,特别是从大约距今14600年前(江西沟1号遗址)到距今3000年前(加日塘遗址),细石叶技术从中国北部传播到几乎整个青藏高原。以卡若遗址为基准,我们根据生存经济的情况,大致将细石叶技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在早期,石器组合以细石叶技术为主,同时还有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某些遗址显示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使用,但对植物的使用证据有限,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续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
目前已有十余个遗址(如151号遗址、黑马河1号、江西沟1号和江西沟93—13号),经过发掘并确认为原地埋藏。利用各种绝对测年技术,多个包含细石叶地点的主要占据期被确定为距今15000—13000年,这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上最早的细石叶器技术记录。高原东部的其他遗址可以追溯到全新世早期到中期,大部分集中在距今8000—7000年左右,如拉乙亥和参雄嘎朔等。有学者将上述遗址中发现的灶、石器和动物骨骼等遗迹遗物解释为不同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模式的证据,并研究了该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占据系统和区域间的相互作用,认为此时期的狩猎采集者的土地利用模式显示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在青海湖周围的黑马河1号(13440—12410 cal BP)、江西沟1号(14920—14200 cal BP)和江西沟93—13号(15058—13975 cal BP)等遗址,少量的灶坑、动物骨骼和石器意味着这些遗址是临时狩猎营地。151号遗址(15400—13100 cal BP)有大量的动物骨骼,表明该遗址可能被用于加工动物。黑马河3号遗址(8540—8369 cal BP)一直是人们短暂停留的小营地,而共和盆地的拉乙亥遗址(6745±85 BP)可能是一个大型的大本营;通天河流域的参雄尕朔遗址(8171—7160 cal BP)被解释为一个石器制造遗址,其主要目的是生产细石叶;较为特殊的是江西沟2号遗址(9100—5950 cal BP),包括细石叶、动物骨骼和陶器,该遗址的上层可能与全新世中期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扩张有关。
旅行成本模型、黑曜石示踪和遗址位置的民族考古学模拟表明,狩猎采集者在低地和高原之间可能发生过长距离的季节性迁移。这些地点可能是旧石器时代觅食系统的多个站点,为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的拓殖提供了基础。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高原和低地相连,横断山脉地区点缀着河谷,低地河谷的生物生产力、野生动物多样性和水资源相对丰富,为青藏高原中部和北部的高海拔地区提供了通道,有助于全新世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在高原和低地平原之间形成独特的占据系统。
然而,在高原西部地区,西北部的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以及南部的喜马拉雅山阻碍了高原人向周围低海拔地区的自由流动。该地区的地形以极高的山峰和平坦的高山荒漠草原为主。自1992年进行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以来,该地区已经发现了20多处石器遗址。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狮泉河以北的阿里高原西北部的沙漠和象泉河流域上游南部的札达盆地。但是这些区域只有地表采集,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关于该地区人类活动的确切年龄和模式仍不清楚。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家对青藏高原西部石器遗址的重新审视,在夏达错、曲松果、且热、梅龙达普、丁仲胡珠孜等地确认了史前人类活动的原始堆积。碳14测年证实这些遗址的年代集中在距今11000—8000年,为探索这一时期高原人类活动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新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夏达错遗址。
夏达错遗址位于海拔4683米的第二台阶上,最重要的占据期的年代在距今8900—8500年。这是在阿里地区首次确认的具有原始堆积的湖泊狩猎采集者遗址,也是阿里地区年代最早的考古遗址。在2020和2022年两个发掘季节,发现了近5000件石器,包含大量细石叶和动物骨骼。石器主要原料是该地区原生的灰黑色硅质岩石,还有一些外来材料,如黑曜石。其中出土的5枚穿孔石针是青藏高原最早的磨制石器的记录,也显示了在高寒环境下史前先民的御寒技术的创新。
从有限的考古发掘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狩猎采集者对高原西部地区的地貌、岩石、水和动植物等关键资源有一定的了解,可能在不同的地貌单元,如河谷、湖泊、山脉和洞穴来安排高原上的狩猎采集生计。来自几个遗址的黑曜石表明,这一时期的狩猎采集者中可能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交流系统。此外,旅行成本路径的模拟结果以及周边考古证据中缺少细石叶技术的事实表明,青藏高原西部的狩猎采集者不太可能利用后勤移动和季节性模式来开发周围的低地。这一时期高原西部的狩猎采集者可能已经在高原上形成了永久性占据高原景观的模式,在考古学中看到诸多分布于不同景观中的小型遗址,应该是在高原上永久占据的生存策略中的某些组成部分。
这些遗址所代表的续旧石器时代可能持续到大约6000年前。然而,过渡到农业的时间仍然不清楚。迄今为止,青藏高原早期农业的证据仍然较少,青藏高原东部卡若遗址的小米种植仍然是考古记录中最早的证据,时间不超过距今4800年。中美学者在江西沟2号遗址发现的陶器残片,年代约为距今6500年,被认为是青藏高原考古记录中最早的陶器。可以初步认为,随着青藏高原周围低地的早期农业定居点在6000—5000年前左右的出现和扩大,青藏高原周围低地的狩猎采集者可能已经接触到农业群体的食物生产技术,如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动物。在广阔而多样的生态环境中,随着青藏高原进入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和游牧者开始密集交往。
四、青藏高原东部的粟作猎人
青藏高原上明确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大多位于高原东部的甘青地区和川西北高原。其中,大渡河上游的刘家寨、哈休遗址和共和盆地的尕玛台、宗日遗址的海拔在2800—3000米左右,已属中高海拔区域。这些遗址中既有马家窑风格的彩陶,也形成了本地风格的陶器,时代上都与马家窑文化共存,多数都出土黄河流域常见的粟黍;但在生业模式上,这些高海拔地区的遗址中狩猎—采集经济发挥了较大作用,与低海拔地区的同时期仰韶文化晚期明显不同。
高海拔地区(3000米以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少。目前,卡若遗址和昌都小恩达遗址是青藏高原3000米以上地区确认的年代最早的两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卡若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保存完好,文化内涵丰富,是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卡若遗址还被认为是青藏高原上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遗址,对研究人类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卡若遗址位于澜沧江西岸的一个台地上,距昌都市区以南约12公里。同一时期的另一个小恩达遗址位于澜沧江东岸,海拔3225米。卡若遗址已发掘3次,总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发现了半山地穴式房址、石建筑、灰坑、炉址、道路等各种遗迹,出土文物十分丰富。1985年,前两次发掘的成果以专题报告发表。2002年和201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和四川大学考古系再次对卡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对遗址中挖掘出的粟类和麦类谷物,进行了AMS放射性碳测年,并将遗址的年代重新定为距今4800—2800年。遗址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年代分别为距今4800—4500年和距今4500—4000年,此后遗址经历了大约500年的空白期,第三阶段的年代大约为3500年前。
最新的考古植物学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800年,卡若就可能建立了小米农业,可能还大量食用了藜科植物。距今3500年左右,在卡若出现少量小麦,标志着麦作农业的传入。然而,对于粟黍是在当地种植还是交易存在争议。基于生态位模型,D’Alpoim Guedes认为,即使在温暖的气候最佳时期,卡若遗址也不可能种植黍,这些谷物可能是通过与低海拔地区的农民交换而来。高海拔是早期种植小米的农民向该地区扩张的一个障碍,狩猎采集者可能保持了竞争优势。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指出在卡若遗址发现与小米种植有关的杂草,以及与马家窑文化南迁有关的几乎所有高海拔遗址都有小米存在等证据,提出了卡若遗址存在种植小米的可能性。另小恩达遗址的动物考古学资料表明,这一时期猎人的猎物主要是小型偶蹄类动物,如麝鹿,且多是成年个体。这些证据表明该遗址存在多资源经济,包括农业、狩猎、捕鱼和采集的生存策略,与上述东北高原和四川西北部的同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生存模式相似。
考古学家认为,卡若的物质文化与黄河中上游、横断山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别是马家窑和宗日文化密切相关。然而,这些风格上的相似之处需要进一步论证。同时,许多学者认为,卡若与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若干相似之处。例如,在克什米尔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某些元素,如房屋结构、陶器装饰和穿孔石刀,不属于印度河文化传统,而可能与青藏高原甚至中国的黄河流域有关。这可以解释为随着新石器时代食物全球化网络的建立,青藏高原东部和西部之间可能出现了物质和技术的互动。
总之,与其他时期相比,我们目前对高原上新石器时代化的进程了解极为有限。目前可以解释的一个模式是,大约在距今6000—5000年前,随着早期农业定居点在青藏高原周围的低地地区出现和扩展,高原周边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可能接触到了农业群体的食物生产技术,如栽培的作物和驯养的动物,促使他们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河谷地区降低了流动性。然而,由于高原的生态多样性,在更高的高海拔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存面貌还不清楚,最近在玛布错和梅龙达普的发掘可能表明高原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面貌的复杂的镶嵌特征。
五、早期金属时代的定居点和墓葬
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学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早期金属时代”,用来指代出现青铜器和铁器的时代,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世纪。目前看来,在青藏高原西部,新发掘的格布赛鲁墓地发现了可追溯到距今3600年前的青铜器;此外,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海拔3800米的宴尔龙墓地也发现了与朱开沟遗址相似的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500年。这两个遗址分别位于高原的东西侧,充分表明至少在3600年前,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先民就开始使用青铜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大麦首次被引入青藏高原的时间。至于早期铁器,在高原的多处墓葬中都有发现,目前而言,青藏高原西部最早出现铁器且年代较为确定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前500年。虽然目前我们似乎可以将“早期金属时代”分为青铜时代(3600BP—2500BP)和早期铁器时代(2500BP—公元7世纪),但由于考古材料的区域性不平衡,我们目前仍然建议使用“早期金属时代”的旧称。
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已经系统发掘的遗址大多位于山前河谷冲积扇。它们主要包括曲贡(3400BP—3000BP)、昌果沟(3400BP—3000BP)和邦嘎(3000BP—2200BP)。这3个遗址相距不远,从出土的物质遗存来看,它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该地区公元前两千纪后半期最独特的物质标志是精心制作和带有复杂装饰的磨光陶器,主要以早期曲贡和昌果沟遗址为代表。然而,正如最近发掘的邦嘎遗址所见证,该地区的物质文化在公元前1000年早期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在器物上的指征就是细石器、磨制石器和磨光陶器的逐渐退场。
这一物质变化也反映在植物组合的模式上。来自曲贡和昌果沟遗址的古植物学证据表明,从距今3400年前到距今3000年前,该地区驯化的作物包括从黄河流域驯化的粟黍和从近东驯化的大麦、小麦和豌豆,在一些遗址还包括荞麦。然而,在大约距今3000年之后,以邦嘎遗址为代表,小米似乎逐渐从这个地区的人类饮食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大麦为主的作物结构。在邦嘎发现的巨型磨盘表明,大麦可能被磨成了粉食用,这不禁让人想到今天在青藏高原最流行的独特的麦作的粉食传统——糌粑(炒过的大麦磨粉与水或酥油茶混合)。这种粉食传统很可能是与西南亚的农作物和驯化的动物一起传入青藏高原的。根据对曲贡和邦嘎遗址动物考古的研究,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主要驯养动物是绵羊和山羊,可能还有黄牛和牦牛以及他们的杂交种犏牛。在河谷遗址附近的高山牧场上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牧业活动痕迹。这些转变都在提示,距今3000年之后,高原先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农牧业的成分空前增加,人员的流动性也可以说前所未有。也大体从这一时期开始,青藏高原明显与中亚山区的文化交流网络的关系愈发密切。比如公元前1000年,在该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中亚风格的带柄铜镜和带流陶器。虽然中部区域经过系统发掘的遗址点依然很少,许多墓葬材料也没有被公布,但可以预见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肯定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由于考古工作的地理不平衡,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大多集中在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尤其以象泉河流域的早期墓葬最为集中,如皮央东嘎墓地、格布赛鲁、桑达隆果、故如甲木、曲踏。出土墓葬总数估计近200座,这些墓葬中最常见的是带墓道的竖穴洞室墓,这也是西部地区的主要墓葬类型。此外,还有地表可见的石堆墓、竖穴石室墓、石棺墓等。从时间上看,以格布赛鲁为代表的石棺墓葬是最早的,其他墓葬类型大致上是并存的。此外,近期在靠近中尼边境的仲巴县海拔高达5000米顶琼洞穴发现了一个大型洞穴丛葬墓(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延续年代近600年,人骨和动物骨骼数量巨大,是这一区域独特的葬俗。遗憾的是,属于这一时段的聚落遗址较少被发现。只在皮央东嘎遗址群中发掘了3个小型建筑聚落,年代与墓葬同时,揭示出这些墓葬的居民就生活在附近;而在象泉河上游的山顶上,有一个大规模的防御性遗址——卡尔东,其年代也与其山脚下的故如甲木墓地有着高度重合。这说明当时既存在高等级墓葬,也存在军事性的大型中心聚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至少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600年期间,青藏高原西部出现了具有更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特定人群,卡尔东遗址的大量建筑(包括祭祀建筑)就是证明,而那些高级物品的流通和丰富的随葬品是这些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在大多数墓葬中都发现了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典型陶器和数量丰富的青铜器、铁器、木器、丝绸、金面具等。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遗物几乎同时出现在从印度西北部和青藏高原西部到尼泊尔中北部一个十分广阔的喜马拉雅高山区域,如在故如甲木、曲踏和桑达隆果的墓葬中出土了大约10个金面具,在印度西北部和尼泊尔的木斯塘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面具。在青藏高原西部的竖穴洞室墓和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的洞穴墓中发掘出装饰精美的木箱棺材,可能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南缘。青藏高原西部墓葬中发现的丝绸、木制品、草篮子、珠子和茶叶来自塔里木盆地南缘或南亚的印度洋地区,表明喜马拉雅地区与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密切联系,在青藏高原西部和印度西北部的墓葬中出土了几乎相同的陶器,更有可能是陶器跟随人们的移动而移动。最近对木斯塘葬地的古DNA研究表明,这一人群的基因组来源与青藏高原中部一致,表明这一时期贸易和移民的扩大。
六、结语
在全球史前考古学中,青藏高原无疑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单元,“青藏高原考古”也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然而,青藏高原地域辽阔,环境险恶,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我们目前对考古遗存的了解并不全面,时空分布也不均衡,尚无法建立起当地的考古年代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这一领域,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学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进展。一些研究为了满足顶级出版物的故事性需求,某种程度上调高了“修辞”色彩,但这些暂时性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来检验,不能被视为定论。目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类进入青藏高原的时间不晚于距今16万年,而且可能不止一条路线。至少在全新世早期,青藏高原就被狩猎采集者长期占据。从大约距今3000年开始,随着大麦和牦牛的驯化,人口流动性逐渐增加,牧业大规模地扩展到高原的边缘,出现了长距离的贸易网络、巨型定居点和社会分层。
可以预见,未来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学将继续由中国考古学家绝对主导,国际学术界对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热情也将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扩大考古田野调查和发掘的地理覆盖面,更准确地确定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并积极推动多学科方法的整合,特别强调区域尺度的环境变化、遗址尺度的动植物资源利用的特殊性,并致力于研究高海拔适应与经济转型、文化景观利用和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3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购书请扫码进入中国藏学官方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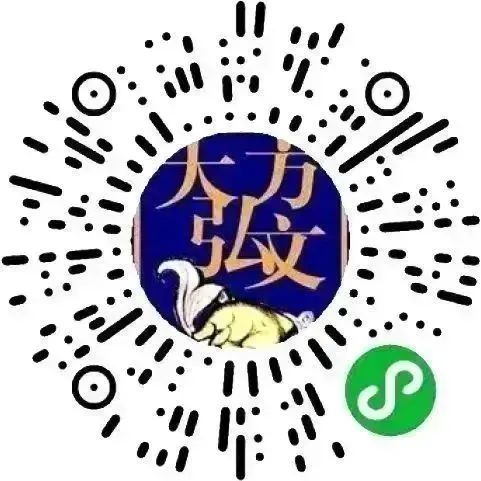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