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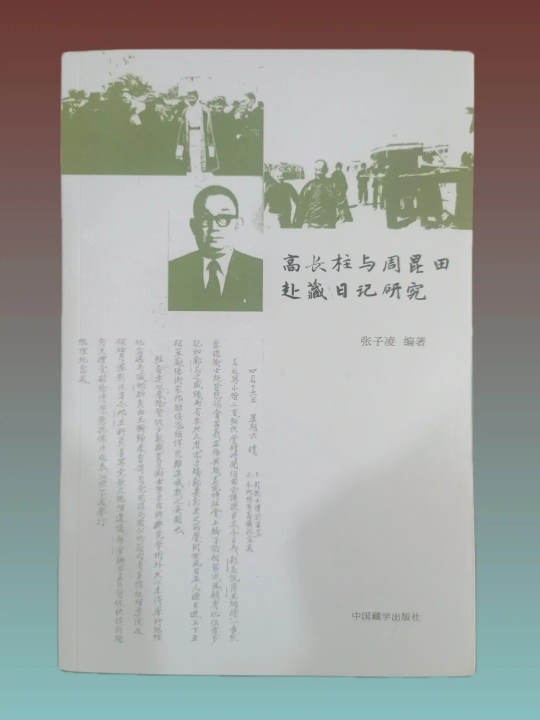
张子凌编著:《高长柱与周昆田赴藏日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23年7月
序言
关注涉藏日记价值,拓展藏学研究新思路
——喜饶尼玛
今天,我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单凭文献资料研究历史,有一定的局限。日记是历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材料,与档案文献相比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当今学界对日记研究的重视程度在加深,因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内容上,更在于其有别于其他资料的特殊性。正如余佐赞(华文出版社总编辑)先生所说:“对于普通读者,可以从这些历史名人、文化大师的日记中看到他们平凡的另一面,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是为其了解中国社会与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窗口’,是一次难得的亲近一线历史细节,获得独特历史信息与文化信息的思想之旅。”但是,我们的学者过去对此关注不够,如不少重要的涉藏日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日记通常被认为是私人书写,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是,它的特点亦较明显,可补公共叙事之不足,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近代史上,不少人因为生活在西藏或被派往西藏工作,所见所闻留下的日记堪称珍贵。同时,一些看起来与藏事关系不大的人,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也与藏事有所接触,从而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另辟蹊径。近代藏族史所涉日记等史料十分丰富,通过仔细梳理与比较,可以弥补相关研究的缺陷,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二者是相得益彰的。
近年来,各个时期的涉藏日记出版甚多,研究者也逐渐增多。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藏学研究领域已经出版了多部相关书籍和论文,一些尘封的历史被公诸于世。如藏族近代史研究中,《有泰驻藏日记》就已为不少学人关注,为研究清末西藏历史提供了较大的帮助。中国藏学出版社等也出版了多部涉藏日记,对研究20世纪的西藏具有特殊价值。仅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戴新三所撰《拉萨日记》就已有王川等多位学者研究,撰有相关论文多篇,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资助。国外学者对涉藏日记的关注也在升温。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西藏现代史:山雨欲来(1955—1957)》就用到了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的《日记》。他特别强调:“这不是夏格巴的个人‘日记’,是他作为‘哲堪孜松’秘书长的角色而记录下的政治性‘日记’。”近年,我的博士韩敬山整理注释的欧阳无畏的《藏尼游记》《达旺调查记》等受到学界关注,也是一例。但是,正如王川教授所言:“此外,还有很多重要涉藏人物的私密日记散落在民间,同样值得整理出版,以推进藏学研究。这些私人日记,少为人知,利用得很不够。”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惊喜地注意到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现就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张子凌就是其中一位研究私人日记的青年学者。自2008年硕士毕业以来,她一直从事与民国藏事档案文献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专注民国时期涉藏历史研究,先后参加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等项目,也发表过不少民国时期的涉藏档案文献的相关论文。
《高长柱与周昆田赴藏日记研究》是她在整理、校注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的两位官员高长柱、周昆田的日记和游记时所编著,并在收录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自身研究所得撰写的新作。
高长柱与周昆田同为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的官员,也同为研究边疆问题与藏学的学者。两位先生也都曾到过西藏及其他藏族聚居地区,其间留下了许多较为珍贵的记述。《高长柱与周昆田赴藏日记研究》所选取的史料,都是难得的材料。其一是高长柱作为护送九世班禅回藏行辕的参军从西宁至玉树的途中所记的日记;其二是篇幅较长的高长柱奉命赴藏拟接替蒋致余的途中日记;其三是周昆田作为陪同吴忠信见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行辕秘书,所回忆的赴藏途中与内返途中的两篇游记。他们都是彼时涉及达赖、班禅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其对亲历、亲见、亲闻事件的真实记载,是非常值得挖掘的史料。这些日记中所记录的内容涉及西藏及藏事相关重要人物、历史事件、地理环境、风物民俗等,字数虽不多,但认真加以整理注释,则非常有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张子凌在编著《高长柱与周昆田赴藏日记研究》时,对一些相关人名、地名作了细心地注释,尤为可贵的是,她克服困难,还加上了藏文。这不仅有利于读者的阅读,也解决了一些前人未予注意或未加解决的问题,使我们对民国时期的涉藏历史、地理以及人物、事件能从不同角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很有裨益的佐证。
个人日记,在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碎片,对日记所载,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就牵涉到使用者的立场、学力和功力了,当然,这并非一日之功。但我们在对学界利用日记体发表的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还存在着依靠单一日记、选题窄小、框架与思路重复等不少问题。由此,提醒我们发现与整理“新”日记、深挖日记中的丰富内涵、拓展研究视野,将私人的记录放到大时代、大事件中进行分析,是进一步深化日记研究不可或缺的途径。在这方面,张子凌的《高长柱与周昆田赴藏日记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另辟蹊径的研究方式让人颇有感触。
目前,有人认为利用日记等进行研究是“碎片化”。这种说法是很不全面准确的。正如著名学者王笛所说:“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没有零件,哪有机器?……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
对此,陈寅恪先生也有一段话讲得好。记者问到他有人诋毁考据之学为细微末节,先生如何主张?他说“细微末节不是考据之病,只要是有系统的东西就合乎科学,譬如生物学要在显微镜下面观察东西,这不是更细微吗?”他说,持这种论调的人反而是无科学头脑。
需要注意的是,日记等史料与档案文献各有优劣,既不可厚此薄彼,也不要厚彼薄此,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参照,互为印证,相得益彰。唯有广览各类史料,对照分析,认真查证,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始能写出严谨科学的学术论著。
毕竟正走在这条路上,我对后起之秀张子凌的努力,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她甘于坐冷板凳,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基础的史料整理、注释做起,实属不易。相信如此而为,必有所成。历史学没有对史料的掌握和熟悉,岂谈研究。藏学界需要有一批不计名利,不图虚名,踏踏实实的学者。
子凌诚意所托作序,虽曾推托,但因作为校友且此书亦是我研究之领域,故写下这些话,是为序。
2021年盛夏于北京
后记
——张子凌
自2008年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民国时期涉藏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十余年来,相较于学界的同龄人,实在算不上刻苦努力,但是凭着对藏学事业的一腔热爱之情,我激励自己编撰了这本,也是第一本独立完成的著作,还是有颇多感受。
在整理档案文献的过程中,我对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日记、游记、手稿等史料关注较多,因为读起来不艰涩难懂且颇有意思,由此便萌生了整理并注释这些史料的念头,同时也抱着效仿学界前辈进行研究的想法,既不耽误本职工作,也正好是学习和钻研学术的绝佳机会。经过数年来逐步的积累,终于略有收获,继而又在整理注释的基础上撰写了三篇文章,即是今天本书的雏形。
选择高长柱和周昆田两位先生的日记和游记作为研究的对象,不能不说是缘分。两位先生年龄相仿,高长柱大周昆田四岁,他们同是安徽老乡,彼时又都在同为安徽人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先生身边任职,且在边务问题尤其是西藏及藏事的研究领域都颇有成果与建树。两人在工作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相似的经历:高长柱曾奉派参加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护送九世班禅返藏,并赴藏接替蒋致余参议,虽最终未入藏,但亦经历了筹备、启动、滞留、交涉、等待之数月历程;周昆田则曾随吴忠信先生入藏见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盛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位先生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将自己的经历以日记或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在编撰本书的过程中,我也着实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在对一些地名进行注释的过程中。像民国时期的一些山脉、河流名称基本延续了清代的叫法,清代关于西藏的史地方舆著作从数量上虽说不少,但因为计里画方的传统制图与西方经纬度画法差异较大,而且无论是《卫藏图识》还是《新疆图志》《新疆山脉图志》内的山脉与河流名称均与今天的名称有较大差异,其中更是夹杂藏语、满语、蒙古语等各种音译的名称,所以,企图将这些地名等项与今一一对应,难度较大。另外由于高长柱与周昆田两位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均去台湾,为相关资料的搜寻带来了一些困难,故此书在研究上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若能对从事民国藏学研究,尤其是喜爱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学者有些许的帮助,我将不胜欣慰。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要说的话实在很多,但是,最想要说的还是感谢,从本书编撰的初衷,进而到日记的整理,论文的写作,逐条的注释,直至出版的过程中都得到了许多老师和朋友的关心与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仅凭我的个人能力,着实难以付梓。为此,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喜饶尼玛教授,不仅时常为我释疑解难,而且还不辞劳苦为本书撰写序言,并联络在泰国的吴忠信先生后人询问关于周昆田先生的资料,帮助我跨越了写作中的瓶颈。教授对吾等青年一辈学者的鼓励与教诲,令我深深感动。感谢台湾政治大学陈又新老师为本书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张永攀老师对我在编撰本书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与答疑解惑;感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张云老师对本书提出的中肯的修改意见与建议;感谢中国藏学出版社洪涛社长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最后,还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季垣垣老师,她在本书的编审过程中花费了大量心血,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书稿臻于完善。
遗憾的是,季垣垣老师已于2022年10月12日因病与世长辞,未能见到这本由她最后一次担任责编的作品。这也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意难平,在此深深缅怀敬爱的季老师。
最后想说的是,由于本书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完成,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有诸多不便之处,导致在编撰中占有资料不全,再加上本人的研究水平十分有限,书中难免存在内容缺漏、资料匮乏,以及论述不全面、注释不精准甚至错误等问题。对此深表歉意,同时也希望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2023年4月24日
购书请扫码进入中国藏学官方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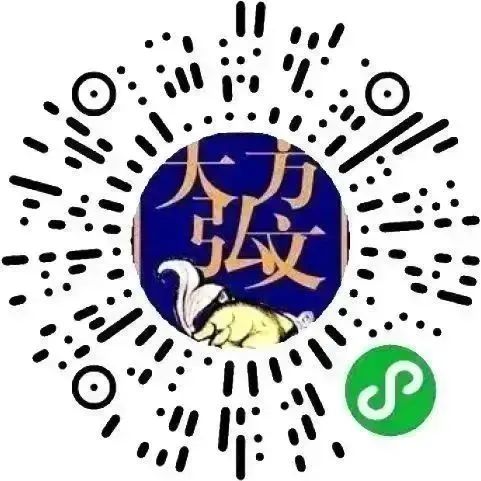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