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云,1960年6月生,陕西省周至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内容摘要】陈庆英先生是著名的藏学家,在藏族历史、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研究,以及藏文历史文献翻译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陈庆英先生的藏学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研究,既是对他去世的一种深切缅怀,也是对他丰厚研究成就的继承发扬,还会对中国藏学事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从藏族历史、藏传佛教、民族关系史等方面梳理了陈庆英先生的代表性著作,在此基础上对其治学路径方法及经验启示进行了初步总结。先生始终坚守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崇高使命,服务国家和人民,有追求、有担当,尊师重道,提携后学,为中国藏学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关键词】陈庆英;藏学研究;治学方法;研究经验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3年第2期
陈庆英先生先后在藏学研究的诸多领域辛勤耕耘,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仅就其主要研究领域和代表性成果进行考察,结合他先后接受《中国藏学》和《西藏大学学报》编辑访谈中的自述,对他的治学方法和成就进行初步的研究。
一、陈庆英先生藏族历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与代表性成果
(一)西藏通史的研究和编撰
“西藏通史”类著作的编撰既是陈庆英先生从事西藏历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也是其藏学研究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他是目前撰著和主编这类贯通性著作最多的学者。《西藏历史》(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一书,内容包括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西藏、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地方政教势力割据时期的西藏、元代西藏、明代西藏、清朝前期的西藏、清朝后期的西藏、西藏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斗争、民国时期的西藏、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自治区的建立11章,简明扼要、脉络清晰而准确地梳理了西藏历史的发展脉络,颇受读者欢迎,并被翻译为英文、法文等多国文字对外传播。他与高淑芬合编的《西藏通史》(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包括引论、西藏的地域和自然环境、考古发现和早期居民及其文化联系;吐蕃王朝时代王室渊源,吐蕃王朝的建立、发展、停滞发展、崩溃历史,以及经济、宗教和文化;割据时期西藏的政治、宗教、社会经济及文化;元朝时期西藏地区统一于蒙古汗国、萨迦政权的建立、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明朝时期西藏的帕竹政权、明朝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藏传佛教和教派斗争、西藏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交流;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民国至和平解放时期的西藏等7编。内容上比《西藏历史》(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更为丰富,资料也更加翔实。此外,他还与丹珠昂奔、喜饶尼玛、廖东凡、张晓明、周爱明合著《西藏史话》与《西藏历史图说》,通过讲故事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普及西藏历史知识。这些西藏通史类著作是集体完成的,陈庆英先生以其学术影响和贯通性广博知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几部著作从体例上来看,主要侧重古代,即使是包括当代历史,也只限于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前,还不是完备意义上的《西藏通史》。而内容丰富、体例完整、资料翔实、引领学术前沿的多卷本《西藏通史》,同样有陈庆英先生的主持和重要贡献。在前期组织调研、安排各卷负责人、联系有关专家、组织讨论大纲、确定体例和重要原则,以至对全书最后的顺利完成,他与拉巴平措两位总主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与人合作主编了其中的“宋代卷”和“元代卷”,参与全书的讨论和统稿工作。
围绕西藏通史中的一些问题,他还与人合写了有关论文加以探讨,诸如与王辅仁先生合作撰文《关于藏族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讨论藏族历史的分期;与冯智合作撰文《藏族地区行政区划简说》,梳理藏族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历史;与李少魁撰文《关于西藏通史研究的断代史思考——兼论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权同步、政治同声、经济同气”的史实特征》,探讨西藏通史研究的断代史问题。他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证了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撰写《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认为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
(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研究
陈庆英先生有关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既体现在元明清各朝历史研究的论文中,又集中体现在由多杰才旦主编、邓锐龄副主编,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一书中。该书具体由邓锐龄先生负责统稿定稿,陈庆英先生撰写了第一编的元朝(蒙古汗国)与藏族地区关系的建立、元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元代西藏地方的政权、明代西藏的政治形势、明代对藏族僧俗首领的封赐、明代在西藏所封的各王和蒙古势力重新进入青藏高原等部分。利用藏文原始资料丰富关系史的内容是其主要特色,例如利用《汉藏史集》一书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元朝在西藏置驿、括户、用兵等史实。讲到1264年忽必烈设置总制院,任命八思巴担任院使,在注释部分全文引用了颁赐给八思巴的“珍珠诏书”全文;在讲到八思巴歌颂忽必烈统一全国功业时,同样翻译了收藏在《萨迦五祖文集》中的八思巴贺表全文等。
(三)吐蕃史研究
陈庆英先生的吐蕃史研究始于其在中央民族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敦煌文书研究,《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一文就完成于这个时期。1981年,陈庆英先生等到甘青涉藏地区去实习,和同学端智嘉在敦煌县文化馆藏《般若八千颂》的经叶边上发现了一份吐蕃王朝时期的驿递文书,两人在此基础上合作写成了《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他还通过土地面积丈量探索了吐蕃的土地制度(《土地面积丈量——试析吐蕃时期的土地制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1982年第2期);通过吐蕃的君臣地位、盟会制度研究,指出了吐蕃赞普由王朝建立之前部落军事联盟的盟主,演变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宰和王朝名副其实的君主,并由此形成一套职官管理制度(《试论赞普王权与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与端智嘉合作探讨了赞普赤德松赞的生年与起名、即位与执政、扶植和发展佛教、三次厘定文字及其与唐朝的关系,考察了其生平事迹(《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翻译了藏文P.T.999号写卷并以注释方式指出吐蕃王朝后期以“天子”称呼赞普已是通行做法,敦煌发现的汉藏文《大乘无量寿经》是为赞普赤祖德赞积福而抄写,由政府出资,文书中的鼠年即为公元844年;微松生于达磨赞普遇弑之前,而非遗腹子等(《从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载《藏学研究论丛》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他的《从帐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一文认为,吐蕃王朝时期是藏族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吐蕃王朝崩溃后出现的农奴主占有农奴的封建农奴制是在吐蕃王朝的基础上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也许应该纳入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的范围内。此外,他与邹西成合作撰写了《吐蕃王朝飞马使印章考释》,与马丽华、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合作释读了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中国藏学》2010年第4期),探讨了松赞干布河源迎亲中的相关史实,指出松赞干布匆匆离开河源返回拉萨涉及王朝内部的兄弟权力之争(《关于松赞干布河源迎亲》,《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四)元朝西藏历史研究
元朝西藏历史研究是陈庆英先生用力最勤、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研究重点主要围绕若干重要人物、制度和事件等展开。包括依据藏文资料梳理了元朝在西藏所封的几位白兰王的事实(《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先后与洛桑群觉、祝启源合作撰写了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等,依照《汉藏史集》等汉藏资料探索了元朝在西藏建立驿站的史实(《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考察了元代在西藏的户籍清查(《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文集》,1996年)。他还重点研究了元代西藏地方的行政官员萨迦本钦的地位和作用(《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元史论丛》第4辑,1989年;《元代萨迦本钦辨析》,《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辨析了萨班与阔端会见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元代乌思藏萨迦政权与蒙古皇室的关系,以及1239年蒙古军进入西藏的杰拉康之战的相关史实。元朝在西藏地区建立的行政机构也是他的重要研究内容,关于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和名称等是代表性成果。关于元代在西藏实施的帝师制度,他除了与仁庆扎西合写《元朝帝师制度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之外,还独自撰有《夏鲁的元朝帝师法旨》《元朝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等。在元代西藏地方代表性人物的研究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元世祖的藏族宰相桑哥(《历史知识》1984年第4期),元代玉树藏族名僧胆巴国师(《元代玉树藏族名僧胆巴国师》,《青海方志》1989年第4期;陈庆英、周生文:《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萨迦班智达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政治活动等。《关于八思巴蒙古新字的创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西宁弘觉寺与西安小雁塔〈正统圣旨碑〉》(与仁庆扎西合写,《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是他对元代文字和碑文研究的成果。
在元代历史研究方面,陈庆英先生对八思巴的研究最用心力,成果也十分突出,主要包括《与八思巴有关的几份藏文文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元朝帝师八思巴年谱》(《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与王辅仁先生合写《八思巴评传》、《塔尔寺楹联上的八思巴字》(《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八思巴致元世祖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八思巴致元世祖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词》(《西藏研究》1987年第2期)和《忽必烈即位前的八思巴》(《思想战线》1988年第5期)等,利用翻译藏文资料和八思巴写给忽必烈皇帝的祝辞来研究相关史事,是这几篇论文的突出特点。他的专著《帝师八思巴传》是长期扎实研究八思巴生平事迹的重要成果,既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他在接受访谈时说道:“我自己下过很大功夫、花费很多时间而写成的著作是《帝师八思巴传》。八思巴是元朝的第一个帝师,他的活动对当时西藏乃至全国的政治、宗教、文化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关于他的记载,在汉文史籍中比较零散简略,《元史》中系统记载他的只有几百个字,藏文《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中有较多的记载,但是年代和前后顺序很不清楚。我是在整理这些资料时,发现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人,应该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先根据八思巴文集中他在各篇文章后面的题记的记载,先清理出他在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清理出他一生活动的轨迹,清理出他一生中两次到蒙古和汉地又两次返回西藏的年代顺序,再结合藏文史籍的记载,对八思巴一生的业绩作出比较清晰的论述。这本书在写作时没有什么科研项目,也没有出版经费,因此在篇幅上受到很大限制。不过出版以后产生了较大影响,有不少跟进的著作和论文,对元代西藏历史和萨迦派历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这无疑是中肯的说法。
(五)明朝西藏历史研究
《江孜法王的家族与白居寺的兴建》一文依据《汉藏史集》的记载,确认江孜法王的家族即夏喀哇家族的祖先,来自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一带,到元代的帕巴贝桑布时因受命镇守江孜地区,又因军功成为一支地方势力,其孙热丹贡桑帕巴受到明朝的封赏并修建了白居寺。该寺在宗教上的独特之处是各教派都能和平共存,萨迦、格鲁、布顿等都在寺内拥有若干殿堂和扎仓,只是在格鲁派掌权后,才占据了白居寺的主导地位。《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政治述略》(《西藏研究》1999年第2期)分别对明代甘青和川西两个地区设立的机构、采取的管理措施作了考察,试图探寻明朝没有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而使藏族地区从属朝廷的关系一直延续下来的原因。《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朝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对宗教的控制加强对西藏等地的影响。明朝封授的藏传佛教宗教首领中,以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宣德年间加封为大慈法王)最为重要,其次是封藏传佛教的高僧为大国师、国师及禅师等。这些做法与明太祖时开始的封藏族首领为都司卫所官员的措施是一致的,是明朝治藏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明朝依据自身的实力及对以乌思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吸取元朝廷与藏族宗教首领交往的办法而采取的重大步骤。《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考证出该书作者即是书中所提到的嘉乔贝桑(སྐྱབས་མཆོག་དཔལ་བཟང),是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初期的合作者,对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作过相当的贡献。
(六)清代西藏历史研究
《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一文认为,西藏使团为首的两位喇嘛其实是《清太宗实录》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条中的戴青绰尔济和戴青俄木布二人,而伊拉古克三是当时厄鲁特蒙古人对高级活佛的一种泛称,并非某一位活佛的专称。“咱雅”这一称号即是蒙古语“伊拉古克三”的对应词,所以咱雅班智达应当是《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北京香山昭庙乾隆御制诗碑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六世班禅主持香山昭庙开光仪式,以及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在香山昭庙会见的相关史事。《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0年4期)一文指出,清朝在两次金川之役中曾将部分投降的金川藏族迁移到北京,特别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迁来的人较多,以至朝廷专门将他们编为一个佐领,归入内务府正白旗,并指定他们在香山建筑碉楼居住,由健锐营就近约束管理,这些金川藏族人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习俗、歌舞、建筑碉楼的技艺等,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点,至今虽然已经过去200多年,但香山的藏式碉楼依然有遗存,香山藏族人的后裔中还流传着藏族歌曲,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民族文化现象。《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中国藏学》1995年第3期)指出,活佛转世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政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整饬、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管理大活佛的一项关键措施。该制度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体现了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事实,有利于维护和稳定蒙藏地区的社会局势,安定边疆,团结宗教上层人物和广大僧俗群众。《雍和宫杂论》一文认为,雍和宫改建“擦尼特扎桑”即藏文མཚན་ཉིད་གྲྭ་ཚང(法相院,显宗扎仓),“巨特巴扎桑”即རྒྱུད་པ་གྲྭ་ཚང(密宗扎仓),“曼巴扎桑”即སྨན་པ་གྲྭ་ཚང(医学扎仓),“扎宁阿扎桑”应是སྒྲ་སྙན་ངག་གྲྭ་ཚང(声明和修辞,系指五明扎仓),还指出乾隆皇帝撰写《喇嘛说》一则用于训诫子孙、威慑蒙藏佛教人士,一则具有自我辩解的作用。《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6期)详细梳理了金瓶掣签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认为它是乾隆皇帝针对活佛转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时结合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和清朝选官制度的签选办法,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一文详细梳理了固始汗进入西藏地区的历史过程,指出固始汗是率领自己的全部部众进入青藏高原的,并且是通过战争攻打下来的,既不同于忽必烈,也不同于俺答汗,他的目标是要在青藏高原长期统治下去,并且保证自己的子孙长期掌握统治权。而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索南饶丹等格鲁派上层既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也没有行政统治的经验,又面临第悉藏巴的残余势力的反抗,认为“在西藏这块土地上如果有一个领袖,时局才会安定,萨迦、噶举、宁玛等其他教派四分五裂的局面才可能有所改观”,因此五世达赖喇嘛希望固始汗留在西藏,甚至还期望固始汗成为平衡格鲁派内部各方面矛盾的一种力量。《六世班禅灵柩回藏考》(《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认为,灵柩返藏过程从制定返藏路线、所作准备等看,乾隆仍然延续了尊崇六世班禅的做法。由于是灵柩返藏,在有些地方也兼顾了人力与经济的考量。
(七)藏族部落研究
关于青海地方史和藏族部落史研究也是陈庆英先生藏族历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先后出版了《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两本书,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对除了庄园制地区以外的藏族部落地区的社会历史做了系统的论述,对藏学研究有长远的学术价值。”《中国藏族部落》在20世纪50—60年代初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收集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和参考有关藏汉文史料,进行综合分析,按现今的行政区划为横断面,对藏族部落的分布和组织系统作了比较全面的简要阐述,又将散见于唐、宋、元、明时期汉文史料中的西北藏族部落附列于后,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关于藏族部落的学术资料性专著。《藏族部落制度研究》探讨了古代藏族部落的发展变化、组织结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宗教信仰、社会文化等,最后附有近代藏族部落的分布,对于全面认识藏族部落,乃至了解青藏高原地区牧区社会文化具有参考作用。
二、陈庆英先生藏传佛教研究的主要领域与代表性成果
(一)历辈达赖喇嘛研究
对历辈达赖喇嘛生平事迹的研究,诸如《历辈达赖喇嘛事略》(《社会科学参考》1989年第21期)是一篇概要介绍。《格鲁派的兴起和一世达赖喇嘛的青少年时期》一文,依据《根敦珠巴贝桑布传》的记载,介绍了一世达赖喇嘛家族早年从康区迁居到今日喀则萨迦吉定乡赛地方,是个相对富裕的牧民家庭的背景,以及早年学经修习的经历。《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的蒙藏关系史料》(《西藏研究》1994年第4期)一文,以翻译《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的资料为依据,指出其对蒙藏关系研究的价值。基于同样方法撰写的《五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关系资料》(《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与蒙古各部》(《卫拉特研究》1992年第2、3期)等,分析了蒙古各部的态度与此事件的关系。《五世达赖喇嘛与印度文化》(《西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五世达赖喇嘛学习梵文和梵语语言学知识,热心吸收印度医学知识以及与印度莫卧儿王室往来的事迹,还详细整理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年谱。《达赖喇嘛及历史定制》是了解达赖喇嘛转世与清朝以来形成的历史定制知识,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的好读物。陈庆英先生主持的《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先将历辈达赖喇嘛的藏文传记翻译成汉文,再结合相关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历辈达赖喇嘛生平的学术专著。
(二)历辈班禅额尔德尼研究
《历辈班禅大师事略》(《思想战线》1989年第3期)一文对历辈班禅大师的事迹逐一作概括介绍,既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史料,又指出了历辈班禅大师在祖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过程中,在国家的政治、宗教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四至九世班禅大师以及他们的灵塔》(《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一文详述历辈班禅的生平事迹及肉身灵塔建造情形,丰富了人们对历代班禅相关宗教和文化知识的认识。《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塔尔寺记事碑译释》(《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翻译并介绍了塔尔寺内弥勒殿(俗称贤康)门前北侧碑文,该碑记述了九世班禅大师1935年5月至1936年4月驻锡塔尔寺时的各项活动,展现了其在驻锡内地期间与汉、蒙古等民族的佛教界人士的密切交往,对促进各民族间宗教和文化的交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十世班禅大师的故乡和家世》(《中国西藏》1997年第1期)认为十世班禅大师是萨迦法王八思巴的传人,介绍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热爱自己的民族和中华各民族、热爱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以及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族人民亲密团结所作的巨大贡献。
(三)藏传佛教高僧研究
《噶玛巴·攘迥多吉两次进京事略》一文依据汉藏文史料,对噶玛巴·攘迥多吉在1331—1334年和1336—1339年两次进京,相继为元文宗和元顺帝做法事,增强西藏地方噶玛噶举派与中央政府关系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西纳家族、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根据《安多政教史》等汉藏资料,对“ཟི་ན”这个出现在宋代文献、活动在甘肃地区的家族,如何在明代定居今西宁湟中一带,及其与元代的西纳万户、塔尔寺西纳活佛之间的关系予以厘清。《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一文认为,西藏首次派遣到沈阳去的使团很可能是由厄鲁特蒙古著名高僧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ནམ་མཁའ་རྒྱ་མཚོ,1599—1662)率领的。《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认为咱雅班智达的家乡在今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乌图美仁乡,其家庭可能是哈纳克土谢图的属民,代替固始汗之兄拜巴噶斯的儿子出家为僧。五世达赖喇嘛称咱雅班智达为琼结班智达、夏仲、热绛巴(རབ་འབྱམས་པ,亦译作兰占巴,指获得格西学位的博通经论的高僧)等,以及阿巴车臣曲杰诺门罕、阿巴诺门罕等,第悉桑结嘉措《黄琉璃》称其为琼结热绛巴·南喀嘉措。阿巴洛本是咱雅班智达在西藏学经后所担任的最高僧职。《清实录》记载的1642年抵达沈阳的西藏使团中的首席代表,可能就是咱雅班智达,他支持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章嘉·若必多吉与清朝皇室兴建的喇嘛寺院》(《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一文对章嘉·若必多吉参与修建雍和宫、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寺院进行了分析考证。《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则从先辈奠定的基础、少年时代的同窗之谊、成为国师喇嘛、皇室兴建佛寺的顾问、组织皇室佛经翻译、处理蒙藏事务的参谋助手等多个方面对其事迹进行了分析研究。此外还依据翻译过来的传记整理了章嘉·若必多吉年谱资料(《青海民族研究》1990年第1、2期)。《土观·却吉尼玛及其〈颐和园礼赞〉》一文介绍了担任乾隆皇帝禅师的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63年抵达北京,1764年历时10年的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建成,随皇帝园中浏览时写下“颐和园礼赞”的史事。《二世嘉木样活佛晋美旺波东行纪略》(《安多研究》创刊号,1993年)一文认为,二世嘉木样是对拉卜楞寺的巩固和发展并将其影响扩大到安多各地和西藏、内蒙古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他1769—1771年前往五台山、北京、热河、内蒙古等地活动,历时长、范围广,接触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等众多人物,并获得了大量布施,巩固了拉卜楞寺的经济基础。
(四)藏传佛教寺院及文物研究
《青海贵德珍珠寺碑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一文依据《安多政教史》载,“觉觉”系汉语“珍珠”的变音,萨班贡噶坚赞应阔端之请来安多,途经青海时曾去贵德朝拜包纳塔,并以阔端所赠珍珠一驮为资建寺,是为珍珠寺。按此该寺当初建于南宋淳祐年间。《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碑刻译释》是第一部系统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碑刻的金石学专著。《青海塔尔寺调查》是陈庆英先生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从事塔尔寺藏文文献研究的成果之一。此外,他还主编了《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一书,按照佛、本尊、菩萨、祖师、护法分为五部分,按年代顺序依次排列,收录了300件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该书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三、陈庆英先生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与代表性成果
(一)蒙藏关系史研究
《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是陈庆英先生较早出版并具有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后来又在对蒙藏关系持续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一书。《蒙藏的早期交往及西夏在蒙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一文认为,从地域上看,蒙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带与青康藏高原的联系,而且加强了这两大地区与中原农业地区的交往;从经济上看,蒙藏关系的发展强化了通过贡赐和互市的形式,从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产品与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行交换的格局;从文化上看,蒙藏关系的建立、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及上升到占据主流地位,形成了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从陆路上环绕和屏蔽中原文化区的广大藏传佛教文化区,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人合写的《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的起源新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一文,依据藏文传记资料发现,多罗那它一生中从来没有离开过西藏,不可能去喀尔喀传教20年,而五世达赖喇嘛与觉囊派创始人多罗那它有个人怨恨,以至于掌权后打压觉囊派,他自然不会把觉囊派的活佛多罗那它说成是格鲁派在喀尔喀最重要的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前身。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前世应当是哲蚌寺的建立者嘉央曲杰·扎西班丹(1379—1449)的某一代转世,当然不存在哲布尊丹巴从觉囊派改宗格鲁派的问题。在西藏人的眼中,喀尔喀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僧籍在拉萨三大寺系统中是属于哲蚌寺的郭莽扎仓。造成这种混淆的原因是,一世哲布尊丹巴曾经对弟子回忆他1650年在五世达赖喇嘛身边学习金刚坛城灌顶的经历,以及后来到扎什伦布寺跟四世班禅学习时,四世班禅说:“你是多罗那它的转生,在语言方面受到多罗那它的语的加持,你要以多罗那它的名义对众生加持施恩!”四世班禅在这里说的多罗那它并不是指觉囊派的活佛多罗那它·贡噶宁波,而是指多罗那它这个用藏文音译的梵文词的本义,即是依怙神、怙主、救主的名字,藏文译为“མགོན་པོ”。
(二)西夏研究
陈庆英先生有关西夏与藏族关系的研究,曾经受到前人关于西夏是藏族的一部分、党项就是“ལྡོང”的意思的观点启发。其后结合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中涉及西夏历史的记载,利用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西夏文的注音和表意来研究与藏语的关系,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西夏语是以一种语言为基本语言,混合了许多其他语种的语言,类似于青海的“家西番”。其相关的研究成果体现在《西夏语同藏语词汇之比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从西夏〈文海〉看西夏语同藏语词汇的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4期)、《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藏学研究论丛》第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西夏族源探讨》(载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民族学报》第22期,1997年)等论文之中。他的主要观点是,现在很难断定藏族与西夏人的关系,原是一个民族,后来分成几个民族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西夏的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跟藏族保持着某种联系,如“འ་ཞ་ལྡོང”可能是归附了吐谷浑的董氏部落,“མི་ཉག་ལྡོང”就是归附了西夏的董氏部落,而“མི་ཉག་ཤར”(弭约夏)是后来建立西夏王朝的那个部落。“ཤར”就是“夏”,又如大夏河称之为“ཀ་ཆུ”,其实藏语当中指“བསང་ཆུ”是夏河的上游。缺乏文字记载的分裂割据时期,只是有个唃厮啰王朝和古格王朝,他认为中间一大部分应该是西夏。西夏就是汉藏和北方民族,如蒙古、女真等夹杂在一起的,成为藏族和这些民族相互交往的很重要的一个中间桥梁,而且它延续了吐蕃王朝的文化、制度等。由于汉文历史文献《隋书》《通典》《北史》《旧唐书》《新唐书》等给吐蕃列传的同时,也给党项或党项羌列传,因此吐蕃与党项是存在密切关系的两个古代民族,是否能弥补割据时期的历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上述研究无疑深化了人们对两者关系密切程度的认识。
陈庆英先生有关藏传佛教与西夏佛教关系的研究,也十分引人瞩目。他先后发表了《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大乘玄密帝师考》(《佛学研究》2000年第9期)、《〈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等论文,从文献典籍和重要人物事迹方面考察了两者的联系。大乘玄密帝师是西夏帝师,来自西藏,是噶举派著名祖师米拉日巴的再传弟子。由清宫流传出的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第六篇《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题款为“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中国大乘玄密帝师传,西番中国法师禅巴集”。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包括西夏文、汉文两种乾祐二十年(1189)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高僧名单,天庆元年(1194)为刚刚去世的仁宗皇帝刻印的西夏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文献中,都有大乘玄密国师。在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第六十六篇《大手印伽陀支要门》的师承次第中,也记载着大乘玄密帝师,他们都是西藏高僧。陈庆英先生认为,西夏的帝师大部分是藏族后裔,有些是直接从西藏过来的,他们中间就有噶举派的。有一位帝师写了《大乘显密》一书,他也许是西藏人,也许是西夏人,也可能是西夏地区长大的西藏人。可以确信的是,西夏的帝师属于藏传佛教。西夏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对元代有重大影响。元朝时期像噶玛巴希、攘迥多吉这样的很多藏族高僧就曾到西夏地区弘扬佛法,他们也知道西夏是加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地带。元代帝师可能继承了西夏的这个称号,并且沿用了西夏的印章。现在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管理制度,与唐宋时期汉传佛教的寺院管理制度具有很多相似性,这是因为西夏时期通过两派佛教融合而形成了这种制度。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陈庆英先生还撰有《“白狼歌”新探》(《江河源文化研究》1992年第2期)一文,对藏语与白狼语同源的词汇和语法习惯进行了系统探讨,发现在白狼语中有多个词汇和藏语同源。他还撰有《民国藏事档案解读之一——〈西藏驻京堪布贡觉仲尼为报到并呈履历事致蒙藏院呈〉》(《民族学报》2005年第24期)、《解读西藏驻京堪布贡觉仲尼到京任职的几份档案》(《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探讨民国时期涉藏档案中驻京堪布贡觉仲尼的相关事迹。参与编选《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担任《藏族传统文化辞典》副主编,编写《阿古顿巴的故事》,担任《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主编之一,为藏学研究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另外,作为陈庆英先生藏学研究又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他在藏汉历史文献的翻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将来另文讨论。
四、陈庆英先生的治学方法及其经验启示
陈庆英先生先后在青海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受过良好的学术研究训练,但是总体而言,他不是纯粹的学院派,所以其学术成就更多地来自长期的基层实践和个人的勤奋努力,特别是长期的青海牧区生活对他的学术和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藏语言的学习和实际运用更是他从事藏学研究最突出的特色,他对此记忆犹深:“在1963年我们到青海共和县倒淌河,在牧民家住了半年,从实践当中学习藏语口语。”他对藏文历史文献的翻译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我觉得翻译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学习藏文古籍。藏文古籍是藏族的先辈学者在几百年前写成的,和我们今天的环境,特别是和汉族学者们的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要读懂它们,除了文字的功夫外,还要仔细去体会作者的思想和逻辑思维,甚至要设身处地去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古籍进行全本的翻译比仅仅选择某些写作论著需要的段落和字句要好很多。另外,从翻译古籍中,还可以学到很多相关的知识,对藏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有更广和更深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陈庆英先生上述的研究领域和所翻译的藏文历史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如元明清三代的藏族历史研究,都是从翻译藏文历史文献开启的,他的代表性成果也是在研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厚的藏文文献资料基础,甚至他翻译的外文资料也多与其研究主题相互关联。而他本人独自或者与同仁合作翻译的藏文著作,都是相关时期十分重要的藏文历史文献,为藏学界特别是从事西藏历史宗教和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辛而要求极高的工作,不仅需要很好地掌握两种语言,还需要丰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懂得翻译方法技巧,以及严谨认真的良好学风,陈先生的藏汉翻译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无论是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还是翻译成果,陈庆英先生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人合作,这一部分成果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以发表论文为例,他曾经与20多人合作,发表约40篇,而且合作的对象既有前辈学者、同辈学者,也有晚辈年轻学者,体现出良好的协作精神。这在藏学界,乃至更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不多见。
从具体研究领域,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研究方法,比如说从敦煌文献入手研究吐蕃经济社会制度问题,从藏族的部落著述研究青海涉藏地方的历史,从历代达赖喇嘛的生活事迹入手研究藏传佛教寺院、高僧以及活佛转世制度问题,从语言、典籍、风俗的考察研究藏族与西夏政权的文化关系,还有从藏文文献的翻译注释入手,研究元明清三代西藏地方历史和藏族历史宗教。他认为,除了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和对藏学事业的热爱以外,做藏学研究要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学者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学术素养,如做历史研究的要懂得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的要懂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二是掌握语言文字工具,包括藏语文、汉语文、外国语文;三是有在藏族聚居区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得到藏族朋友的信任和帮助。这也可以说是他从事藏学研究的真实写照。
2002年,西藏通史课题研究立项以后,陈先生带着我们历史所的几位年轻同志在西藏跑了很多地方,拜访了很多前辈和同辈学者,看了很多文物,查阅了大量的藏文文献,同时也实地考察了很多民间传说发生地,以及历史古战场、重大事件发生的地理环境,重要历史人物的故居等,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在与陈先生长期的共事之中,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他始终坚守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崇高使命,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有追求、有担当,反对戏说猎奇、捕风捉影,敬业地从事藏学研究,尊师重道,对自己的老师和前辈怀报真切的感恩之情,同时也热心真诚地帮助、提携后学,为中国藏学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购书请扫码进入中国藏学官方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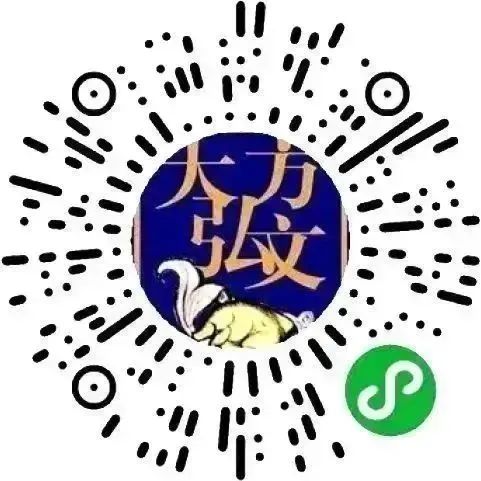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