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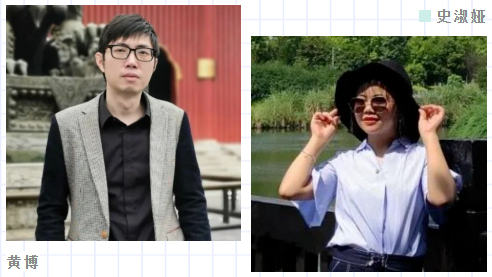
【摘要】唐高宗即位后晋封松赞干布为賨王,但无论是地域上还是族属上,吐蕃与賨人都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吐蕃崛起于隋唐之际,賨人在此时却已基本消失。文章梳理了史料中关于賨人和吐蕃的族源、特征及其与汉、唐等中原王朝的关系,分析了汉文文献中賨人、吐蕃族源记载纷繁复杂的原因,认为唐高宗之所以分封松赞干布为賨王,可能是賨人与吐蕃存在着一种跨越时间的虚拟联系。賨人、吐蕃与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高度相似,这使得两者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一种虚实相通的共同性。另一方面,两者各自呈现出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混融状态和多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状态,即可能是松赞干布得名賨王之由,更在不经意间体现了中古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賨王;松赞干布;吐蕃;唐朝;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简介】黄博,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史(藏族史)和中国古代史(宋史)。史淑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22)01—0072—08
松赞干布统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极大地推动了西藏历史发展的进程。纵观吐蕃王朝的崛起与繁荣,也并非只是依靠吐蕃的一己之力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吐蕃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军政机制整合青藏高原上的诸如象雄、苏毗、吐谷浑等部族,另一方面又广泛地与中原、西北、西域各民族的先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持续、深入的交往和交流。可以说,吐蕃王朝时期是历史上藏族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一次高潮,其中唐蕃之间的交融互动最为频繁,影响也最为深远。学界对唐蕃关系的研究全面而深入,但有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比如唐朝册封松赞干布的的“賨王”封号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来讨论和解析松赞干布的賨王封号的含义和意义。
一、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野下吐蕃与賨人的共同历史
唐高宗即位前后,松赞干布在唐朝的册封体制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先是因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出兵助王玄策破中天竺,而获封附马都尉、西海郡王,旋即因高宗新继位而致书唐廷表示忠心,而晋封賨王。关于这次封王所赐给松赞干布的王号,在中古史籍中却有多种说法,除了“賨王”之外,还有“宝王”和“宾王”,但主流典籍如《通典》、新旧《唐书》等都记为“賨王”,“宝王”和“宾王”主要来自于明刻本的《册府元龟》。比勘宋刻本《册府元龟》,可以清楚地看到,“宝王”、“宾王”皆属讹字,因此松赞干布的王号当为“賨王”无疑。那么,唐朝官方为什么给吐蕃首领册封一个“賨王”的称号呢?
有关松赞干布賨王封号的解读,学界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王尧认为“賨”应与藏语的“ཚོང་”、“བཙོང་”相关,本义为交换,賨人应是古代四川境内北部和东北部的藏族,因此賨王就是藏王。与之不同,洛加才让认为史籍中的賨人指的是居于嘉陵江流域的板楯蛮,并不是藏族,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賨王,是因为松赞干布助唐军灭天竺一事,与古代典籍中賨人“剽勇”的形象,以及汉高祖借助賨人之力平定三秦的典故有关。唐朝册封松赞干布为賨王的意涵,笔者基本赞同洛加才让的破解思路,即不能简单地把吐蕃和賨人的共同联系理解为同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空上的分支。如果将吐蕃与賨人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历史,决定了在中华民族命运共体中的各民族,必定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跨越时空的共性。具体到历史上,吐蕃与賨人之间存在的某种“异族相类”的相似性,使得不同的民族拥有共同的历史也成为可能。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海郡王到賨王,唐廷对于吐蕃人在中原王朝的封贡体系内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海郡王遵从的是地望封爵的传统,西海为古郡,始置于西汉末年,此后屡有兴废,最晚的一次是隋炀帝时所置。西海郡治所徙置不常,但地望多在青海湖东,故唐廷以西海郡地代表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亦是顺理成章之事。综观有唐一代对边疆民族政权首领的封号,也多循此例,如与松赞干布同时代吐谷浑可汗们,所获得的封号即从“西平郡王”、“河源郡王”而进一步晋升为青海王;此后兴起的南诏,其首领也是先封“台登郡王”,再晋升为云南王。惟有松赞干布的賨王之封是一个例外,这一封号没有遵循唐代常用的属地原则,而是给吐蕃首领封赐了一个带有强烈的族属性质的王号。賨王之“賨”,其所指代的乃是秦汉时期西南夷中的一支著名的人群,又称“板楯蛮”,其生活的地域范围在渝水(嘉陵江)两岸。板楯蛮因助汉高祖平定三秦而得到西汉朝廷的优待,其中的渠帅七姓“不输租赋”,而“余户乃岁入賨钱”,即以賨钱代替上缴给朝廷的赋税,賨人之得名即源于此。
事实上,吐蕃与賨人无论在地域还在族属上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从空间上来看,吐蕃兴起于西藏腹地的雅隆河谷,兴盛于青藏高原,而賨人则主要活跃于四川盆地东部的嘉陵江流域,两者通过地域上的关联性而产生某种族属上的渊源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从时间上来看,在唐代,賨人已是一个“历史民族”,而非“现实民族”。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中,賨人(板楯蛮)或不断迁徙,或离开世代聚居的山地迁居平地,最终与汉族融为一体。隋唐以后,史籍中基本上已再也见不到有关賨人活动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唐朝册封松赞干布为賨王之时,賨人已经消融在历史之中了,时人并不会真的在族属意义上把吐蕃人和賨人混为一谈。所以,松赞干布的賨王之封号似从属地原则转型为族属原则,但这一族属应该不是实指,而是一种可能跨越时空的虚拟联系。
其次,要真正理解吐蕃与賨人的虚拟联系,还必须把两者放置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观察。隋唐之际,賨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但在历史记忆中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一方面,以賨人歌舞为基础编成的“巴渝舞”,从汉代开始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礼乐典制之中,一直传承到隋唐时期,成为南北朝乱世之后大汉礼乐硕果仅存的“清乐六十三曲”之一,是秦汉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典范之作。《旧唐书•乐志》载:“《巴渝》,汉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汉伐楚,以板楯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高帝观之曰:武王伐纣歌也。使工习之,号曰《巴渝》。……魏、晋改其名,梁复号《巴渝》,隋文废之。”可见源于賨人的巴渝舞,至唐代尚存舞曲和歌词,舞曲有《矛渝》《安台》《弩渝》等,只不过对唐人而言,“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而已。因此,对今人而言,或许有些冷门的賨人,在唐代的文化界却并不陌生。比如唐代文学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前流行的骈体文,作者需要大量属辞用典,高祖李渊下令编纂的唐前典故类编《艺文类聚》收录有关“舞”的各种典故中,就有“巴渝舞”。
另一方面,唐初编成的正史《晋书》中有专篇记载十六国时期成汉政权的“载记”,其中对于賨人历史的描写就相当生动鲜活。《晋书》认为成汉政权所依恃的基本力量就是巴人(賨人),书中除了把賨人得名之缘由再讲一遍之——“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及汉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之外,还大力渲染了賨人的剽悍勇武、能歌善舞的风俗习性——“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晋书》编写是在唐太宗亲自关心和参与之下,由宰相房玄龄、褚遂良等人领衔编纂。《晋书》完成于贞观二十二年,正是高宗册封松赞干布为賨王的前一年。同时,这一年唐蕃之间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当年五月,松赞干布出兵助唐使王玄策平定中天竺之乱。王玄策此前奉命出使天竺,恰巧碰到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病死,国内大乱,其臣下阿罗那顺自立,发兵围攻王玄策。王玄策一行属外交使团,只有30人,最后寡不敌众,力战被俘。事后,“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助战,王玄策最终得以率吐蕃及尼婆罗援兵反攻中天竺大军,击溃其主力,俘阿罗那顺以归。事后松赞干布亦遣使向唐廷献俘。
最后,吐蕃发兵助王玄策平定中天竺之乱,可谓唐蕃交往过程中非常成功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其事不但与賨人助汉高祖平定三秦的历史相似,细绎史实可以发现,賨人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经常以其剽勇助力平乱。賨人此前又称“白虎复夷”,传说秦昭襄王时,因“群虎”为害秦、蜀、巴、汉之地,“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最后因賨人之力,射杀白虎,賨人也因此获得秦王优待,“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这则故事中为害秦、蜀、巴、汉之地的“白虎”,当为活跃在秦巴山地、崇祀白虎的廪君蛮,后世与賨人一起俱称巴人。賨人的剽勇之风,其后屡屡为中原王朝所借重,东汉时期,经常是“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因其作战神勇,“故号为神兵”。朝廷多次借助賨人之力征战四方,史籍中屡有“实赖板楯连摧破之”、“亦倚板楯以成其功”的赞辞。历史上的賨人一登场即以剽勇著称,而吐蕃人在唐人的认知中也是天性劲勇之辈,其勇猛之风当不下賨人,比如《旧唐书》描写吐蕃人的风俗,“弓剑不离身……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
而松赞干布在唐高宗即位后又表示,“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这两件事情结合到一起所展现出来的吐蕃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助力唐朝事业的情景,犹如两汉在军事上依重賨人那样,唐蕃双方联手疆场的佳话也可以续写下去。从这个意义上看,吐蕃与唐,跟賨人与汉朝的交往交流何其相似!唐高宗此时以“賨王”之号封授松赞干布,可能就是唐朝与吐蕃的交往交流的现实,和賨人的历史形象交相辉映的结果。
二、吐蕃与賨人的深层联系: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空共性
“吐蕃—賨人”的历史联系,除了前文所揭示的典故意义上的相似性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内涵。历史典籍中的賨人故事在隋唐之际正发生着重大改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賨人的族属开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纠缠不明的交融态。以《晋书》的《李特载记》为例,该书以为成汉政权的建立者李特一族,“其先廪君之苗裔也”,接着转述了廪君与盐神的传说以追溯賨人的起源。当然,将賨人与廪君之裔联系起来的做法,并非《晋书》首创,南朝的《晋中兴书》、北齐时所修的《魏书》中的《李雄》传,既已秉承此说。廪君神话最早见于《后汉书》的《巴郡南郡蛮传》,但其中廪君蛮和板楯蛮却是族属不同的两支人群,对此学界已论说甚明,特别是在其族源神话和传统风俗中,廪君蛮因廪君之魂魄化为白虎故而世代崇祀白虎,而板楯蛮则应募专以射杀白虎为事,两者最初实为水火不相容之两族。但《晋书》误将廪君蛮和板楯蛮混为一谈,却不可以简单地以学问不精责难唐初之史臣,賨人从族属分明到混杂不明的过程,其中的确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前所述,賨人的聚居区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的山地,与后来廪君蛮所长期生活的巴渝之地相邻,两者活动的范围大体都在秦汉时期的巴郡境内,且经常一同行动。《三国志》载,东汉末年曹操征讨张鲁之际,有“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此条记载尚可见当时巴夷(廪君蛮)和賨人(板楯蛮)二者仍然有清晰的区分,但已是联名并称、联合行动了。事实上,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后世被外界视为一体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是,魏晋之后,賨人处于逐渐消融和重组的过程中,这也强化了賨人这种族属混杂不明的状态。成汉时期著名的“獠人入蜀”事件促成中古时期巴蜀地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賨人又与獠人有合流之势,东晋时人就已“误会”賨人为獠人,如郭璞在谈及“汉高祖募取三秦”的典故时,已径称“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募取以平三秦。”所谓“獠人”,其共有的特征为竹王崇拜、凿齿穿耳、使用铜鼓、死葬悬棺等,语言上也具有壮侗语族的特征,与賨人显系两族,本无疑义。更有意思的是,賨人的一支在当时又与氐人交融在一起。成汉李特一族本为賨人大族,东汉末年李特祖先率五百余家归顺曹操,迁居略阳,与氐人杂居,此后其族称又有“巴氐”之号,学者大致认为巴氐当为賨人之后裔豪族与氐族之流民的一种组合,或者也可能是巴人而氐化者。综上可见,賨人在隋唐以后的史籍中呈现出的族属不明的现象,实际上正是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反映。
与隋唐之际賨人的情况相似,唐宋时期中原知识界对于吐蕃族属的认知也处在一种混融不明的状态。如《新唐书》就把吐蕃的起源和羌人混为一谈,称“吐蕃本西羌属”,并详叙了吐蕃与西羌的源流,认为吐蕃之祖“鹘提悉勃野”是源出西羌系的“发羌”、“唐旄”等部,因其“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唐人杜佑撰著的《通典》,在考述吐蕃族源时则补充了吐蕃族源的另一个可能性,书中以“或云”的方式叙述了十六国时期南凉王室后裔逃遁立国于吐蕃的故事,主要内容是南凉的统治者秃发利鹿孤的幼子樊尼在亡国后,投奔了北凉的沮渠蒙逊,其后世子孙任临松郡丞,与主簿皆得众心,至北魏末年,天下大乱,“招抚群羌,日以强大,遂改姓为窣勃野,故其人至今号其主曰赞府,贵臣曰主簿”。其后《旧唐书》更加丰富了这个流亡立族的故事,谓樊尼在亡国后,投奔了北凉的沮渠蒙逊,北凉亡国后,“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当然,此说在学者们看来不值一辨,当然不足为信。南凉和北凉都崩溃于5世纪前期,而藏文史籍记载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蕃的赞普世系已传承了30代,如按樊尼西奔于北凉亡国后推算,则30代只约二百余年,亦极不合理。
上述这些说法虽然并非信史,但从《通典》到《旧唐书》都载记其事,可知此说也是唐人对吐蕃族源的一种认知,就像史书中的賨人的族属一样,曾经给吐蕃的溯源研究造成了不少困惑。如构成早期吐蕃主体的悉补野部兴起于西藏腹地的雅隆河谷,他们与氐羌系的发羌部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渊源,吐蕃王室源于南凉王室流亡后裔的说法,也经不起其他史料、特别是吐蕃史料的印证。事实上自来就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有怀疑的态度,马长寿很坚定地认为,“发羌为吐蕃的祖源之说,绝不可信”,格勒对这一问题也有详细的辨证,从文献史料和历史语言等多方辨析了此说的种种疑点。
辨证吐蕃与羌人的关系当然重要,但显然唐人喜欢把吐蕃的族属与羌人混为一谈也是事实。对于这一难题,如果我们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来看待这些记载的话,很多问题就可以豁然开朗。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的腹地,而青藏高原的东缘生活的都是氐羌系的人群。吐蕃在崛起的过程中,就吸纳了甘、青、川、藏等地众多的羌人部落,最典型的就是苏毗。《新唐书》称,“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苏毗在加入吐蕃之前乃是羌人的一支,伯希和认为“苏毗”之称本是一个羌语词,而它的古藏文名称“孙波”(སུམ་པོ)则是一个藏语词,当是苏毗被吐蕃征服后改称。而松赞干布时期,苏毗被吐蕃征服,敦煌藏文写卷P.T.1287载,“王子赤松赞(即松赞干布——引者注)在位时,娘·莽布支尚囊受命收抚苏毗诸部,归于治下”。其后,吐蕃在东向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征服了党项羌、白兰羌、多弥羌等诸羌部落,吐蕃的兼并诸羌,客观上使得吐蕃与西羌之间的交往交流持续而深入,无疑给唐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吐蕃源于西羌之说,应该是唐代史家在双方长期交融后产生的误会。
此外,在吐蕃源于西羌的描述中,《通典》《旧唐书》等把吐蕃王室的来历溯源至南凉秃发氏也值得深思。事实上两者在历史时空上的跨度都太大,绝难置信,似又不可解。南凉秃发氏本属鲜卑拓跋的一支,因移居河西,后世又称之为河西鲜卑。秃发氏降魏后,魏太武帝曾以秃发氏与己同源,赐姓秃发氏为“源氏”,历北魏、隋、唐,皆称著姓,唐玄宗时即有名相源乾曜知名于世。有意思的是,河西鲜卑本身就是流亡立族叙事的代表,《晋书》谓秃发氏“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入河西。”吐蕃的族属与河西鲜卑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吐蕃的发展壮大却跟鲜卑人关系匪浅,从松赞干布开始,另一支西迁的鲜卑部族与羌人融合后所建立的吐谷浑最终被吐蕃王朝所吸收,《魏书》《晋书》均载“吐谷浑”本为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廆的长兄,因兄弟不和,率部出走,其后转徒西迁至甘、青地区与当地诸羌、胡部落融合后形成的新族。而在吐蕃史家笔下,吐谷浑与吐蕃毗邻,吐蕃称其为“阿柴”。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松赞干布收服苏毗后,“其后赞普亲自出巡,在北道,即未发一兵抵御,亦未发一兵进击,迫使唐人及吐谷浑人,岁输贡赋,由此,首次将吐谷浑人收归辖下。”可见,吐蕃在崛起过程中与鲜卑后裔的交往交流也非常密切,以致吐蕃王室源于鲜卑贵族之后的说法在唐代一度颇为流行。
最后,前揭賨人与汉朝的交往交流过程中,賨人日常生活的能歌善舞的代表“巴渝舞”在经过改造后被吸收到中原王朝的乐舞体系中,成为中原王朝礼乐典制的组成内容,传承了数百年。由此看来,这并非一种简单的接触式的泛泛之交,而是深度交流后的形成的一种文化交融状态,而吐蕃在和唐朝的交往中,文化交融也是非常显著的成就之一。在“賨—汉”交往的文化交融状态中,汉朝将源于賨人的巴渝舞吸收改造成为中原王朝的礼乐典制的组成内容,而“唐—蕃”交往的文化交融状态则是吐蕃将不少唐朝的文化要素吸收改造成为吐蕃文化的组成部分。吐蕃崛起后一开始就有主动学习、借鉴汉文化优秀成果的意识,而松赞干布正是吐蕃和唐朝大规模文化交融的开启者。松赞干布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后,就“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后世的藏文史籍也记载了松赞干布挑选4名聪明有识的吐蕃人携重金前去汉地学习的故事,并且还亲自嘱咐他们,“你们到汉地去,学习对我们吐蕃有益的学问。”现存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尚书》的藏译本,在P.T.968中保留了藏译《尚书》的《泰誓》《牧誓》《武成》的一些残篇,笔者此前曾考察过,这些残篇的藏译文都具有相当深湛的经学造诣,并非简单的依书直译,而是参考了唐代关于《尚书》的研究成果如《尚书正义》等,足见双方在文化交流上的深入程度。
另一方面,在追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松赞干布时代也是后来藏族史学家在后世塑造的一个黄金时代。如所谓的“博唐”(སྤོར་ཐང)之术就被认为是松赞干布时期的唐蕃文化交融的文化成就。此术实乃中原内地流行的堪舆风水术结合阴阳五行理论推算吉凶的一种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唐代也非常流行,这一学说流入吐蕃与文成公主关系密切,藏文古籍《柱间史》记载,唐太宗因中计而焚毁了《五行卜辞》等书,造成阴阳五行推算占卜之术失传,但文成公主却在此前将这些书收藏了起来,并在后来把这些书带到了吐蕃。《贤者喜宴》也载,文成公主入藏后,以“博唐”推算出吐蕃境内的各处地理方位和地形的吉凶祸福,并据此设计了镇伏之法。这些说法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蕃文化交流在松赞干布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小结
虽然历史上的賨人与吐蕃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时间上,賨人活跃于秦汉时代并在隋唐之际作为一个整体已基本消失,而吐蕃则恰恰崛起于隋唐之际;在空间上,賨人主要活动的地域在巴蜀地区的嘉陵江流域,而吐蕃则兴起于青藏高原腹地,本应风马牛不相及。但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态,却将本来“此起彼伏”的两族拉到了一起,唐高宗选择“賨王”封授吐蕃的首领,某种程度上正是唐代官方对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认知。可以说,賨人与吐蕃看似“虚拟”的联系背后,有着穿透时间(历史过程)和空间(地理分布)的“实在”联系,两个时空交错的古代民族,各自呈现出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混融状态:賨人与廪君蛮、巴人、氐人、僚人等族,吐蕃与西羌、鲜卑诸部的纠缠不清。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属认知和族源记忆,既是松赞干布賨王封号得名之由,也在不经意间体现出中古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