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顾问
白振声 陈庆英 格勒 郝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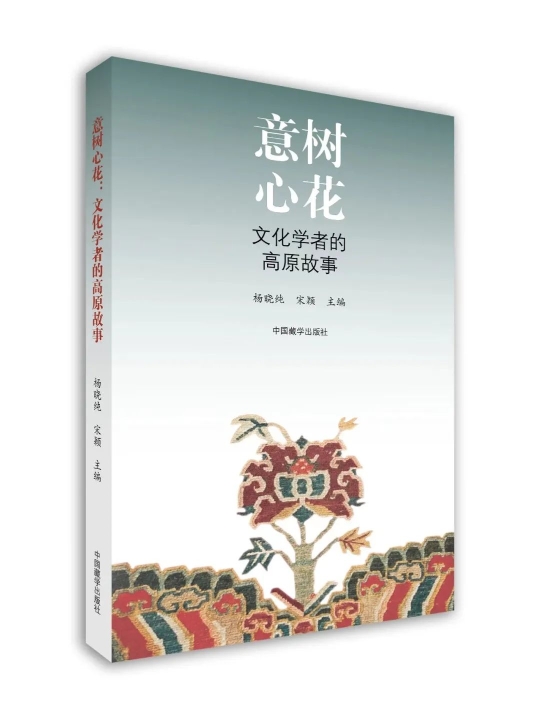
《意树心花: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
杨晓纯 宋颖 主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序
格勒
我最喜欢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天清地明的季节。每到这个季节我就可以走出书房,漫步在花树成林、鲜花盛开、绿草围绕的校园里。而且每周一次乘坐免费的校车到双流新校区,与那些活泼可爱的学生见面,把我有限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们。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联合博士点聘请的一名教师,我过去大部分时间都在武侯老校区给博士生和硕士生讲课。如今我接受了为本科班讲授新课《考古学导论》的任务。
如今的双流新校区树木成林、绿草茵茵、花香四溢,眼前的一切仿佛是我曾多次去过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校园,一座座红色的砖墙排列有序,校园里人工湖边樱花、桃花、梨花等竞相开放。正当我沉醉在美丽的校园景色中之时,背包里的手机响了。一条来自我曾经工作二十多年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微信转移了我观看校园风景的视线。微信来自我曾担任第一任所长的社会经济所青年学者杨晓纯(现为当代所副研究员——编者注):“格勒老师,您好。2月26号给您寄出的《意树心花: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书稿,您收到了吗?”我恍然醒悟,是啊!我古稀之年记忆自然衰退,忘了早在2月25日小杨就给我发微信告诉我她和宋颖主编的《意树心花》一书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可以出版了,并特别提出:“格勒老师,我有个不情之请,想请您拨冗为这本书作序好吗?”同时发来了书稿目录,不久又快递寄来了纸质版的书稿。我当时欣然答应,毕竟我是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老员工、老党员、老所长,谁见了都道一声“保重”的一位老人。但当我翻开沉甸甸的三百多页的书稿时,心里直犯嘀咕,别说写序,首先阅读一遍就得花不少时间,而我毕竟已进入头昏眼花、腰酸背痛的古稀之年。按理说退休后优哉游哉、无所事事,写个序言至少不缺时间吧,然而自2011年从单位退休后,我依然坚守在藏研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联合申办的博士点课堂。平时不但要阅读、备课、讲课,偶尔有空还要参加名目繁多的学术会议或应邀为一些刊物撰写一两篇论文,等等,琐事缠身,加上游泳、走步、健身等等,小杨嘱托之事耽误至今令我内心惭愧不已。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通过阅读杨晓纯和宋颖主编的《意树心花: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可以看出是按作者的经历和所讲的故事内容精心编选完成的。全书分为“流金岁月”“花开千树”“一路同行”“初心不变”四部分。全书三百多页,收集了六十六位作者的文章。其中“流金岁月”部分收集了十五位大多年事已高或已经退休作者的文章。据“百度”解释,“流金岁月”为过去的美好时光兼有怀旧的心情。虽然我们这一代或两代文化学者美好、珍贵的经历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所经历的坎坷复杂的蹉跎岁月却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和值得回味的人生印记。从农奴社会、民主改革、平息叛乱、“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到改革开放,我们都经历了、参与了、痛苦了、享受了。我为经历过这些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辉煌历史而庆幸。这部分故事的作者既有邓锐龄、郝苏民、白振声等八九十岁的学术老前辈;又有陈庆英、喜饶尼玛、朱晓明、毕华、马盛德、孙勇、车明怀、胡岩等与我同龄的六七十岁学者;唯一廉湘民例外,迄今在职。第二部分“花开千树”收集了包括杨福泉、何贝莉、祁进玉、杨军财、王川等多达二十位学者的文章,他们是小于我们这一代的中年学者。清代诗人戴亨有诗曰:“花开千树锦,柳亸一林烟。鹿过溪留迹,云归月满川。”我们这一代学者日复一日地刻苦研读,不但练就了自身心满钵满的学术容器,而且形成了滚滚向前的溪流,虽然弯弯曲曲,但为后人留下了可以追寻的学术印迹。第三部分“一路同行”包括杨明洪、郭建勋、当增吉、陈立健等十六位学者的故事。最后第四部分“初心不变”包括徐平、王小彬、格桑卓玛、李志农等十五位学者的文章。他们大多都是我见过或认识的学者。
六十六位作者老中青,无论谁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或离不开的故事,这就是为了研究藏学,跋山涉水,走过西藏、走过四省涉藏州县,走过青藏高原,为党的事业走西藏、走高原。他们为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幸福而曾经或正奔走在青藏高原的高山峡谷中,书写出一篇篇精彩的论文,伏案出一部部精心雕琢的著作,撰写出一篇篇供中央相关部门决策参考的报告。《意树心花》仅仅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千千万万田野调查故事或涉猎藏学中的一段、一节、一项而已。文中所写每一个故事无疑皆为他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事,他们抱着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拳拳之心,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个生动、真实、令人向往的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可以说,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了比教材更加鲜活的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记得刘延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时讲过,“了解一个民族,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我们藏研人要尊重和了解藏族文化究竟从何着手?我们的前辈藏研人用他们的言行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永远忘不了我被分配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不久,总干事多杰才旦(曾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专门请邓锐龄先生为我们年轻人讲述做学问之道,我从他的演讲中感受到他治学严谨,为人谦和。他撰写论文时论述严谨、用词精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意树心花》中写道:“1962年,我 37岁,才开始做西藏史的研究工作……说搞藏族史,我得学学藏文吧。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还是学了一年多的藏文。”后来他调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参加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史的一个重点课题,他给我们讲了在他古稀之年为了解和研究西藏历史在原有基础上又重新开始学习藏文。这令我们感动万分。我的硕士导师李有义教授曾说过:“西方的藏学首先是从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开始的,因为要研究一个民族首先你就得懂他的语言,否则你就无法接近他和了解他。”邓锐龄和李有义、王森、李安宅、胡坦等许多老一辈汉族藏学家一样,为了研究藏族和了解藏族而学习藏文的精神和优良传统,值得今天研究藏学的年轻人传承和发扬。为此我曾专门撰写论文,其中写道:“一千多年来,记录藏族历史文化的藏文史籍或古籍浩如烟海,其内容除了宗教,还有历史、哲学、医学、艺术等等。当我们今天如此为西藏的传统文化陶醉之时,或如此多的人试图证明藏族古老文明底蕴之时,若不懂得藏语或藏文,何谓藏学研究?”岂止老一辈藏学家,《意树心花》文集中作者之一的我的同龄人、好朋友陈庆英原籍广东省,也是汉族学者中学习藏文的榜样。记得我们共同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经常一起上课,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与端智嘉合作把《旧唐书·吐蕃传》翻译成藏文,后来又把《论西藏政教合一》《汉藏史集》等藏文名著翻译成汉文,为中国藏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不但能阅读古藏文,还能与我们这些藏族学者用藏语进行交流。每当汉族同行与我讲藏语,无论水平高低,我内心都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
如果说我在《中国藏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第一部分讲的是“藏学研究与藏语文学习”,说明藏学研究离不开藏语文的学习和研读,那么中国特色的藏学研究更离不开为现实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就是陈虹同志主持工作时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服务”工作宗旨,其中两个服务就是科研要为西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朱晓明同志在《意树心花》中形象地比喻为“牵住‘牛鼻子’”,即抓住现实中出现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关键在何处?一是中央需要什么,我们研究什么;二是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需要什么,我们研究什么,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的各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研究什么。朱晓明同志说:“2008年,拉萨发生了令人震惊的 3· 14严重暴力违法犯罪事件,……中央统战部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布置了一项带有长远意义的课题,要求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回答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如何构建寺庙管理长效机制问题。”这项重点课题的成果为形成中办有关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的文件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意树心花》的作者群中还有我认识的廉湘民、毕华、车明怀、胡岩、杨明洪等等,都撰写过为现实服务的高水平文章和调研报告,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赘述。
《意树心花》中有我熟悉的很多作者,甚至有些作者与我一路同行为完成我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曾在高原上骑马、走路、坐拖拉机翻雪山、过草地、进村入户进行田野调查,其中包括王川、杨明洪、徐平、杨军财、郭建勋、当增吉、格桑卓玛等,后来他们当中有三位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我们撰写的论文对普通受众也许晦涩难懂,因为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是通过梁艳的一篇口述史认识了我,还有的旅游爱好者和企业家是通过《月亮西沉的地方》认识了我。由此我相信《意树心花》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因为这是一部由许许多多故事像天珠项链一样串起来的文化学者的“自供状”,讲述了他们自己在高原上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意树心花”以及他们对高原的一往情深。
我的校友王川与我同行高原多次。他在《从断壁残垣荒坟石碑中追寻藏地的民间神灵》一文中讲述了我们去噶玛寺时他第一次骑马的故事:“1996年春季,我因周大鸣教授的介绍,参加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研究员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藏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昌都县噶玛乡的宽广草地上,我在奔腾的马背上,一边快走踏清秋,一边听格勒博士讲述活佛转世制度创建者——都松钦巴的传说故事,天空中飘荡着这位康巴汉子的豪迈笑声;在噶玛噶举派的祖寺——噶玛寺,我们不仅认真考察了寺庙的结构,还激动地观摩了明代中原出产的瓷器、带有长篇文字的锦缎以及寺庙的其他宝物,分明看到了入藏的宦官侯显一行的身影……”是啊,我们是幸运的朝拜者和研究者,因为这座著名的寺庙如今因火灾焚毁。它独特的原貌永远留在我们的照片中和记忆里。
《意树心花》中不少作者最刻骨铭心的故事就是第一次进藏。徐平与我多次进藏一路同行,可他最忘不了的是第一个田野点西藏达孜区邦堆乡罗吉林村。他本着“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田野调查传统,住在多布吉家里。他说:“多布吉夫人是一位结实的中年妇女,温柔少语,总是带着一脸微笑……她每天会给我烧一壶新挤的牛奶,不断地添加到茶杯里。刚开始的时候,我怕拂了她的好意,她倒一次我喝一次,我喝一次她立即再添满,无论是酥油茶还是鲜牛奶。我长期吃草的胃终于受不了了,上吐下泻,带去的黄连素、痢特灵都吃完,也不见好转,几天就让我起不了床。多布吉从墙缝里抠出一个纸包,拿出几粒羊粪蛋似的藏药,建议我试一下。一吃就灵,我才过了田野调查必过的水土关,也开始理解藏族文化的独特和深厚。”我们学者的高原故事中类似的故事不可胜数,因高原反应而肺气肿、因翻车而死里逃生,各种险境一个接着一个。但我们进藏的初心永远不变,我们对“第三极”的高天厚土依然一往情深。
杰出的学术创造者又恰恰大多经历过无数磨难和逆境,这种现象似乎是冥冥之中的有意安排,《意树心花》的作者中不乏著作等身之辈,令我们敬佩。但我更敬佩有的作者在高原故事中遇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学术探索阻碍时,依然坦然面对、坚持不懈,获得成功。长期潜心研究的学者喜饶尼玛,我们常见面,最熟悉不过了。但他在《那年,我们初涉调研》中所遭遇的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但我们在田野考察途中深夜被从床上叫醒检查身份和介绍信的故事确实亲身经历过。喜饶尼玛说:“多年以后,学人聚会。一位学者听我谈起那次甘孜遭遇,竟笑了起说,原来是你们呀,当时都不信有这样的事!”既然是田野考察,为了获得意想不到的第一手学科资料,类似遭遇是否自然而然,是否不可避免?但我相信尼玛他们“在益西寺见到了一幅珍品,是民国初年中央政府给该寺住持的嘉奖令”时一定心里高兴、喜笑颜开。这也符合天地间“相辅相成”的千古不变的道理吧。正所谓“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是比在珠宝店橱窗内看见一粒大珍珠更为快活”。
六十六位文化学者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在序言中只能引用一小部分,我认为有一定代表性的故事段落或语句。实际上《意树心花》的不少作者,尤其是年轻文化学者所描述的高原故事的灵魂与我同在,我们之间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所以当我结束这篇序言时,向辛勤编辑的两位年轻人和出版这部文集的单位以及所有走过高原的文化学者们致敬、点赞。
2022年3月 27日
于成都高攀路阳光春天
图书购买链接: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