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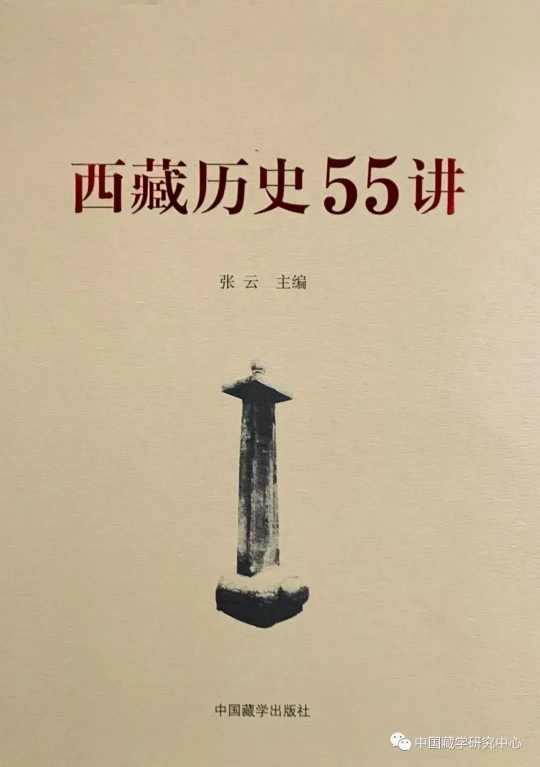
第43讲 九世班禅被迫出走内地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属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他们的转世灵童需按宗教仪轨,认比自己年长、学问高深、受了比丘戒的对方或其他高僧为师,为的是剃度、取法名和受戒等。多年来,他们都是互助互谅,和衷共济。
一、英人挑拨,矛盾日显
但自清末以来,由于英人从中挑拨,其下属官员为争个人权势而人为制造矛盾,两人渐生隔阂。1919年进藏的甘肃代表团成员朱绣曾谈及,光绪二十八年春,班禅去拉萨朝拜师父时,其属下在布达拉宫前击鼓而过。达赖喇嘛因此十分恼火,斥其过师门而击鼓,妄自尊大,遂罚银1500两。自此,其左右互相谗构,嫌隙日深。但据史料记载,矛盾似乎发生得更早一些。如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在给清光绪帝的奏折中,就曾提到“后藏班禅素与达赖不睦”。
实际上,达赖喇嘛、班禅间的关系恶化与英人的挑拨是分不开的,早在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期间,英帝分子便大力拉拢九世班禅,企图使他成为其控制西藏的代理人。1905年,当时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鄂康诺(O’Connor.)前往日喀则要求九世班禅到印度加尔各答会见英王储,“实密谋废达赖图藏”。九世班禅虽被迫前往,但英人“始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而此事在达赖喇嘛方面引起极大猜疑。1906年,英人贝尔又至扎什伦布寺,停留约两月,显然是为了拉拢九世班禅,他很清楚“拉萨与扎什伦布寺之间,妒忌甚深”,因而不遗余力。以后,他见九世班禅内向之心颇坚,便又加紧与达赖喇嘛联系,竭尽挑拨拉拢之能事,这是后话。
1910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因出走印度,清廷废其名号,拟由九世班禅取而代之,暂摄藏政。班禅对此婉言拒绝,但因后来未随十三世达赖喇嘛去印度,反而受驻藏大臣所请,到拉萨主持了藏历新年仪式,遂使噶厦在印度的官员大为不满。至1912年,川军与藏军发生激战,钟颖抵敌不住,求援于九世班禅。九世班禅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此举自然不满,于是“后藏僧民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九世班禅还“暗令哲蚌寺僧助之”。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即开始清除异己,首先惩办帮助过川军的僧俗官员,对九世班禅的内向之举,也嫉恨在心,双方关系更趋恶化。
这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听信英人挑唆,极力扩大藏军,大打内战,与川军作战耗资巨大。因此,为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等诸多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实施“新政”。噶厦即以此为由,向扎什伦布寺发布通知“在抗尼、抗英、反清战事中,即军粮、军饷全是噶厦支出。目前噶厦钱粮两缺,因此,扎什伦布寺方面应按孜康列空原规定承担全藏军饷总额的四分之一;另据后藏十三宗向噶厦呈文,愿承担向噶厦政府支派骡马、差役的要求。请扎什伦布寺拉章即派代表前来噶厦协商”。这从其所辖土地、人口、收入等方面看是很不合理的,显然侵犯了九世班禅的固有权利和地位。按清代成例,达赖、班禅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平等的,都归清朝驻藏大臣节制,在民众中也有“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之说。九世班禅对此自然不能接受。
1915年,西藏地方政府在日喀则地区设立基宗(相当于地区行署),僧官罗桑团柱、俗官穆霞两人担任基宗,其职责除管理在后藏的宗谿外,还要管辖班禅所属的4个宗和所有谿卡。
1915年6月,九世班禅致信十三世达赖喇嘛,一方面申诉扎什伦布寺的痛苦,另一方面希望去拉萨与达赖喇嘛面谈。达赖喇嘛在回信中虽然同意面谈,但提议推迟至翌年。而后,达赖喇嘛却宣布“闭关坐静”,婉拒晤面。但1917年,西藏地方政府颁布的《火蛇年法令》却不顾历代达赖喇嘛给予扎什伦布寺的特权,规定江孜宗境内的扎什伦布寺所属的农奴应支应七分之一的马差,超过100匹马和300头驮畜还得征收驮畜徭役税。一直到1919年才同意九世班禅赴拉萨。他到拉萨时,达赖喇嘛只是“特邀侍卫兵十二人到东嘎迎接,并差遣堪钦一人、堪穷二人、列参巴二人、普通孜仲五人在鲁定林卡设灶郊迎”。这种与班禅地位很不相称的礼节,使人们大感诧异。达赖、班禅这次在拉萨就前后藏事宜进行了多次晤谈,但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九世班禅对此非常失望。
1921年,噶厦新设立的军粮局向扎什伦布寺征收了约3万藏克青稞和1万个银币的年附加税。1923年,噶厦所颁布的《水猪年法令》更为苛刻,竟规定扎什伦布寺的所有农奴都必须支应噶厦所派的驮畜等差役,以致扎什伦布的全体官民感到无法生存。面对这一切,九世班禅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毫无把握,“认为逃出西藏为最妥善”。他曾以去拉孜宗芒卡温泉沐浴为名,相机出走未遂。
二、被迫出走,倾心内向
1923年冬,一件突如其来的事终于促成了九世班禅的出走。当时,扎什伦布寺的几名僧官突然被唤至拉萨,无故被捕。九世班禅闻讯大惊,自觉噶厦在英人的指使下,可能加害于己,如不速走内地,性命难保。
于是,九世班禅留下一信表示,虽蒙达赖喇嘛多方关照,然而,军粮局官员没有公平合理地处理此事,反而指令扎什伦布寺拉章的属民无偿地支应运输等差役。但扎什伦布寺不可能承担提供物资供给和各项费用以满足军费开支的责任。因此,他只好暂时秘密地离开扎什伦布寺,以寻求康区和蒙古施主的帮助。
11月15日,深夜发生的一切注定是不寻常的。黯然神伤的九世班禅冒着凛冽的风雪,秘密率领堪布及身边重要僧俗人员15人,趁着夜色经纳当、岗金进入藏北羌塘“无人区”,最终前往内地,寻求中央政府的帮助。
数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闻讯,即令代本崔科率军千余人向北追赶,终未获。西藏百姓对其成功出走拍手称快,有街谣曰:“都说班禅是兀鹰,展翅飞翔去他乡,都说崔科像猎犬,空手而归嗅地面。”
九世班禅出走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令日喀则基宗彻底控制了后藏地区,以后又派来札萨喇嘛,直接过问扎什伦布寺内各项事务。自此,九世班禅所属寺庙、宗谿均由噶厦管理。
1924年4月25日,九世班禅一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甘肃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安西(今甘肃省瓜州县)。自此,他获得了内地各级官员及百姓的热烈欢迎。民国政府大总统曹锟得知九世班禅前来,遂电复甘肃兰州督军陆洪涛以前清迎六世班禅的规格接待。班禅遂在安西县长的护送下,乘八抬大轿抵兰州。督军陆洪涛率军民数千人至郊外迎接。从北京专程赶来的“迎护专员”李乃棻宣布了曹锟大总统令,授予九世班禅“致忠阐化”的封号。8月,九世班禅在民国政府官员的护送下,取道西安赴北京。其时正逢直奉军阀大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大总统曹锟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驻扎西安的民国军被直系军队紧紧包围。九世班禅一行被阻郊外,不能进城,只好派大卓尼钟苏郎与交战双方接洽,商议安全通过火线。九世班禅爱国东行之举,受到交战双方的竭诚欢迎,使九世班禅顺利进入西安城。
1924年12月29日,九世班禅在西安就停止内战问题向全国发出通电。在通电中,他列举了从民国军政部门到内外蒙古王公贵族约60个名流要人之名,表示“我国值风雨漂零之际,正危急存亡之秋,亟应速息内讧,力图上策”,希望各界人士“彻底觉悟,共保和平,免阋墙之纷争,谋根本之建设”。通电是九世班禅抵达内地后,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政治态度的宣言,他表达了自己忠心为国的思想,也在全国各族人民面前展示了一个爱国高僧的形象。
1925年2月2日,九世班禅在临时执政段祺瑞长子段宏业、蒙藏院代表图桑诺布、章嘉呼图克图等人的陪同下,乘专列抵达北京,受到数万人热烈欢迎,而后下榻于中南海瀛台。次日,班禅大师与临时执政段祺瑞会面,“报告藏务及东来使命”。段祺瑞表示“一俟国内安定,藏事当可迎刃而解”。
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外侮频仍,九世班禅冒险东来的爱国行为唤起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敬意。他无论在北京、杭州,还是在五台山,都受到僧俗各族民众的欢迎。他也尽力满足信徒朝拜之愿,并适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内地耳闻目睹的一切,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只要中国大地战乱绵延,藏事的解决就无从谈起。他于是竭尽心力,毫不气馁,大声呼吁“以博爱群生之旨,发存亡与共之言”,反对内战,反对分裂,谋求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祖国。九世班禅正是以行动把自己与国家的安危紧紧连在一起。
是月,民国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九世班禅指派代表罗桑坚赞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十三世达赖喇嘛指派的代表顿柱旺结。九世班禅在会前再次敦促各方不要因自私“酿出国内兵争,丧军民之生命,耗国家之金钱”,应“同心诚意,化出我见为基础”,“一心想中国往好处走,自然五族共助,人同此心,从此财政富足,民生安乐”。在会议期间,他还递交意见书,号召“弭止战祸,实行五族共和”。
8月1日,民国政府蒙藏院以九世班禅“远道来京,赞筹统一,精忠翊国,嘉慰良深”授其“宣诚济世”封号,并颁金册金印。与此同时,九世班禅还报经临时执政批准,在北京福佑寺设立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为罗桑坚赞。以后又在西宁、成都等地及印度成立办事处。后因北京始终处在动乱的中心,军阀混战不断,九世班禅遂应蒙古王公之邀至沈阳,并以黄寺为行辕驻地。因驻地邻近内蒙古,信教蒙古王公顶礼膜拜者甚多,九世班禅亦常至东部蒙古各地进行佛事活动,举行了数次时轮金刚法会。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九世班禅又在南京成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以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九世班禅闻讯后,悲痛万分,亲率僧人为达赖喇嘛诵经追荐。他在内地期间,为国家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无论是西边尼泊尔军犯境,还是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他都勇敢地站出来,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活动中。中央政府对他的爱国行为颇为赞赏,先后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西陲宣化使等职。以后,又被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九世班禅不顾生命危险,在内蒙古等地揭露日寇暴行,号召广大民众抗日救亡,并诵经祈祷抗战胜利。由于九世班禅在内蒙古民众中很有声望,日本人“屡次潜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内蒙古与中央分离之局面”。但是,九世班禅深明大义,爱憎分明,严词拒绝了侵略者的拉拢。难怪有人认为“九·一八国难后,日本用种种办法,勾煽其间,而内蒙古官民,屹然不为所动者,大师宣化之功也”。事实证明,这种评价并不为过。九世班禅还身体力行,多次捐款捐物。在他生命濒危之际,还为抗战捐款3万元,购公债3万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和信心。
三、回藏受阻,中道圆寂
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后,始终牵挂着家乡,曾多次向中央政府陈述回藏意见,尤其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达赖喇嘛在内地派驻办事处,与中央关系有所改善后,他的这种想法更为迫切。中央政府对九世班禅入藏一事,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很明显,爱国的九世班禅回到西藏,对维护祖国统一,必将大有禆益。1929年8月,蒋介石在接见西藏代表贡觉仲尼时,专门谈到此事。贡觉仲尼答道:达赖喇嘛愿迎班禅回藏。但噶厦则认为“至班禅左右人等,时常挑拨,现在未声明逃奔理由之前,西藏碍难欢迎”。可见,在九世班禅回藏问题上,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是很深的。
1930年,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奉命入藏宣慰,任务之一就是妥善解决班禅回藏及其政教权力问题,但他途中病逝,未能完成使命。
同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因商业税等发生冲突。尼泊尔为此进行全国总动员。九世班禅闻讯,即拟组织军队前往西藏反击侵略,同时达到回藏目的。国民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组织外交、内政、军事三部共同拟定办法。此事未等落实,康藏纠纷再起,遂停办理。
1933年,九世班禅再派安钦呼图克图和仲译钦莫王乐阶持其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取海道前往西藏,交涉返藏事宜。安钦等人抵藏后,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欢迎。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双方积怨全系属僚挑拨,表示欢迎班禅回藏,并允发还扎什伦布寺原属之拉孜、昂仁、彭措林、康巴等4宗,并从后藏撤回札萨喇嘛和新任宗本。
1933年12月17日,正当班禅回藏问题的解决出现转机之时,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
在追荐十三世达赖喇嘛事务上,九世班禅“请中央从优追封达赖,又复派其驻印、康、青各处长,揣带重金,分赴西藏各大寺,并令西康、蒙古、印度及中国北部各小寺院,诵经追荐,同时亲撰祈祷达佛灵童之经赞,分发各地寺院僧众随时诵祷”。九世班禅不计前嫌的做法再一次扩大了他在信教群众中的影响。
中央大员黄慕松赴藏致祭,与噶厦官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其中涉及如何解决班禅回藏问题。当时,西藏僧俗民众“欢迎班禅入藏的声浪甚高”。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灵童迄未寻得,“而班禅仍不回藏,是犹失去父母之孤儿”。有鉴于此,噶厦中个别人恐失民心,不得不同意班禅回藏,但提出须由海道返藏及不必中央护送。
中央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黄慕松拉萨之行沟通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直接联系;西藏地方新任摄政热振对中央十分友好;西藏民众急盼九世班禅回藏,这都说明班禅返藏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个机会十分难得。
1935年3月,九世班禅致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除陈述藏案近况,宣化步骤及建设计划外,特地提出了四点回藏计划。他表示“卫藏交涉,大体就绪,轻骑回藏,亦无不可”,但有关西藏地方的一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有负班禅来华倾诚祖国,民族共和之初志”。因此,希望政府“早定方针,以期解决,而免久悬”。他是把回藏看成了与祖国统一相连的大事,而并非个人的事。他还希望中央能在他回藏之时,“酌拨赈款,分散民间”,“开辟青康卫藏长途汽车公路”,“继在重要各县,架设电台,分置邮局。并饬各宗兴办小学,教授藏文,以养其读书习惯,再由而加授中文及科学常识,按期选派青年留学内地,以资深造”,拳拳为民之心,跃然纸上。最后,他谈到回藏路线决定取道青海,另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一、请中央简派得力大员护送回藏,此事不独关系国家观瞻,中央威权,且班禅今后之宣化建设,诸待指导,咨询有自,俾免陨越。二、请补助入藏旅费。三、请政府选派武装卫队,以策安全,而扬国威。
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217次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主要内容为:一、班禅回藏经费准拨100万元;二、准其酌带卫队官兵500;三、根据清朝惯例,由中央简派得力大员护送。
9月4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诚充为护送班禅回藏专使,组成行署,并于宪兵司令部挑选官兵组成仪仗队。班禅返藏工作随即展开。11日,后藏恩久佛及班张文纲堪布等为欢迎班禅返藏,先期到达塔尔寺。27日,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代表取道玉树来塔尔寺。不久,西藏地方政府又电告班禅,已派多仁台吉由北路至青海,务请早日动身,以慰僧俗。英帝国主义深知班禅回藏意味着什么,于是竭尽全力进行破坏。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在这方面的表现最能说明问题。11月9日,他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中国派遣军队入藏”,“违反西姆拉条约第三条”。同月27日,英使馆又提出“英国政府对于国民政府拟派仪仗队300人护送班禅喇嘛回藏事,依据西藏当局之异议,及森姆拉条约第三条之规定,表示反对”。中国政府据理力争,指出西藏当局对此事并无异议;援引未经我国政府正式签字的“西姆拉条约”,“殊不能认为适当”。
事情很清楚,问题的症结并非“仪仗队”等,而是涉及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英帝国主义动辄以代表西藏地方的利益为幌子,实际上从班禅回藏之事决定之后,西藏地方确有个别人屡予阻挠,但摄政热振、噶伦彭康及基巧堪布等对班禅经由何地回藏以及护送官兵诸事并无异议。西藏地方政府之所以坚决反对班禅带“卫队”“蒙、汉人”入藏,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帝国主义的煽惑。
正是在这一年,英国驻锡金行政官威廉逊(F. Williamson)到拉萨,在西藏上层内部活动。他一方面胁迫噶厦允其在拉萨设置常驻人员,另一方面则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阻挠九世班禅回藏。他深知西藏人民对班禅的感情,故提出西藏应该欢迎班禅回藏,但是昔日清朝官兵,曾欺压藏民,所以现在为西藏考虑,必须予以拒绝。面对英国方面的压力,中央政府态度十分坚决,仍支持班禅按既定计划入藏。
1936年4月至7月,蒙藏委员会驻藏官员蒋致余数次电告中央,英国方面曾给西藏当局去电,就班禅回藏问题,与国民政府交涉,希望西藏地方政府坚决拒绝。他还报告了噶厦少数人与英国勾结反对班禅入藏之事,建议行政院“转饬外交部设法应付,万毋堕其觳中”。
同年6月,九世班禅率队进至拉卜楞,举行了第九次时轮金刚大法会。翌日即前往玉树。此时,英国人也加紧了活动。8月,英国驻锡金行政官古德又到拉萨,强行设立代表处及电台,以“报告在班禅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古德的随行人员中还有印度东方司令部的旅长,据说是要在军事上向西藏地方当局“提供有用的咨议”。不久,英国即向西藏出售包括大炮在内的军火,使噶厦的底气更足了。
在英国人的蛊惑下,西藏地方即在多种场合提出,欢迎九世班禅入藏,但不得派仪仗队而由藏方派兵至西藏界迎接。蒙藏委员会通过护送专使就此向西藏噶厦作了耐心的解释,指出:
班禅为维护尊严,保护安全,应带所需要卫队,黄慕松前在拉萨,曾与西藏当局约定。
中央对西藏佛教领袖派专使及仪仗队护送,已有成例。
班禅回藏为全藏人民所渴望,如中央不派专使及仪仗队为之护送,不仅不能表示中央推崇佛教之真诚,且班禅也会招募卫队,以壮观瞻。
班禅回藏之必须保障,事属当然。如噶厦忽略实际情形,既不希望中央派员护送,又不允班禅自行带兵,则不独无以慰西藏人民渴望之殷,复逼班禅久住边界,将来西藏局势变化如何,实不可预料。
班禅最初要求卫队人数甚多,今准派300人,对西藏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央用意,一方面为维护班禅在佛教上之尊严,一方面也为维持颇安定之西藏现况。热振活佛等爱国人士对班禅入藏的态度是明朗的,尤其得到护送专使解释仪仗队进藏缘由的电文后,当即回电,表示欢迎。电文说:“……班禅大师回藏实为佛教众生之无上幸福,前此藏方群众,对护送官兵入藏与藏中政教利害关系,不无疑虑。慈承来电解释,诚意说明,自当遵嘱极力开导,转令知照。以后情形,当再电告。惟望贵处福利佛教众生,设法敦促班禅大师迅速入藏,至所盼祷……”但由于热振活佛较年轻,不敌噶厦中少数权位较高之人,而这些人一意孤行,唯恐班禅回藏,爱国力量得到增强,危及其既得利益。当然也有个别对班禅出走内地负有直接责任者,害怕遭到报复。于是,随着九世班禅西进的脚步,这场纷争也愈演愈烈,而主角之一竟是英国人。
这期间,英驻华公使屡屡就班禅回藏问题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并威胁说,如果卫队入藏,“藏兵必将抵抗”。令人尤为奇怪的是,大洋彼岸的英国政府所提异议,仅1936年12月就有好几次,竟远远超过了西藏地方政府。中国外交部根据种种迹象,断定西藏局势有可能恶化,即向行政院报告。12月15日,中国政府郑重向英方提出:
中国西藏事务乃内政问题,毋庸英国代为建议。
中国政府正在设法促进班禅与拉萨间,为和平回藏商洽,决不致引起西藏之不安。
英国方面接到答复后,仍不死心,继续活动。而与此同时,班禅西行人马逐渐靠近西藏,于12月18日抵达青海玉树,“军民数千,冒雪欢迎”。
班禅大师到达玉树后,与西藏地方当局派来的代表进一步商洽,亲自致函索康,说明中央派遣专使及仪仗队,系援照旧例,尊崇佛教,并无他意,希望解除疑惑,使入藏前途臻于顺利。但是,西藏地方当局又节外生枝,提出卫队经黑河到后藏,5个月内必须全部撤回,后藏赋税仍归前藏征收,同时还说明如在问题未解决前入藏,当以武力拒之。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院批准蒙藏委员会根据班禅意见拟定的办法,即“仪仗队护送班禅到达后,即行撤回”,但英国方面竟视之为软弱,更加明目张胆地干涉我国内政。
英驻华公使多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英方对九世班禅入藏带仪仗队,不能同意”,要中国政府不再坚持派官员和仪仗队入藏。
1937年8月18日,九世班禅离开玉树,西进至离西藏更近之拉休寺。
众所周知,此时的中国大地正在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较量,抗日呼声响彻全国。中国政府须集中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更重要的则是,蒋介石正在依赖英美等西方国家提供各种援助,岂敢因“西藏问题”开罪英国,因此,支持班禅回藏的态度有了转变。
19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三二五次会议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除电饬赵专使守钰转告,并函达军事委员会及重庆行营查照,及令行外交部外,合行令仰知照。此令”。对此,蒙藏委员会的说明是“抗战期间,中英关系,必须顾虑,仪仗队入藏,恐起纠纷。班禅如必入藏,则须俟藏方有确实回音,且派队到境相接,一切妥善后,方可决定”。可见,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进藏的意见,确有华北战火已燃,一旦西陲再起衅端,进而影响盟国关系之虑。
深明大义的九世班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震惊之余,不无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班禅决不舍中央官兵入藏,亦不顾入藏后受藏政府限制而疏远中央”,并电中央表示服从。但是,出走内地14年,现在已到了家门口,九世班禅的属下不忍就此罢休,乃于9月1日再次与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代表磋商,并作了较大让步,如同意仪仗队官兵到藏休息5月后即行撤退等。可是噶厦中少数人的真正目的是阻挠倾心内向的班禅大师回藏,因此条件更趋苛刻。9月25日,噶厦回电除再次缩短仪仗队在藏休息时间为两月外,还要求原道撤回,并提出行辕及仪仗队到藏后,须服从前藏政府命令。九世班禅接电后,立即向中央表明态度,“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不愿中央威信陷于隳堕,即遵院令,暂缓西行,以待将来”。同时提出住地、经费及将来入藏保障等三项要求,随即于10月8日离开拉休寺,12日重返玉树。
班禅大师十余年的夙愿,化作了一场梦。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加之肝病突发,11月初,他粒米难进,每食即吐,夜不能寐,终因医治无效,于1937年12月1日2时25分,圆寂于青海玉树寺甲拉颇章宫内,享年53岁。在抗日战争枪炮声中,九世班禅的遗嘱留在了历史记忆之中:
余生平所发宏愿,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近十五年来,遍游内地,渥蒙中央优遇,得见中央确对佛教尊崇,对藏族平等,余心滋慰,余念益坚,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拟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途圆寂,今有数事切嘱如下:……至宣化使署枪支,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予中央,共济国难,俟余转生,再请发还。又关于历代班禅所享权利,应早图恢复,最后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汉藏和好,札萨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此嘱。
中央政府得知九世班禅圆寂的消息后,尽管抗战军务紧急,仍立即发布追赠九世班禅的封号令,充分肯定了他“早岁翊赞统一”“懋著功勋”,“特令褒扬,追赠‘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封号,并着给治丧费一万元,特派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前往康定致祭,用示国家笃念殊勋之一至意”。同月25日,班禅大师灵柩被移至甘孜。
1938年8月5日,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为专使的致祭人员60余人到达甘孜。8日,举行了隆重的致祭九世班禅典礼。
从1923年离藏入中原,到在青海玉树圆寂,近15年的内地漂泊,九世班禅为“陈述藏情,倾心祖国”,出走内地,度过动荡的生活。这期间,他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辛勤奔波。他无时不在思念着西藏的土地和人民,眼看就要实现夙愿,却“壮志未酬身先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便是当时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能够为所欲为。正是在英国人的指使和操纵下,噶厦少数人才敢阻班禅大师返藏。只有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他才可能回归故里。历史对此作了最好的说明。
有学者指出,九世班禅在内地的爱国行动“客观上使噶厦不能在‘非爱国主义’之路上走得太远,在国家处于动荡衰微之时,西藏地方即使有帝国主义势力的怂恿与支持,仍然基本维系着与中央的联系,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较为顺利地解决西藏地方长期与中央不正常关系,其作用显而易见。这是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此而言,班禅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
从九世班禅在内地近15年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在国民政府时期,这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始终以坚如磐石的意志将护国佑民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指南。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