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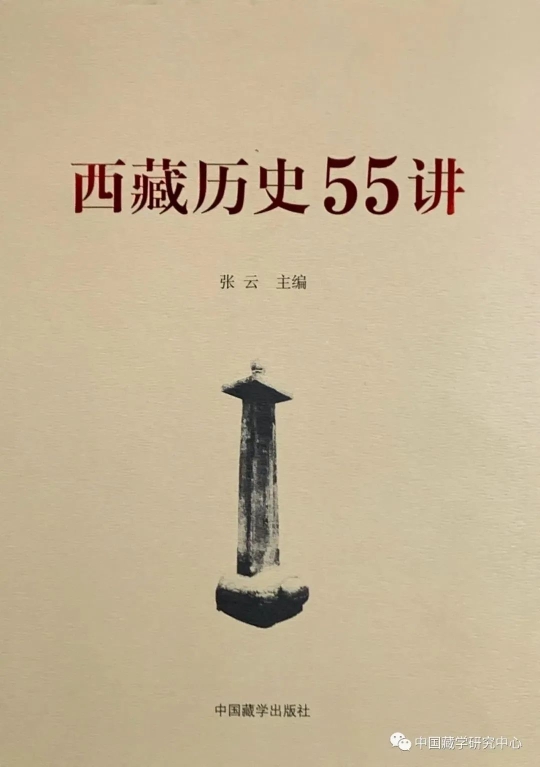
第42讲 1919—1920年甘肃代表团入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一再催促民国政府交涉藏边划界等问题。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全国范围内形成反对出卖国家领土和权益的爱国热潮和舆论压力,迫使民国政府拒绝英国续议藏约的要求,谋求与西藏地方改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9月,甘肃代表团由青海湟源启程,于1920年1月抵达拉萨,成为民国时期首个公开入藏的内地代表团。甘肃代表团抵达西藏后,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及西藏僧俗各界广泛接触,了解各方政治态度,为沟通汉藏关系,维持边藏和平作出了贡献。这是民国时期西北边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一、历史背景
民国初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疏远。民国政府曾多次派员入藏联络,都受到英国方面的阻挠和干涉。英国以承认中华民国及支持袁世凯政权为条件,逼迫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议”。在随后举行的西姆拉会议(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上,英国提出划分所谓“内外藏”的“西姆拉条约”,试图取消中国在藏之主权,民国政府拒绝签署条约。会议以破裂告终,“西姆拉条约”无效。
1914年后,中英有关藏事的交涉一度搁置不议。由于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一方面以西姆拉会议以来取得的在西藏的权益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而有恃无恐;另一方面,也因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无暇顾及;而民国政府也由于“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护法运动等政潮接连不息,无暇与英国续议藏约。
(一)《绒坝岔停战协定》与英国催议藏案
1917年7月,第二次康藏战争爆发。当时,正是川边各军阀势力激烈混战之时,又有英印政府怂恿支持,藏军步步推进,川军接连败退。在藏军大致占领了“西姆拉条约”规定的所谓“内、外藏界限”时,英国驻华公使馆官员台克满(E. Teichman)赶赴昌都等地,从中“调停”。最终于1918年10月签订《绒坝岔停战协定》,规定汉军退至甘孜,藏军退至德格,停战一年。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方随即不断催促中国续议藏案。
1919年5月,英国驻华公使馆正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绒坝岔停战协定》即将期满,边界地区又将爆发冲突,要求尽快开议藏约,并请中国提出解决条件。民国政府认为,若拒绝英使提议,英方可能再次唆使藏军东进,川边军备空虚,恐难抵挡。同年5月30日,民国政府根据1915年6月袁世凯主政时期提出的关于“内、外藏界限”的最后妥协方案,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 N. Jordan)声明四项解决办法。8月13日,朱尔典又向中方提出两种调停办法,均要求德格划归西藏,昆仑山以南、当拉岭(唐古拉山)以北之地划归内藏或中央不设官不驻兵。
(二)民国政府公布藏案交涉情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经济严重衰退,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俄国也由于十月革命爆发,导致沙皇政权崩溃。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影响“西藏问题”解决的两个大国都受到一战的影响,客观上,为民国中央政府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1919年,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国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反对出卖国家领土和权益的爱国热潮及舆论压力,迫使民国政府不敢出卖国家利益。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民国政府决定通电全国,公布藏案交涉情形,征询相关各方意见,暂缓与英国开议藏约。
1919年9月5日,民国政府外交部通电毗连西藏各省地方,公布1913年西姆拉会议以来中英有关藏事交涉的部分内容。因当时中国邮电使用韵目代日法,5日代日韵目为“歌”字,所以,民国政府发出的这份电文称为“九五歌电”。“歌电”一经发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川、滇、甘、青等地纷纷通电谴责,学生组织示威游行、通电抗议。
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通过甘肃督军张广建代转电,明确指出:中英续议藏约之界限“是举青海大半部、玉树二十五族纵横数千里之地,一朝而弃其主权。始虽废为瓯脱,终必被人占领,较之前清时代抛弃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者,其损失之巨大,有过之无不及”。马麒坚决反对中英有关西藏界务的交涉,指明其严重损害领土主权:
西藏本中国属土,年来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涉。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认,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
川滇黔陕四省协会也通电全国,呼吁“际此一发千钧,尚望联络一致,急起直追,严密监视政府对藏之行动,勿许断送”。远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也强烈反对英方提出之划界办法。留日学生通电全国,指出:“英使所提之划界办法,将云南、四川、甘肃、新疆各边界万余里之地,要求划归西藏范围,完全撤销西南屏障,此事关系吾国存亡,万不可轻为让步,以造将来无穷之巨祸。”可见,这一时期,全国上下及海内外各界都强烈反对中英有关藏事的交涉。
二、为何由甘肃派代表团入藏联络?
早在1919年4月,民国政府部分人士已联名报告,提出民国以来汉藏双方缺少接触,隔阂日深,欲解决藏事,还是以派员入藏“联络感情”,乘机与达赖喇嘛直接商洽,最为上策。说明这一时期民国政府内已有派员赴藏联络的意向。与此同时,对于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和甘肃督军张广建而言,《绒坝岔停战协定》即将到期,川藏边界局势再度紧张,青藏边界能否保持稳定?面对英人一再催议藏约,中央是否会忽略甘青地方的利益,同意将玉树地区划归内藏,退兵撤官?这些都成为马麒、张广建等甘青地区实力派人物最关切的问题。
此外,就入藏道路而言,英国以“藏约未议结期内,中国不能由印与藏交通”,故由印入藏一道受阻于英印政府;川藏道此时仍是两军对峙的状态。因此,由甘青方面派员入藏已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
据史料记载,1919年春,在民国政府尚未发布“九五歌电”,通报与英交涉藏案情形前,甘肃方面已经有派员入藏的打算。5月底、6月初,甘肃督军张广建召请著名宁玛派活佛古浪仓(dgu-rong-tshang)和玉树格鲁派活佛拉布坚贡(lab-skyabs-mgon,意为拉布寺怙主,也作“拉布尖贡”)等赴兰州会面,商议入藏事宜。最终选定四位赴藏代表,即甘肃督军公署咨议(也称参议)李仲莲、参事朱绣,及甘青地方的著名藏传佛教僧人古浪仓活佛和拉布坚贡,携带张广建、马麒致达赖喇嘛和班禅等西藏僧俗上层的信函礼物入藏。张广建随即向总统报告了相关情况。
三、甘肃代表团人员组成
甘肃代表团主要由两名政府官员(李仲莲、朱绣)和两名藏传佛教僧人(古浪仓、拉布坚贡)组成。这样的人员构成,主要是考虑到古浪仓和拉布坚贡精通藏语文,且与达赖喇嘛的堪布是旧交,而李仲莲和朱绣两位明白事理、通晓边疆情形,四人同行,可相互扶助、相机应对。当然,这样的人员构成应该也是考虑到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及政府中僧俗官员并立等情况而作出的安排。
李仲莲,字亚青,时任甘肃督军公署咨议。
朱绣(1884—1928),字锦屏,青海湟源人。幼年时就读于湟源名儒、纂修《丹噶尔厅志》的杨景升先生开办的私塾。后因家道中落,到西宁乾泰茂商行做学徒。他是一个很有志向、关心边事的青年,在商行当店员做学徒期间,就订购《申报》等新式报刊,对国内外大事颇有见解。与时任西宁道尹黎丹相识后,成为道尹公府随员。1915—1916年,朱绣以西宁道属参议会议员身份,赴兰州、洛阳、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参观考察。归后不久,执教于宁海蒙番学堂,与周希武等合力革新学制,改定学校教程,为青海地方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1919年,黎丹以朱绣“素怀经营边陲之愿望,且能言善辩,可为出使之材”,遂保荐其为代表受派入藏。1920年,由藏归来,马麒升任他为镇守使署顾问。著有《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海藏纪行》和《拉萨见闻录》等。1925年,朱绣再次作为马麒的代表赴京,参加段祺瑞主持的“善后会议”。会后,他前往江苏南通参观,颇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影响。为振兴实业,他还担任青海垦务局会办,积极推广垦务。为振兴西北,发起“西北问题研究会”。1928年,朱绣、周希武等人计划前往兰州,接洽国民军入青事宜。7月25日,从西宁出发,行至老鸦峡莲花台时,遭遇伏击,中弹身亡。
古浪仓(1875—1932),全名乌坚久哲曲英多吉(o-rgan-vjigs-bral-chos-dbyings-rdo-rje),出生于青海古浪堤地方(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为尖扎南宗寺(gnam-rdzong-dgon-pa)三世古浪仓活佛。青年时曾赴宁玛派名寺尕多寺(ka-thog-dgon,也作嘎托寺)和佐钦寺(rdzogs-chen-dgon-pa,也作竹庆寺)学习。火蛇年(1917),前往五台山朝拜,后又赴北京游历。其间,曾与总统黎元洪、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七世章嘉活佛等会面,受总统封赐“宁海红教总佛长”名号及印信,印文直译为“西宁青海等地宁玛派政教总主古浪仓达喇嘛之印”(ziling-mtsho-sngon-sogs-kyi-snga-vgyor-rnying-mavi-chos-srid-spyi-bdag-chen-po-dgu-rong-tā-bla-mari-tham-ka),回到青海后,曾建立药房,设立小型工坊,制造唐卡、地毯等。1919—1920年,受派赴藏联络。协助黎丹创办西宁藏文研究社,编纂《藏汉大辞典》,对藏汉文化交流贡献良多;又曾兴办藏族小学,为开启青海现代民族教育作出贡献。古浪仓精通藏族传统天文历算和医药,还积极钻研沼气发电、电镀金银等现代技术,是“青海藏传佛教中最早的开明人士之一”。水猴年(1932)八月四日圆寂。
拉布坚贡(1889—1944),全名江永洛桑嘉措(vjam-dbyang-blo-bzang-rga-mtsho),青海玉树拉布寺(lab-dgon-pa)寺主活佛代玛堪钦元登巴系统第十三世活佛。拉布寺是玉树地区格鲁派主要寺院之一,位于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拉布乡。明朝永乐年间,宗喀巴弟子代玛堪钦元登巴奉师命到称多拉布地方弘传格鲁派教法。在当地拉布头人尼玛本的协助下,于明永乐十六年(1419)改原有萨迦派小寺为格鲁派,名为拉布寺。寺院初建,即受到宗喀巴和明朝的支持。随后,代玛堪钦积极活动,在青海玉树、四川石渠等地兴建、改宗了一系列寺院。代玛堪钦受到蒙藏群众信奉,被尊称为拉布坚贡。清同治十二年(1873),清廷赐名“普济寺”,由西宁办事大臣锡英制匾颁送,悬于寺内。至此,拉布寺进入全盛时期,辖子寺十八座。民国时期,十三世拉布坚贡江永洛桑嘉措曾协助黎丹创办西宁藏文研究社,编纂《藏汉大辞典》,为藏汉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又前往北京等地游历,回到拉布寺后,着手整治拉布地方河道,规划道路和居民建筑,扩建经院;创办商号,发展商业,成为当时玉树颇有影响的人物。
四、赴藏途程
1919年6月,古浪仓和拉布坚贡与甘肃督军张广建会面后,由兰州返回各自寺院做入藏准备。9月下旬,甘肃代表团李仲莲、朱绣等由湟源启程赴藏。地方各界对此次派员入藏,沟通汉藏关系寄予厚望。一位友人特意作诗赠予朱绣,诗中写道:“从此重连同种谊,家家都立共和旗。”
朱绣将赴藏途中日记结集成册,名曰《海藏纪行》,详细记述了自青海湟源至西藏拉萨的路程、山川形势、史地沿革及所见所闻,是研究甘肃代表团入藏行程的可靠资料。而藏文《历代古浪仓传》(dgu-rong-sku-phreng-sng-pyivi-rnam-thar)中也包括了此次赴藏的三世古浪仓活佛的赴藏日记等资料。将这两种汉、藏文资料相互印证,就能比较清楚地了解甘肃代表团入藏的途程、见闻等情形。
据《海藏纪行》所记,民国八年阴历闰七月二十九日(1919年9月22日),李仲莲、朱绣等由湟源县启程,逾日月山、渡黄河,翻越巴颜喀拉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4日)抵达拉布寺,与古浪仓和拉布坚贡汇合。
甘肃代表团四位代表齐聚拉布寺,在此处休整数日。此时,恰逢结古地方霍巴商人罢市出境,大起风潮。驻防玉树支队副司令马玉山和玉树理事员苟萃珍派人前来,请李仲莲和朱绣等赶赴结古,调解处理。这里所说的霍巴实际是指来自甘孜、章谷、炉霍、朱倭、白利等地的民众。明朝末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征服喀木(康区)后,征收这一区域的赋税以养青海蒙古。所以,处于青海蒙古直接管辖下的甘孜、章谷、炉霍、朱倭、白利等地,被称为霍尔五部,该地的藏族等民众称为霍巴。
(一)调解处理结古霍巴商人罢市出境风波
九月初一日(10月24日),代表团一行由拉布出发。初二日(10月25日),抵达结古。玉树毗连川藏,为青海西南门户,结古则是玉树二十五族商业荟萃之地。结古居民300余户,其中霍巴商人家庭90余户,主要从事川青藏间的贸易;其余多是贫民穷户,受雇于霍巴家庭做用人。玉树所产羊毛、皮张、虫草等,由霍巴商人运到炉城(康定)售卖,购回川茶等物资。当地的主要日用品,如牛羊肉、酥油、柴草、牛粪等,多为霍巴家庭消费。此时,霍巴商人以税率过重等缘由,罢市出境。这意味着200多户贫民将失去生活来源,地方当局将失去税源,一时市面萧条,人心惶恐。
为解决霍巴商人罢市问题,代表团邀集40余名霍巴商人协商解决办法。霍巴商人历数苦况,要求减轻税率。经过半月余的磋商调解,几经周折,终于议定:川茶入境,每百牛驮减征15驮,二十五族出产之羊毛、虫草等物,只征税于买或卖一方,不得两方皆征。罢市风波平息后,霍巴商人仍旧贸易,贫民免于困苦。甘肃代表团赴藏途中调解结古霍巴商人罢市出境风波,“结古男妇老幼,感激委员之德”;朱绣还在此处感叹道:“结古诸物价昂……惟洋货颇贱,足见英人通商势力矣!”
停留结古期间,甘肃代表团了解到川边一带谣言丛生,有的说甘肃派宁玛派喇嘛古浪仓率兵攻打西藏,又说西藏派兵防堵,不准特派员入藏。以致囊谦(nang-chen)一带民心惊惶,大有拔帐避兵之势。为此,代表团分别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和驻守昌都的噶伦喇嘛强巴丹达强巴丹达,(byam-pa-bstan-dar),详细说明代表团来藏情形,以免误会。此时英国驻华公使馆官员、驻打箭炉特别助理(Special Assistant)路易斯·金(Louis King)正在川藏边界地区游历,他试图说服噶伦喇嘛在甘肃代表团最终抵达西藏边界前加以阻拦。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他命令噶伦喇嘛允许代表团成员入藏。
(二)入藏途中风波不断
结古风波平息后,九月二十一日(11月13日)拉布坚贡回拉布寺准备行李物品,计划几日后再与朱绣等会合。可是,九月二十六日(11月18日),就传来了拉布坚贡的80驮行李物品在途中被果洛部落抢劫一空的消息。此时,已入天寒昼短之秋,代表团决定不再稽延,继续前行。拉布坚贡因途中遭劫,未能同行。
代表团原计划于九月二十二日(11月14日)由结古出发。出发前,又发生了古浪仓活佛的随从与驻玉树支队司令的属下斗殴的风波。驻玉司令部下令撤回乌拉,古浪仓活佛遂以自备的牦牛驮运启程。而朱绣等人则处于无驮载之牛的窘境,发出了“平地风波,变生意外”,“哀我旅行,其何以堪”的感慨。
九月二十七日(11月19日),李、朱等人得由结古启程,当晚抵达扎西松多地方,就收到了马玉山副司令派人送来的汉藏文信函各一封。汉文信函为马玉山所写,转达了昌都噶伦喇嘛强巴丹达欢迎代表团,但需请示达赖喇嘛后,始可入境之事。藏文信函为噶伦喇嘛原信。其意即令代表团暂不前进,等候确信。但朱绣等认为,既已启程,断无候信之理,遂决定继续前行。
十月初三日(11月24日),古浪仓与朱、李等再次会合,一路同行。由于该代表团是一个相对松散的临时组织,途中难免出现意见不一、步调不协调的情况。十一月初五日(12月26日),古浪仓提出,欲亲赴昌都,与噶伦喇嘛当面磋商意见,但朱绣认为,此次入藏应当以联络感情为宗旨,适值川边多事,而英人路易斯·金又抵昌都,若亲往昌都,难免另生枝节。古浪仓亲赴昌都一事被劝中止,但他仍暗派随从人员前往昌都。
此时已近初冬,过雪山,涉大河,风餐露宿,途中艰辛非同寻常。朱绣在《海藏纪行》中记道,“日行于无人之境,犯瘴疠而逐水草,寒风如刀,刺面有血,侵骨欲僵”,“狼啸之声,近于帐侧”,“消冰煮茶,景况凄凉”。
高原上行路已难,偶尔出现匪徒劫掠,更令入藏之行困苦倍添。朱绣记道:“初九日,阴。早五时,由羊肠沟中启程,向西行,过大牙壑。风雪骤至,寒若严冬。忽枪声隆隆,果洛番廿余人由山谷驰马而来,直行掳掠,卫兵即开枪击之,贼见人众,未敢向前,旋被卫兵射击,始败退于山巅……由此冒雪行,过色麻尕牙滩,无草无水,只有野葱可食……是晚,风雪不止,寒气袭人。”
(三)途遇达赖喇嘛派驻湟源代表
一路风雪颠簸后,甘肃代表团行抵青藏边界。1916年起,西藏地方政府在藏北三十九族地方设立“霍尔总管”(hor-spyi),由堪穷扎巴朗杰担任,负责征税、执法及行政事务。得知甘肃代表团即将到达西藏地界,霍尔总管派一个名叫却结的头人前来迎接。头人声称,此前收到达赖喇嘛下达的命令,“甘肃派来委员四人,随带跟人五十余名,至三十九族境时,沿途供给乌拉,妥为护送”。朱绣不禁感叹:“天气严寒,沿途无草,以致〔马〕瘦如柴,将有倒毙之势,正处于困难之境,忽蒙达赖优待,不独为余之幸,亦国家之光也。”
随后,代表团随同前来迎接的地方头人,于十月二十八日(12月19日)翻越当拉岭(唐古拉山),进入西藏地界。行经三十九族地方、巴欠(sbra-chen,巴青),于十一月十日(12月31日),抵达俄曲卡(nag-chu-kha,那曲)。这里是青藏交通要冲,西藏地方政府在此设有僧俗官员各一名,管理达木蒙古三十九族,征收税务,盘查往来行旅。
次日是1920年元旦,朱绣在《海藏纪行》中记道:“今日为〔民国〕九年元月一日,与俄曲堪布及昂索,并派驻湟源之贡麻尕琫会晤,详谈西藏各事。”这里所说的俄曲堪布(mkhan-po)和昂索(nang-so)是噶厦派驻那曲的僧俗官员,那么“派驻湟源之贡麻尕琫”又是何人?古浪仓日记为此提供了重要信息:skyabs-mgon-rgyal-bavi-dbang-bovi-tshong-dpon-sgo-mang-sgar-dpon可译为“达赖喇嘛的商官、(哲蚌寺)果莽扎仓的商队首领”“贡麻”是果莽的异译,“尕琫”则是商队首领噶尔琫(sgar-dpon)的异译。
结合汉、藏文资料可知,这位“派驻湟源之贡麻尕琫”就是4个月后抵达西宁的噶尔琫洛桑更登(blo-bzang-dge-vdun)。他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驻青海湟源地方,负责贸易、联络事宜的西藏官员。他原本计划前往兰州,呈送达赖喇嘛致甘肃督军的信函礼物。因抵达湟源后水土不服,未能亲赴兰州,遂将礼物信函托由马麒派人送达。达赖喇嘛在信函中还明确提出:“洛桑更登是渠心服〔腹〕,遇事可靠,如有机密要件,不妨告知,必能达到目的,嗣后关于藏内一切事件,仍望始终维持,以飨倾向之念,但藏地要情,千万勿令外人窥知,免生他患。”由此看来,这位噶尔琫不仅是负责贸易事务的商官,也肩负着一定的政治使命。而且,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也有意与马麒、张广建等甘青地方实权人物建立直接联系,只是由于忌惮英国的干涉,因而,派出洛桑更登以贸易代表名义派驻甘青,实则兼负政治职能。
朱绣、古浪仓等人随后途经彭多宗(phod-mdo,旁多谿)、热振寺(rwa-sgreng-dgon-pa)、伦珠宗(lhung-grub-rdzong,林周宗)等地,于十一月二十三日(1920年1月13日)抵达浪荡宗(glang-thang,朗塘谿,今林周县朗唐)。
朱绣记道:“廿四日,晴。乌拉未齐,在浪荡宗休息一日。”“廿五日,晴。早六时,由浪荡宗起程……六十里抵拉萨大招之南,住于柏林公寓。”据《海藏纪行》和《古浪仓传》所记,甘肃代表团的三位主要成员李仲莲、朱绣和古浪仓活佛于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1920年1月15日抵达拉萨。而另一位成员拉布坚贡由于赴藏途中遭土匪抢劫不得已暂时返回寺院,随后于藏历十二月六日才抵达拉萨。
五、在藏情形
甘肃代表团抵达拉萨时,西藏地方政府依例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古浪仓活佛在日记中记道:地方政府的僧俗公职人员前来迎接,包括司伦雪康(srid-blon-zhol-khang),擦绒、赤门、贡桑孜三位噶伦等高级僧俗官员,以及拉然巴格西喜饶嘉措为代表的哲蚌寺鲁崩康参僧众等前来致敬献礼。
甘肃代表团首先朝拜了大、小昭寺等名胜。随后,西藏地方政府安排的驻江孜商务总管、僧官堪穷洛桑迥乃(rgyang-rtse-rtse-drong-lo-tsā-mkhan-chung-blo-bzang-byung-gnas)和格西喜饶嘉措向代表团成员介绍了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礼仪。按照惯例,来访者只有得到达赖喇嘛接见后,才能拜会西藏地方的其他僧俗人士。抵达拉萨十天后,甘肃代表团的三位成员首次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见面。
藏历十二月五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接见了甘肃代表团。代表团向达赖喇嘛赠送的礼物有:绸缎和氆氇各一驮,银瓶、银壶、银碗各一对,砖茶7箱。据古浪仓记述,见面时古浪仓被安排在达赖喇嘛的右席,坐垫较高,两位汉官(李仲莲、朱绣)坐在左席。司伦雪康和众噶伦均在场陪同。
第二天上午,甘肃代表团再次赴布达拉宫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在此见到了正在拉萨的九世班禅。当天,代表团还前往大昭寺二层的噶厦办公处,与众噶伦会议;并通过江孜给甘肃方面发了电报。
十六日,代表团拜访了九世班禅,并合影留念。九世班禅告知,即将起程返回后藏,欢迎代表团到日喀则。
十七日,代表团再次拜会十三世达赖喇嘛。
藏历新年即将到来,达赖喇嘛派人送来食品等礼物。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代表团受邀参加了在布达拉宫举行的跳羌姆等传统仪式。
藏历新年过后,甘肃代表团与西藏方面就政治事务进行了多次正式会谈。
藏历正月二十九日、二月四日,代表团与噶伦、三大寺代表等僧俗官员代表多次举行会议,商讨各项事宜,其中两个主要议题是:一、关于西藏地方派遣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川藏问题,但西藏方面拒绝了派代表赴京商谈的建议。二、川边停战协议延期问题。因1918年签订的《绒坝岔停战协定》一年期限已过,川藏边界两军对峙,随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屡经讨论,双方同意,维护和平,不轻开战端。
在拉萨期间,古浪仓活佛经常与格西喜饶嘉措辩难问学,交往频繁。古浪仓在天文历算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据古浪仓日记所载,时任门孜康医药学校校长的钦绕诺布向他学习了《日月食推算法汉历心要》,解决了日月食预报的难题。古浪仓活佛还向拉萨的僧俗人士传授了电镀金、银及石印等工艺技术;并与三大寺众格西辩论显密教法,名望日盛。
甘肃代表团在拉萨访问的三个多月里,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司伦雪康、总堪布及众噶伦会面,与僧俗代表会商事务,还广泛接触了西藏僧俗各界,对政教上层的政治态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李仲莲、朱绣在《呈报抵藏情形文》中明确写道:“西藏内部本系新旧两派,旧派居十分之七,新派只居十之二三。旧派以藏王及总堪布、三大寺为最有势力者,多数尚有思念故国之意。新派以四噶布伦为最,常受英人愚弄,藉为护符。”“惟查各方面情形,藏番对汉甚愿照旧和好。”清末民初以来,中央政府及内地各方对西藏内部的政治情况多有隔膜,此次代表团成员通过一段时间的直接接触、考察,对西藏的政情有了较多的认识,为中央及甘青等地方制定对藏政策、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依据。
甘肃代表团离开拉萨前,十三世达赖喇嘛设宴饯行。朱绣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中记道,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宴会上声言:“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驻藏大臣——引者注)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九世班禅也派人从扎什伦布寺送来公文和礼品,朱绣认为“其倾向共和之心,较达赖殆有过之”。
4月27日,甘肃代表团离开拉萨,起程返甘。8月,代表团带着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及西藏僧俗大会等的函件回到甘肃。
六、简要评价及历史影响
就目前所见的资料而言,甘肃代表团入藏虽然获得了民国中央政府的许可,而英国方面也希望民国政府向甘肃代表团授权,进而在拉萨重启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谈。但民国政府并未授权这样做。而且,从甘肃代表团的派遣过程、人员组成等方面看,与后来代表中央政府入藏的贡觉仲尼、黄慕松或吴忠信等代表团性质确实有所不同。因此,不应将其视为中央政府代表团,而是民国时期首个公开入藏的内地官方代表团。
甘肃代表团访问拉萨百余日,与西藏政教上层广泛接触,增进了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有利于恢复和改善关系。其一,通过广泛接触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等西藏僧俗上层,联络感情,解释嫌疑,有利于消除多年积累的隔阂,了解各方政治态度,为今后恢复、改善关系,处理“西藏问题”提供基础。其二,有利于缓解川藏对峙的紧张局势,维护边藏和平。1918年10月签订的《绒坝岔停战协定》一年期限已满,川藏边界局势再度紧张。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因四川军阀内战,不能援助川边,遂致饷械断绝,电请陕甘督军张广建转呈中央,请令甘肃拨给饷械支援。西藏地方也从各处征兵、征粮,积极备战。双方剑拔弩张,情况紧急。正当战火一触即发之际,甘肃代表团入藏联络,双方同意维持防守主义,继续停火,为维护边藏和平作出了贡献。
时任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认为,甘肃代表团入藏“是自1910年中国军队迫使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件,也是英藏关系倒退的一个表现”。然而,内地各军阀势力争斗不止,政潮动荡不息,民国政府无力解决“西藏问题”,甘肃代表团获得的成果未得到充分利用。
对英国而言,由于一战后英国驻华公使催促中方开议藏约的方法未能奏效,英国一直在寻求新的对藏政策和方法。甘肃代表团入藏,“给处于关键时刻的西藏形势带来了新的因素”,在英印政府、印度事务部及英国驻华公使馆等有关各方内部“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为此,英国重新审视和调整了对藏政策,最终,英方决定派遣贝尔使团入藏,随后又批准了向西藏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训练等政策。此时,西藏正值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高潮时期,西藏方面同意了开通江孜至拉萨之间的电报线路,在江孜举办英文学校,批准英国登山队入境攀登珠峰等一系列要求。此后一段时间内,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随之进一步扩大。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