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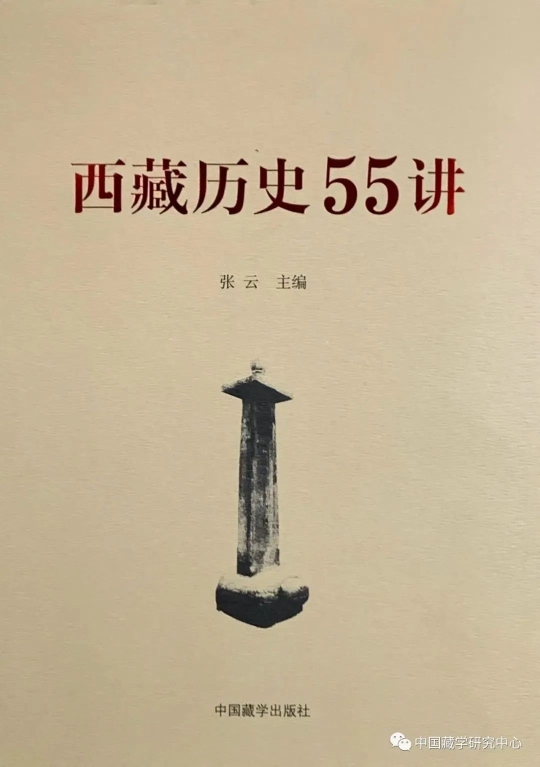
第5编 民国西藏历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时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的38年,称为民国时期。民国时期虽然只是短短的38年,却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一页。以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历史为主体,大致可以划分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热振活佛摄政和达扎活佛摄政三个历史阶段。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历史主要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藏族与内地汉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关系,仍然是影响和决定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民国时期,中国正经历着艰难的近代化过程。西藏地方自辛亥革命后,在英国的支持下,曾一度与中央政府疏离,驱走中央驻藏官员和驻军,采取“两面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不正常关系”。然而,西藏地方在政治上始终未与中央政府完全断绝关系,而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尽管在国内军阀混战、列强侵略的困难局势下,仍然一以贯之地以国家根本大法及各种法律,坚决维护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坚持西藏地方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此处理一切与西藏地方有关的事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法律,以及西藏地方的法律大多沿袭清朝法律等方面看出来。
民国时期特别是在国民政府执政时期,中央政府先后派大员入藏,册封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在拉萨设立派驻机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西藏地方政府和在内地的九世班禅也设立驻京办事处,并先后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各种机构或代表会议,享有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参政议政权利。特别是两千多年以来,西藏地方与内地频繁的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交往,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割不断的纽带,是双方关系的基础。
近代以来,国外有些学者和逃亡国外的达赖集团,一直鼓吹“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谬论,其中民国时期“西藏事实上独立”是他们的根据之一。民国西藏地方的真实历史无情地批驳了这种谬论。就是当时极力支持、鼓动西藏脱离中国“自治”“独立”的英国政府,也只是歪曲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承认或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民国后期企图染指西藏的美国及独立后的印度等国,均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第二,民国时期,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活动,是影响这一时期西藏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英国及英印政府积极支持和扶植西藏地方上层中的亲英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将侵略势力深入扩展到西藏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各方面;策划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觊觎并企图侵占西藏东南部的门隅和察隅等地;极力阻挠和破坏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每当民国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有所改善时,英国总是立即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阻挠和破坏,甚至通过外交方式,向民国中央政府施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冷战战略的需要出发,也开始染指西藏,进行了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
第三,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仍保持着自清代以来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但是,在世界近代化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1904—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留库伦、北京、印度等地期间,耳闻目睹近代科技、教育、军事的发展。为促进西藏地方的发展,巩固政教合一制度,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逐步实施改革,也被称为“新政”。改革涉及政治制度、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是在西藏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主动适应时代需要的社会改革。改革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加强和巩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但客观上具有促使西藏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性质。如在噶厦中新增了一些办事机构,如藏军司令部、拉萨警察局、电信局、电报局等具体实施各项近代化建设的职能部门;试办近代化的工业;注重文教事业,派遣留学生前往英国、俄国学习军事、机械等专业,设立藏医院“门孜康”;建立和装备近代化的藏军等。这些改革措施客观上促进了西藏地方的近代化,影响深远,具有进步的意义。这也是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明显的“两面性”(表现在与中央政府和英国的关系上)和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不仅如此,随着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对外的逐渐开放和外界接触的增多,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族解放运动思潮,在西藏一小部分知识阶层中也产生了影响,并且逐渐渗入西藏社会的诸多方面。1934年西藏龙夏的改革,1944—1946年的“西藏革命党”事件,以及近代西藏著名学者、人文主义先驱根敦群培的思想、论著和活动等,均是这一时期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西藏社会中的反映。
第四,尽管在民国时期西藏社会出现近代化萌芽,但是其政治体制仍然是牢固的政教合一体制,支撑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民国时期,西藏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生产力落后,封建农奴制度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土地进一步集中到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三大封建领主手中,他们为满足日趋腐化的生活而加重了对广大农奴的压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某些改革措施,特别是扩充和武装藏军一项,清查和增加贵族、寺院的税收以为军费,自然使三大领主加重了对一般农奴的压榨。英国对西藏的经济掠夺,也加重了广大农牧民的负担。1923年九世班禅被迫北上,龙夏的改革失败等,都清楚地反映出民国时期腐朽的西藏农奴制的没落。这也是民国时期西藏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
第41讲 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
在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后,民国中央政府通过宣布五族共和、满蒙回藏各属之待遇条件,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任命西藏办事长官等一系列政治上的安排,宣示中华民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1912年,民国政府任命西藏办事长官钟颖。1913年,驻印华侨陆兴祺继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由于英印政府阻拦其入藏,陆兴祺未能入藏,但他仍旧成为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等西藏地方政教上层之间的重要联络人;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陆兴祺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强烈反对“西姆拉条约”;1913—1915年,他组织遣返流亡在哲孟雄、英属印度等地的前清官兵、内地商人及其家属回国,处理前清遗留的西藏邮政、海关等事宜。应该说,陆兴祺为民国初年沟通西藏地方与民国中央政府关系作出了贡献。
一、清末民初西藏地方政治形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为维护扩大其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利益,阻止俄国势力南下,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通过战后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1904年“拉萨条约”等,攫取了诸多在藏权益。英国两次侵藏战争中,清朝中央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不支持西藏地方的抗英斗争,导致其在藏统治权威被削弱。1910年,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等事件接连发生,导致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关系恶化。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驻藏军队内部革命派、哥老会等势力纷争,发生哗变,又发展为驻藏军队与西藏地方武装之间的争战。西藏局势进一步恶化。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取代清朝后,通过宣布五族共和、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等政治安排,宣示对西藏的主权。
二、民国政府任命前清驻藏陆军统领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宣示民国中央对藏主权
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布:中华民国是合汉、满、蒙古、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面对武昌起义后十数行省先后宣布独立的局势,民国政府作出声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虽然,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处于“政令不出京城”的困境,但新兴的共和政体已经成立,一系列政治体制变革正在进行。职官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变革最直接的体现。
为了稳定局势,民国政府在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基本延续原有的权力格局,主要通过职官的设置与调整,实现国家政治由原来的封建王朝向共和政体的转变。1912年5月9日,民国政府任命前清驻藏陆军统领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也就是说民国政府委任原驻扎于西藏的清朝军事官员担任民国政府的西藏办事长官。这主要是为了稳定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实现政治体制的平稳转变。
这位新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钟颖(1876—1915)是满洲正黄旗,而且还是同治皇帝的表兄弟。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他被任命为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1909年,清廷命钟颖率领新军入藏,于1910年2月抵达拉萨,到藏后担任驻藏陆军统领。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后,驻藏军队内部发生哗变,随后又发展为驻藏军队与西藏地方武装之间绵延数月的争战。民国政府所期望的平稳政治过渡并未实现。1912年底,在英印政府的干涉下,包括原清朝驻军统领、民国政府新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在内的全体驻藏官兵被迫撤离西藏,造成当时再没有中央驻军与官员在藏的局面。1913年3月底,钟颖和部分士兵停驻于西藏边境亚东地方等待中央政府的命令,但迫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的一再催促,最终于4月14日离开西藏地界,前往印度。民国政府以“贻误藏事”免去钟颖西藏办事长官职位。1915年,民国政府以罗长裿被害一案,判处钟颖死刑。
对于钟颖受命担任西藏办事长官前后一段时间的表现,有学者评论道:“在领导拉萨驻军反对亲英分裂势力武装进攻的反分裂战斗中,是尽了职守、表现不错的,他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斗争中,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多次拒不离开西藏,长期坚持不交出武器出藏,领导反对亲英势力的艰苦战斗,这点应予以肯定。”
三、民国政府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
钟颖被免职后,由谁接任,如何维系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当时,民国政府考虑接替钟颖担任西藏办事长官的人选,主要包括:清末受派入藏查办藏事的张荫棠(1866—1937)、清朝最后一任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1876—1947),以及曾任川滇边务大臣的王人文(1863—1939)等。
张荫棠曾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以参赞身份随唐绍仪赴印度就“拉萨条约”与英国进行谈判。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唐绍仪回国后,张荫棠以全权大臣身份接议藏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清政府命他入藏查办事件,由于他秉公执法、整顿吏治,获得西藏上下各界尊敬。西藏广泛种植的“张大人花”据说就是张荫棠入藏时带入西藏的,可见其名望深入人心。张荫棠在藏期间,提出了一系列革新计划,开启了西藏地方推行近代化暨清末新政的先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张荫棠任全权大臣前往印度,与英印政府谈判新的藏印通商章程。宣统元年(1909)后,他担任出使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四国大臣。民国成立后,留驻美国的张荫棠随即被任命为驻美临时“外交代表”,之后又受命为驻美公使。
温宗尧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以副都统衔任驻藏帮办大臣。宣统二年(1910),因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出走印度,清政府革去其达赖喇嘛名号,并准温宗尧开缺赴川。1911年南北议和期间,担任南方参赞,协助伍廷芳工作。1912年8月,任国民党参议。
王人文,云南大理白族。清末,曾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宣统三年(1911)担任“护理四川总督”期间,支持四川人民爱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王人文曾被武昌政府誉为四川革命的“八大功臣之一”。1912年加入国民党;同年4月,任川滇宣慰使。民国时期,曾多次当选参议院议员等职。
不难看出,民国初年,这几位西藏办事长官候选人都算得上“声望素著”,他们或曾在藏任职,或曾任职川滇,都是清末经办或涉及藏事交涉的政府官员,或了解藏情,或通晓边务。然而,由于国内外局势及个人处境等不同原因,这几位候选人终未能任职办事。而且,民国政府成立初期,英印政府极力阻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改善关系,民国政府先后派出的几批入藏代表,如赴藏劝慰员杨芬,册封使马吉符、姚宝来等均未能入藏。因此,鉴于西藏地方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中央隔阂很深,藏中再无中央政府派驻官员等困难情形,民国政府迫切需要的是一位熟悉藏情、热心藏事,能够使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班禅、噶伦等西藏地方政教上层保持联系的中间人。因缘际会,陆兴祺这位在印度加尔各答经商的华侨成为民国中央政府的最终选择,于1913年4月2日被任命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
陆兴祺这个远在印度的华侨商人又是如何成为民国政府的最终选择并委以重任的呢?这还要从清朝末年,陆兴祺与多位经办藏事的官员之间的交往说起。据记载,陆兴祺,号韵秋、鸣秋,少年时即来到印度加尔各答,在此经营“天益号”商行(Thinyik Trade Company)。当时,由印度进藏的中国官员很多都得到他的照料,汉文记载中多称其为“天益号主”或“天益长”。由于他在印度经商多年,并从事印藏间的羊毛等货物贸易,因此,他对印度及西藏地方的情况都较为熟悉。如1904年,驻藏官员马吉符到加尔各答,曾与陆兴祺相见,两人还谈起“印度洋人”的问题。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1月,道台陶思曾奉命赴藏处理开埠事宜,到印度加尔各答后,陆兴祺专程前来拜访他。次年5月,陶思曾由西藏返回加尔各答时,就住在“天益号”。清朝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还曾经委任陆兴祺为驻藏采办,每月发给饷银30两,并向清政府保举他晋升四品官衔的候选同知。
清末时,陆兴祺就曾协助驻藏大臣联豫等在印度收集与藏事有关的信息。如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赴印之际,陆兴祺曾探报达赖喇嘛抵印及在印相关情形,通过电函向联豫及四川总督赵尔巽等报告,为清中央政府决策藏事、调整政策提供了信息。如《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辑录的四条涉及陆兴祺的电文,主要内容都是联豫以陆兴祺提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抵达印度等信息向清政府报告情况。
正由于陆兴祺是这样一位“少年留学印度,于藏印情形,至为熟识,藏事素著热心,向来驻藏官员多所借重”的爱国华侨,所以,在民国初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联络不畅、声讯难通的情况下,陆兴祺逐步成为联系西藏地方与民国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角色,利用其身处加尔各答的地利之便,设法积极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噶厦等西藏上层联系,为联络西藏地方、收集和报告西藏地方情况等发挥了作用,受到各方重视。
1912年8、9月间,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成立之初,陆兴祺即受聘为顾问。蒙藏事务局是民国政府主管蒙古、西藏事务的机关。1912年4月22日,总统袁世凯发布命令,宣布:“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其理藩院事务,著即归并内务部接管”。1912年5月,蒙藏事务处宣告成立,隶属于内务部。不久后,因“蒙藏事务繁巨”,于同年7月改设蒙藏事务局,直隶于国务总理。1914年5月,又改组为蒙藏院,直隶于总统。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南京设立蒙藏委员会。
陆兴祺受聘担任蒙藏事务局顾问后,凭借身处印度、接近西藏地方等有利条件,联络各方,积极参与民国初年的涉藏事务。
1912年底、1913年初,驻藏官兵被迫离藏,钟颖等留驻靖西(亚东)期间,陆兴祺以“与藏人交往甚密”的华侨商人,同时又是“中华驻印委员”的身份,多次致电达赖喇嘛、噶伦等西藏地方上层,以及留藏任职的前清官员谢国梁(庭树)等,说明是非利害,力图劝阻西藏地方驱逐西藏办事长官钟颖等出藏。而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留印期间及返藏后,陆兴祺还通过各种途径与西藏地方在印的一些官员取得联系,劝告达赖喇嘛及其左右倾心内向祖国,尽力解释五族共和,努力维护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介于陆兴祺关注藏事,熟悉西藏情况,颇得前清驻藏官员信任,以及民国初年他为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中央保持与西藏地方关系积极联络等原因,民国政府于1913年4月2日正式任命陆兴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
任命一名华侨商人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官员,即便在今天看来,也难免引起疑议。在任命前,民国政府显然也有一番考虑,因而,授予陆兴祺的职衔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而非正式的“西藏办事长官”。所谓“护理”,也就是官员出缺时,以次级官员守护印信,代理其事。民国政府首任“西藏办事长官”钟颖任职期间,以“办事长官关防未到以前,暂用驻藏大臣关防”。而钟颖由印度启程回国前,曾将这枚前清驻藏大臣铜质关防交给陆兴祺。因此,民国中央政府沿用旧制,令陆兴祺守护印信,代理其事,命以“护理驻藏办事长官”,也算是“名副其实”。而且,以“护理”而非“西藏办事长官”之名,既可适当缓解舆论反对之声,也可在日后有更佳人选时,再正式任命为“西藏办事长官”,留有转圜余地。
四、陆兴祺沟通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僧俗上层关系
陆兴祺任职“护理驻藏办事长官”之初,正是民国初年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最为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陆兴祺为民国政府中央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及西藏地方政府转发、递送了许多往来函电,传达中央政府指示,沟通双方关系。1913年3月25日,九世班禅致电民国政府,表达“班禅久仰中朝,实沾德惠,凡在我属汉边官军民等,无不力加保护”,“仰跋年余,尚未见示,究竟要此土地人民与否,好定意向”。鉴于九世班禅“效忠民国,维持藏事”,民国政府于1913年4月1日颁发了“加封九世班禅致忠阐化名号令”。该加封令由陆兴祺派专人送达扎什伦布寺。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作为西藏政教领袖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按照历史定制,接受中央政府封号,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陆兴祺为促成这一历史事件发挥了重要的联络作用,有利于维护和宣示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值得注意的是,总统袁世凯还明确告知班禅“嗣后如有呈报事件,即交陆兴祺转寄,藉期接洽”。之所以强调由陆兴祺转寄,除了考虑到清末民初西藏邮路不通、需要经驻印的陆兴祺中转函电等因素外,可能还与清代以来形成的历史定制有关,即规定达赖喇嘛、班禅、摄政等西藏政教领导人必须通过驻藏大臣向皇帝呈递文书,而不能径行呈递,而此时陆兴祺已被任命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袁世凯特意强调“如有呈报事件,即交陆兴祺转寄”可能也隐含有延续清代定制、申明对藏主权的意义。
除了转递中央政府与西藏各方的往来函电,联络西藏地方外,陆兴祺还主动致电中央政府,呼吁保卫西藏、巩固边疆,积极为藏事建言。如民国二年(1913)1月6日,陆兴祺向袁世凯转呈达赖喇嘛的函电,并致电袁世凯:“藏自去秋兵变,汉官陆续内渡……若不从速派员进藏赓续收理,则藏非我有矣”,“即派专员酌带护兵进藏,假与达赖商办藏事为名,使藏局未即脱离我关系,彼或未便强阻。至川滇边界,祈饬该省派兵重驻,以办日后不得已划界地步,是为至要。”从同一日发出的另一封电报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陆兴祺作为商人所具有的对环境和机会的敏感,以及他具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如他在了解到“钟(颖)此次与番议和,曾请英官签押保证”,“带同民军千余日内抵靖(西),闻有被累喇嘛数百随奔”等情况后,敏锐地意识到“惟靖地孤悬,万难久驻”,“现闻达赖已派噶布伦一人、堪布四人,来印致谢印政府,其中必有别谋”,提出应“于此时引与周旋,相机劝诱,以移僻志……密派专员带款来印商办一切”,他还指出“故论藏事,首宜注重外交,次宜联结达赖左右,以为转圜之计”。此建议顺应当时国内外形势及西藏局势的发展,中央政府予以肯定和采纳,答复陆兴祺:“来电注重外交一节,极为有见,已送外交部核办。”
五、陆兴祺揭露英印政府分裂西藏图谋,强烈反对“西姆拉条约”
民国初立,英国政府即提出有关西藏的要求,企图扩大在藏势力,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这一时期也希望借助英国的支持,巩固、扩大自身统治权力。因此,英国和西藏都要求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议。
1913年6月下旬,陆兴祺致电民国政府,其中写道:“达赖喇嘛来电其意趋重撤兵、争地。彼迭请在大吉岭会议,所持定亦如此,盖欲以外人为后盾耳。”陆兴祺的话不幸言中,在英国操纵策划下,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召开了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
中华民国政府全权代表陈贻范于1913年10月2日行抵加尔各答。虽然,陈贻范具有较为丰富的外交经验,但他对藏事知识不多。因此,西姆拉会议前后,陆兴祺积极发挥作用,协助民国中央政府谈判代表陈贻范,为其备妥议约资料,并委派熟悉藏情的秘书李嘉哲陪同前往西姆拉赴会,履行了“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职责。
会议开始后,陆兴祺利用身处印度的便利条件,收集、报告会议情况,揭露英印政府分裂西藏的图谋,为民国政府最后取消陈贻范画行的草约,拒绝承认“西姆拉条约”提供信息、提出了建议。如1914年4月28日,在陈贻范被迫草签“西姆拉条约”的第二天,陆兴祺看到草约后立即致电袁世凯,强烈反对该约:“惊悉印政府外交手段之老到不可企及,其内容之酷烈,直据西藏为己有,固不仅剥尽我国主权而已。但争界固为要着,而其中各条件若不悉力磋商修改,使我徒驻一官、兵三百,除糜饷坐食外,尚有何效力”,建议由外交部将约稿详细译出,由总统迅速召集会议筹谋挽救。他在电文中严正提出:“乃关领土主权,岂可因受人所逼而拱手退让?”他还建议,立即电告驻英公使刘玉麟向英国政府“据理力争,以期公允。务使此约发表后,不至惹起列强作同等要求及藏边之扰乱”。不难看出,陆兴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尤其对英印政府企图分裂中国,阻止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政治意图有深刻洞察。
5月11日,陆兴祺再次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外交部,清楚说明西姆拉草约界图的重大危害,即“侵蚀青海全部,且侵入中国本部处甚多”,并详细列举草约界图对新疆、甘肃、云南、四川等地的严重侵害,并大声疾呼:
前清收取金川若何艰难,今既归入藏界,且占理藩厅之大半,若合所划者通长拉计,失地之巨那得不神悚胆寒,彼今逼我按照彼图划押,异日按图索地,势所必至。地理形象犬牙交错,万不可不审慎周详,查准经纬各度之所在,方与从事,否则贻害无穷。不但此也,西金、尼泊尔,布丹既折英手,应将印藏详细界线急行划清,以免侵占,亦宗主国应尽之义务。
陆兴祺的电文中如此深入表里的分析,为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作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拒绝承认“西姆拉条约”的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应该说,陆兴祺及秘书李嘉哲等对西藏问题及边疆情形的熟稔,使他们能够在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得失的紧要关头,为中央决策提供有理有据的政策建议、履行“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有西方学者评价陆兴祺在“西姆拉会议”期间是个关键人物,说他的“情报网是极好的,他有清晰的政治头脑。他向北京提出的意见是始终一贯的:寸步不让”。而陆兴祺所发电文言辞间充溢的爱国热忱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陆兴祺救助、组织滞留哲印人员回国
1912年联豫等前清官员、驻军,以及部分内地商人、眷属等被迫离开西藏,进入印度。到1913年1月,民国政府新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钟颖也被迫离开西藏。联豫、钟颖等先后回国,但一部分官兵、商人及眷属流落在哲孟雄(今印度锡金邦)、英属印度等地。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对这些难民极为同情,自1913年起协调人力、财力进行救助,并组织他们回国,这一工作到1915年底结束。
对滞留在英属印度的内地商人、前清官兵及家属,英属印度当局采取了限制性措施,特别是对前清官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还要求写下不再干预西藏事务的“具结”,并扣押在英国人经营的指定旅馆里。为防止他们返回西藏,1912年10月至1913年5月间,英印当局又把他们分7批遣返回中国。据中、英两国的档案显示,这7批被遣返的中国人由加尔各答乘船返回上海,包括前清官员、士兵及妇女、儿童等,共计1633人。
1913年4月9日,在被迫离开西藏前,西藏办事长官钟颖还分别致电江苏都督、四川都督,强调回国人员中有40名退伍的士兵,他们都“苦劳可悯”,到上海后请江苏都督派人照料,资助他们返回四川。在他们返回四川后,请四川都督在“藏饷项下发给十四个月薪饷”,以免他们返乡衣食无着。
因滞留哲孟雄、印度的内地商人、前清官兵生活困苦,1913年4月26日,钟颖专门致电陆兴祺,希望能汇款6000元,以便加以资助,“稍加资润,劝使内渡”。陆兴祺对此也很忧虑,他曾多次组织当地华侨、华商捐款,资助这些流寓印度的军民回国和生活。陆兴祺还多次致电总统袁世凯,汇报这一情况,强调这些流寓军民“无处觅食,生计愈穷,死亡相闻,危迫至极”,请政府“设法筹济”。在1914年6月3日致财政部的电报中写道:
西藏自变乱后至今,已逾两载,所有留藏华人生计久绝,困苦至极,陆续来印觅食者,现统计已达六百余口。经商无本,食力无方,不通言语,不服水土,穷愁交迫,死者已十之一,病者已十之三四,嗷嗷待毙。实已危迫万分。以国体所关、民命所系,已电恳大总统恩准救济,闻已蒙交大部核办。现计宜资遣回国者三百余人,其无家可归须发急赈者二百余人,万祈尽速筹措,不胜切盼。陆兴祺,江。
1914年6月20日,袁世凯下令财政部“筹拨银二万两,以资赈济”。北京民国政府批准拨款二万两救济流寓印度的军民,令陆兴祺很是振奋,可财政部却迟迟不汇款,又让他很无奈。7月,他三次致电财政部,催促汇款。直到1915年5月21日,财政部才通过花旗银行汇来赈济款大洋一万元。此后,陆兴祺又多次向财政部催索余款,久未得到回音。
1915年6月5日,外交部致电陆兴祺,请他用英文报告“办理赈济与资遣流落噶伦堡华民等事现在办理情形”。陆兴祺在回复外交部的电文中写道,正派人调查噶伦堡与附近地区穷苦华民,以便由“生谷拉”轮船遣返上海,依据以前的清册,“待赈者三百人,候遣者二百余人,尚有流落西藏边界者甚多”,都非常穷苦。但财政部的汇款“不为敷用”,他已五次电催财政部,“均不见复,请即向该部催将恩准之款全数汇下,以便快捷完事”。这一报告看来产生了作用。1915年6月10日,陆兴祺收到了财政部汇来的余款。
1915年8月,陆兴祺就救助、组织滞留境外人员回国事宜向民国政府提交专门报告,即《呈报资遣出藏流落哲印等处难民回国情形缮具年籍花名男女大小丁口清册请鉴核文》。呈文中写道:派人前往哲孟雄之大吉岭、噶伦堡等地,“详细调查现在人数,一面招示各处难民愿回国者前来报名”,“得闻此信如庆再生”。根据所派调查员的报告,“现有生计暂不回国人数约百名,暨现住病院未痊者十余人与僻远之处尚无音信者另行办理”外,已经报名“点验共计男女大小丁口一百九十名”。这190人已于6月23日“乘轮车来印度,经派员点验名数相符”,即搭乘“生谷拉号”轮船于6月29日上船,30日开驶回国。10月,他再次出资将第二批人员运送回国,并将第二次回国人员花名清册呈报民国政府。
这些得到救助回国的人员对于救助他们的钟颖、陆兴祺的工作都感恩戴德。如1917年前后,“西藏被难官兵、商民、回番代表”张登魁、李家耀等130多人在一份呈文中称,他们在西藏变乱后随同钟颖被迫出藏。钟颖回国之前,还嘱咐他们“俟大举入藏时,尔等为内应”。此后两三年间,他们“既被仇于藏番,复受凌于外人”,因此“禀请署长官陆兴祺,电请中央”,大总统“轸念难民为国受苦,准由印度照前次办法,经官节节遣送回国”。
对于陆兴祺救助的工作,当时国内各界给予高度评价。一方面,中央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在经费上给予全力支持。1916年1月初,陆兴祺呈递了“两次资遣出藏难民用过巨款造册呈请核销”的报告,总统袁世凯在1月3日即批复“交财政部审计院核销,册并发”。3月15日,经财政部、审计院审核后,总统批复“准予核销”。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舆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尚秉和是辛亥革命的经历者,他从1911年起创作《辛壬春秋》,1924年刊行,书中介绍了西藏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史事,其中专门强调,“中国难民……流亡于哲孟雄、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辛壬春秋》一书,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书中强调陆兴祺遣返难民之事,表明当时社会舆论对此事的重视。
七、陆兴祺为沟通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所作的贡献及评价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民国政府为稳定西藏地方局势,迅速任命前清驻藏陆军统领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在钟颖被迫离开西藏后,英印阻挠民国中央派人入藏的困难情形下,民国政府于1913年4月任命身处印度的华侨商人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希望借助这位熟悉藏情、交游广泛的侨商,与西藏地方保持联系。由于英印政府一再阻拦,陆兴祺始终未能入藏履职,但他发挥自身优势,利用与西藏商人关系密切等条件,通过各种途径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噶伦等西藏政教上层联络,为沟通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西姆拉会议前后,他积极协助民国政府进行谈判准备,并凭着一腔爱国热忱,以“身在印度,对于彼国图藏情形知之颇悉”,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理有据的建议。陆兴祺还积极救助、组织流落哲印的难民回国,承担了前清遗留的西藏邮务等事宜,为维护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作出了贡献。虽然,“也许陆兴祺终其一生也不知道他的每一道通过印度的电文均被英方截获了”。而且,在最初几年积极经营藏事后,其后的大部分时间陆兴祺都在内地,因而在藏事上较少作为,且几次提出有关藏事的建议均未见下文。虽然,这与其个人原因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政府更迭频繁,中央政府无力解决“西藏问题”这一根本原因造成的。
应该说,成立之初的民国政府通过任命“西藏办事长官”“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努力维护、宣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即使在民国初期对边疆地区施政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陆兴祺这样的爱国华侨和包括众多藏族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都反对西藏脱离中国,为了国家主权和山河完整,他们备历艰难曲折而效忠尽力,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和爱国热情。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