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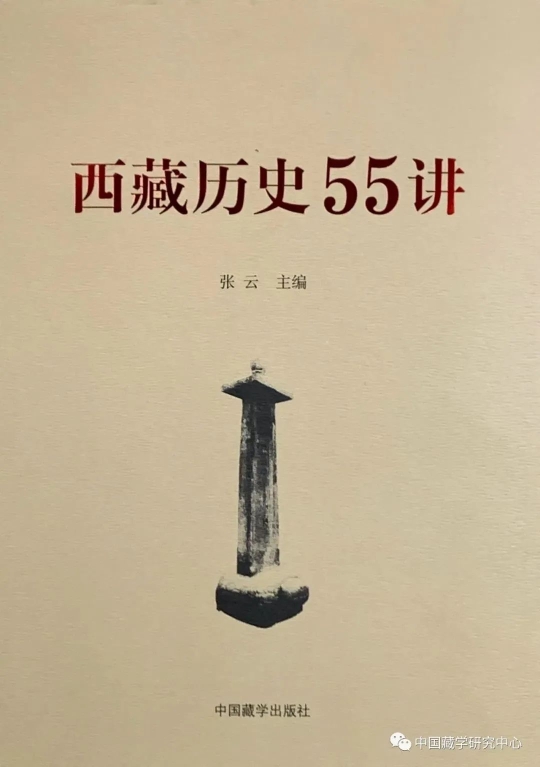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39讲 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与西藏人民奋起反抗
1903年,英国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距离第一次侵藏仅15年。英国为何如此急不可耐地发动对西藏的第二次入侵?其过程和影响如何?清朝政府是如何应对的?西藏人民又是怎样奋起反抗的?下文将分而述之。
一、入侵背景
当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加紧筹划侵略西藏的时候,沙皇俄国也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青藏高原,其触角伸到了拉萨,这令以英属印度总督寇松为首的英国强硬派万分担忧。俄国在19世纪中后期对我国西部边疆派出多支“考察队”,这成为俄国搜集情报的重要手段。这些“考察队”都配有武装、大批测绘器材与后勤供应。他们不顾中国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反对,肆意横行,在我国藏族聚居地区制造多起血案。尽管如此,这些“考察队”也仅是在新疆、蒙古、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区活动,始终未能进入拉萨。
19世纪中期以后,俄国加强了探查从俄境赴西藏道路的情况,大力开展对藏贸易,充分利用俄境内信仰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主要是僧人、商人),赴藏刺探情况,并打入上层社会,影响达赖喇嘛的决策,以实现俄国渗透西藏的野心。其中,德尔智是最为著名的一位。
1900年10月2日至15日,《圣彼得堡杂志》(Journal de St. Petersburg)报道,9月30日,沙皇在里瓦几亚皇宫(Livadia)接见了达赖喇嘛政府的官员“阿哈布拉·阿旺·多杰耶夫”(即德尔智,这是其第二次出访俄国)。这一报道令印度政府十分震惊。这无疑是对竭力试图同西藏建立“直接联系”的英印政府的一个强有力打击。
据印度总督哈定(Hardinge)所言,俄国公认的西藏事务专家巴德玛耶夫(Dr. Badmaev)“成功地同达赖喇嘛保持着某种关系”,并认为德尔智此行是来解决拉萨同俄国布里亚特人(Buryat)和卡尔梅克人(Kalmuks)之间的宗教问题(他们大都是佛教徒)。然而,有一点很确定,“无论达赖喇嘛派出的使团目的是什么,俄国政府都充分利用了这次出使”。
从全球形势来看,20世纪最初几年里,英国在世界的殖民主义统治和扩张受到俄、法等国的挑战。首先,俄国加快了在亚洲的推进速度,并占领了满洲里,对朝鲜、蒙古和新疆也心怀觊觎。英属印度北部的阿富汗边疆受到挑战,第三次阿富汗战争很有可能爆发;英国在伊朗和波斯湾也受沙俄势力扩张的威胁;英法冲突在非洲达到了顶峰;英德关系日益恶化。所有这些因素对英国如何处理“西藏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英国不愿冒险在西藏开辟一个新战场;另一方面,英属印度边疆又受到俄国殖民势力日益南扩的严重威胁。
此时的俄国也愈发认识到西藏的重要性,决意同英国争夺西藏,巴德玛耶夫在写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这样说道:
英国已经在克什米尔称王,并通过克什米尔从西向我渗透,而现在英国又想控制西藏,以便从东部向我渗透。站在印度这边来看,西藏对亚洲至关重要。谁统治了西藏,谁就统治了青海和四川省。谁统治了青海,谁就控制了整个佛教徒世界,就连俄国的佛教徒也不例外……一个真正的俄国人难道真的不明白允许英国进入西藏有多危险吗?和西藏问题比起来,日本的问题简直微不足道。小小的日本的确会威胁我们,但毕竟中间有水相隔,而强大的英国却将与我们面对面地打交道。
可见,俄国对西藏十分重视,并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占领西藏会给俄国带来严重后果。
印度早期秘密革命活动家、学者塔拉克纳特·达斯(Taraknath Das)这样评价英国在西藏的扩张:“英国在西藏扩张势力,成为英国在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抑制俄国向印度推进,而且能够令英国完全控制长江流域,并以此对抗俄国和法国在中国的企图,确保‘印度帝国’的稳定。”
英俄加剧了对西藏的争夺,俄国膨胀的野心不断刺激着英国紧张的神经,这就是英军首领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兵入侵西藏的国际背景。
二、原因分析
英国在短短15年后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原因如下:
第一,贪得无厌:英国妄图扩大对藏经济侵略。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割让台湾,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与俄国也加剧了在中亚的争夺。经过第一次对西藏的武装入侵,英国对自己在西藏的经济侵略远远不能感到满足,希望进一步增加口岸,并获得开矿等特权,为此,在1893年中英《藏印条款》签订后不久,英国政府开始和清朝政府交涉,企图迫使清政府给予英国人更多在西藏的特权。
第二,寇松上台:强硬的对藏政策。
1899年1月6日,乔治·寇松取代额尔金(Lord Elgin)成为新一任印度总督。寇松采取了同其前任额尔金总督完全不同的强硬政策,这是因为:首先,寇松精力超凡,作为莅任伊始的大英帝国印度最高长官,寇松无法容忍“这种令人愤怒的边疆争端”继续存在;其次,寇松高度重视俄国向英印边疆推进的任何举动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寇松多年来关注亚洲政治,他坚信英国迟早都会起来反对俄国统治整个亚洲的威胁,正如其在1901年10月所写的:
作为一名研究俄国雄心壮志和处事方式15年的学生,我可以自信地说,俄国的最终目标就是统治亚洲。
从荣赫鹏的回忆录中可知,寇松发动入侵西藏战争的理由如下:
作为邻居,西藏人长期以来不断制造麻烦;他们破坏英国同代表西藏人的中国签订的条约;他们阻断印藏贸易,弄坏界柱……若俄国在西藏建立了一个站点,而我们却无法采取对抗措施,俄国将会在整个东北边疆引起我们极大的焦虑,正如其在西北边疆和北部边疆所做的那样,我们也许不得不增强边界守备力量了。对抗俄国在西藏不断增长的影响才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所在。
寇松找出种种入侵西藏的借口,而“对抗俄国在西藏不断增长的影响”才是其真正目的,这暴露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强盗逻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英俄争夺中亚的国际背景的确是影响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的重要因素,然而以寇松为首的英国侵略者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这一出兵西藏的借口,仍值得深思。
三、甲冈之争
1901年7月,英国印度事务大臣照会俄国外交部,声称英国对俄国与西藏之间的接触“势不能沉默不问”。其后,寇松要求英国政府批准他入侵西藏的计划。英国政府决定首先利用藏哲边界问题制造纠纷,为进一步侵略寻找依据。
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1902年6月26日),在寇松等精心策划下,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惠德(White)带领200余名英兵闯入甲冈,蛮横地命令当地藏族官员、守卡士兵和老百姓必须在24小时之内撤离甲冈界外。当地藏族官员多次向惠德提出抗议,惠德均置之不理,认为1890年驻藏大臣代表西藏同英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如此,并再三用武力进行威胁。
甲冈一地本来就是西藏人民世代居住的地方,是中国西藏领土的一部分。因1890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关于这段边界划分措辞模糊才引发了此地归属问题之争。然而甲冈始终都处于西藏地方政府有效管辖之下。惠德入侵甲冈之后,清查该地牲畜,据其统计,共有羊6270只,牦牛737头,其中属哲孟雄人者,羊仅1143只,牛仅80头,其余皆属西藏人。这一点更进一步证明甲冈是西藏人民传统生活之地。
英军使用武力迫使西藏官兵和老百姓撤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后,立即拆除甲冈原藏军隘卡,插立帐房,当地藏军仅40名,无法抵御。驻藏办事大臣裕钢传集噶伦,严正通告边事紧急,应派要员同汉官迅速前往阻止,但噶伦等以三大寺公议未妥推诿。五月二十八日(7月3日),达赖喇嘛给裕钢咨文,三大寺也递出公秉,均说不能派出噶伦,仅饬令驻边藏官达吉占堆(即英文文献中出现的Dhurkey Sirdar)一人前往。裕钢上奏说三大寺“禀词桀骜,似不知边情缓急,且似不以汉官为可恃,奴才等不胜焦急”。因此他只好派出委员何光燮于六月初二(7月6日)启程前往干坝一带阻止英军深入。
英军继续北侵至干坝后,驻藏大臣裕钢在7月23日照会英属印度总督,“委派三品衔特用知府何光燮,并知会达赖会派番员,同往边界,与贵国惠大员晤商”。清廷也于9月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 M. Satow),指出:“此次贵国官员,带兵径抵藏界,并未先期知照,且有拆毁隘卡情事。”“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速电印度总督,转饬该兵官,将拟办何事,俟驻藏大臣委员到彼,和衷晤商,切勿令兵队前进,以免藏众惊疑,期于边事有裨。”而萨道义却在复照中强词夺理,歪曲1890年的中英藏印条约,说甲冈在哲孟雄境内,反诬藏人越界游牧戍守,为武装侵占甲冈作辩护。并提出:“惟冀驻藏大臣所拟派何牧(何光燮)及达赖委员,与惠大员聚会妥商一切,即能将所有历年误会各节,全行销释。”正如中国亚东税务司巴尔(Randall Parr)所指出的,英国“拟与有权之藏官重订约章,以后华官无治理西藏之权。西藏政府倘不派员与之商议,彼竟乘机入藏代为治理……强令西藏为自主,与高丽同等。”其目的就是妄图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涉,侵害我国对西藏的主权。
由于当时英印政府与英国伦敦政府在对藏政策方面尚未达成一致,故英国暂时同意和中国委员就藏哲边界进行谈判。清廷派何光燮和亚东税务司巴尔前往边界参加。英印政府又提出中国谈判委员到哲孟雄甘托克(Gangtok)进行商谈,遭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当时,何光燮正患病,而驻藏大臣裕钢又即将调回。11月29日,裕钢照会印度总督,告知“何委员现已病痊,复经本大臣札饬赴边,并约会巴税司与贵国惠大员晤面妥商”。然而,当何光燮一行抵达边界后,惠德却迟迟没有回音。实际上,英国正在筹划新的侵略方案。
四、武装挑衅
1903年,英军重组,荣赫鹏成了唯一的政治首领,惠德被辞退,总旅长麦克唐纳被指定为护卫队的军事司令,最终英国使团人数骤增至8000人。
至1903年12月初,英国方面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只等采取行动。然而,12月的寒冬,向西藏边境采取军事行动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寇松在给新任国务大臣的电报中表示:“尽管寒冷,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是完全有利的。我们估计在完成此次行动并保持通讯联系与给养供应方面没有困难。”
12月10日,麦克唐纳、荣赫鹏、惠德等会合于隆吐,准备入侵西藏。英国侵略军的配置人员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荣赫鹏为首的所谓“西藏边境委员会”,即“西藏使团”,成员大部分由文职人员等组成;另一部分则是麦克唐纳率领的军事部队,主要任务是保证使团的“安全”。“这种在军事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精心制造的平衡关系,成为英国统治印度期间一再出现的模式。这两种利益常常发生矛盾。”
12月11日,英军偷渡则利拉山,集合于亚东口外,巴尔告知裕钢,此次英国带来的士兵要比干坝宗会谈时候更多。12月13日,英军越界,进占仁进岗,侵入亚东。而与此同时,驻干坝的英国使团仍在佯装与中方代表谈判,而荣赫鹏则从另一方向发动武装进攻。当时,西藏军队700多人驻扎在干坝附近各隘口,完全没有估计到英国会背信弃义地向春丕、帕里一带入侵。英国官方《泰晤士报》写道:“英军攻占春丕,对西藏人是一个重大的意外事件。”
英军入侵西藏后,亚东税务司巴尔与一名监督、一名藏官设宴于税关,以客礼相待,劝荣赫鹏班师回锡金,说驻藏大臣和噶伦即将来亚东,荣赫鹏不允。他们又劝荣赫鹏在亚东停留两三个月,荣赫鹏仍不理会。当日,巴尔具函告知拉萨具体情况。12月14日,英军占领春丕,停留4日;在此期间,干坝的英军和“使团”则按原计划赶到春丕,与荣赫鹏所率主力会合。12月15日,裕钢接到外务部电,要他“迅即亲赴边界,先与英员妥为商议,并切实开导藏番,毋得执迷不悟,致启衅端。”与此同时,英军2000人已经入侵仁进岗,裕钢表示立即致电外务部他不再等候噶伦,饬令备办夫马,定旬日后启行。而噶厦仍拒绝支应,并反对裕钢现在前去。
五、骨鲁大屠杀
12月18日,麦克唐纳率领800名轻装英军,从春丕向西藏重镇帕里进攻。12月19日,英军连运夫在内3000余人抵达帕里。21日,英军全副武装侵占了帕里宗。与此同时,西藏地方也在积极征兵,且不告知驻藏大臣。裕钢致电外务部,认为战争无法避免。
1904年1月4日,以荣赫鹏为首的“使团”抵达帕里。1月7日,英军进一步占据了帕里东北的堆纳(Tuna)。英军在堆纳做好一切准备以便直驱江孜。英军在堆纳共停留了3个月,直至3月底。在堆纳,荣赫鹏与麦克唐纳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麦克唐纳因无法忍受堆纳恶劣的气候以及物质、燃料的匮乏,在抵达堆纳第三天即率领大部分军队返回春丕,只留下荣赫鹏驻扎在堆纳。藏军并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攻孤零零的荣赫鹏驻军,仍对和平谈判抱有幻想。
1月12日,西藏拉萨派出代表同英军谈判。藏方指责英国背信弃义,入侵西藏领土,强占春丕和帕里,坚决要求他们退回亚东再进行谈判。荣赫鹏无理狡辩,坚持非到江孜不可。2月7日、10日,西藏代表再度同荣赫鹏谈判,均无结果。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4年2月9日),有泰抵达拉萨,11日接任驻藏大臣,裕钢启程回京。3月21日,荣赫鹏致函有泰:“本大臣等开赴江孜,恭候驾临,面商一切,并请随带主权番官。再请贵大臣严饬藏番,本大臣等定日开赴江孜,途中不得妄动起衅,若果无状,以后遇事则大有为难矣。”3月27日,有泰复函荣赫鹏,告知急欲会见荣,并已会见了达赖喇嘛;但因达赖喇嘛不愿提供交通便利,故遇到困难。鉴于此,有泰认为,西藏政治就是观望放任,而汉族官员则沉溺于自私自利,因此,藏人便规避行动。但若与达赖喇嘛争吵则只会生事,因此,他会“继续”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他已决定“给北京写个简要的汇报”,并再度敦请运送。关于会谈之事,有泰说,自己有绝好的理由带着扈从前往江孜,但“藏人狡猾欺诈,不遵守原则”,他得逼迫藏人“明白什么是原则”。若荣赫鹏突然侵入其土地,恐怕其又会故态复萌,由此不利于贸易条约的缔结。达赖喇嘛曾告诉有泰,如果有泰退还亚东,达赖喇嘛就会挑选藏人代表,邀请他(有泰)前往商谈相关事宜。
荣赫鹏接到有泰复函后,根本未予理会,反而积极备战。3月28日,麦克唐纳从春丕返回堆纳时,又带来“十磅大炮三尊,七磅大炮一尊,第三十二队工兵四连,第八廓尔喀兵三连半,以及野战病院工程队等”。连同原先在堆纳的军队,英军共计100余名,印军1200多名。
西藏地方政府对集中在骨鲁一带的藏军也作了部署,主要分左右两翼:左翼在距离骨鲁约9公里的曲眉仙郭,在赴江孜大道上建筑防御工事,阻截英军;右翼在拉莫湖对岸作掩护。
1904年3月31日,1300余名英国侵略军开始向曲眉仙郭藏军营地推进。当时,西藏代表作最后一次努力,要求荣赫鹏谈判,以避免使用武力。而荣赫鹏则一面伪装谈判,一面派其步兵、骑兵、炮兵偷偷向藏军阵地推进,等到谈判之时,藏军已经被敌人重重包围了。英军谈判代表到来后,首先声称:“既然要议和,为表示诚意,我军先将子弹退出枪膛,也要求贵军指挥官下令将火枪的点火绳熄灭!”英军指挥官即当场命令子弹退出一发,殊不知,在那一刹那间英军又将子弹推上了膛,藏军并未发觉,依令将土枪点火绳全数熄灭。于是,英军谈判代表荣赫鹏把藏军指挥官拖住。当英军的机枪开始向藏军疯狂扫射时,英军谈判代表也突然拔出手枪将藏军谈判代表拉丁色代本、朗色林代本、班禅代表苏康努、如本康萨及三大寺的一名谈判代表统统击毙。
第一声枪响后,英军使用来复枪和大炮在近距离约180米处,向手持大刀、长矛、火绳枪的藏军展开了赤裸裸的血腥大屠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帝国军队,就这样惨无人道地杀害了藏军近千人。荣赫鹏是这样描述这一场景的:
我方来复枪和大炮就对藏人实施了最致命的密集性摧毁……几分钟之内,整个战斗便告以结束。死去的藏人遍布平原,我军未接到直接命令便自动停火,但实际上每人只射击了13枪。
英国学者兰姆书中如是说:
英军与藏方发生了首次武装冲突。在这次战斗中,有700多人丧生,毋宁说这是一次对藏人的大屠杀,而这次大屠杀竟然发生在藏人同意缴出武器之后!
骨鲁大屠杀结束后,英军“尽管十分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却无心庆贺”。而侵略者还在为自己寻找侵略西藏的借口:“是由于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
无论怎样辩解,以伤亡不足10人的代价,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野蛮屠杀了使用大刀长矛的西藏人近千人,这样血腥的事实永远不会从历史中抹去。
六、江孜保卫战
江孜是山南通往拉萨的门户。英军抵江孜不到一个月,藏军就有一万多人聚集到江孜、日喀则及拉萨到江孜的大道上,准备保卫江孜。
1904年4月5日,英军开始入侵江孜,沿途即遭到西藏军民的阻击,双方在雪那寺展开激战,藏军伤亡100多人后撤退下来,英军占领了雪那寺。4月9日,英军向峡谷的藏军进攻,藏军在山脊上进行射击,随后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藏军奋战6个小时之久,打死打伤敌人280余人,藏军共伤亡150余人……杂昌谷地阻击战,虽然没有达到阻止英军继续前进之目的,但却充分表现了西藏人民不惧强暴、不怕牺牲的抗英勇气,再次向侵略者表明:西藏人民是不容欺负的!
4月11日,英军抵达江孜,先占领了江错白地,进而又占据江洛村。13日,英军占领江孜宗政府所在地,即江孜炮台。英军在此大肆掠夺,抢去了100吨粮食、若干牛羊肉干和数吨火药,并摧毁了宗政府。随后,他们便驻扎在宗政府附近的江洛林卡,将“包括它在河岸边的田庄与外部建筑改造成一个防御堡垒……军队在空地上扎营,把佛堂改成食堂。
在江孜的英军遭到了西藏军民的袭击。5月1日,英军发现距离江孜东47公里处有藏军集结,修筑了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于是决定分兵前往。5月5日黎明,一支800人组成的藏军从日喀则赶到江孜英军大本营,发动了突袭。英国军官瓦代尔(Colonel Waddell)描述藏军此次突袭:
那天夜里,或更确切说是凌晨……我们突然被西藏人古怪的战斗呐喊惊醒。他们几百个声音嘶哑的西藏人,在我们的矮墙外几码的地方,突然尖声大叫……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此过了几分钟我们的卫兵才进入阵地开始还击。
此次突袭险些令荣赫鹏丧命。藏军突袭虽然被打退,但却夺回了江孜宗政府炮台及附近几个村,形成对英军大本营的包围。而江孜谈判却一拖再拖,正好成为荣赫鹏进攻拉萨的借口之一。被围困在江孜的英军在粮食给养等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5月24日,一支增援江孜的英军部队抵达,暂时改变了英军的困境。26日,英军集中兵力向东边帕拉村藏军阵地发动进攻。经过11个小时的激战后,英军最后占领了帕拉,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战斗中,藏军无比英勇,英侵略军军官瓦代尔写道:
西藏人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坚决、机智和英勇,对我们这些亲眼目睹他们袭击我们营地的人来说,不足为怪。说西藏人不能打仗,这种荒谬的错觉应该彻底打消了。他们的英勇举世无双。
6月13日,荣赫鹏、麦克唐纳等率军从春丕出发,到江孜解救被围困的英军大本营,并准备进军拉萨。英军增援部队抵达江孜后,英军官兵总数达到4600人,还有3800名运输及服务人员,总计11500人以上。为了解除被藏军围困的处境,英军在6月28日向宗政府左侧的紫金寺发动了进攻。紫金寺是一座著名古寺,矗立在一座小山上,控制着江孜通往日喀则的道路,当时有藏兵200余人、僧兵30多人守卫。后来藏军援助塔工的300民兵和100僧兵增援该寺,一场紫金寺保卫战打得异常激烈。藏军多次勇敢地击退敌人,但狡猾的英军从四面围攻紫金寺,并用炮火不断轰击,最终占领了紫金寺。
紫金寺失陷后,英军便集中火力进攻江孜宗。而鉴于藏军在江孜接连失利,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采取战和相结合的策略。7月1日,噶伦抵达江孜。2日,双方进行了会晤,英方以武力要挟藏方签约,但其条件藏方无法接受。3日下午,西藏谈判代表到达谈判场所,荣赫鹏借口其迟到,推迟了4个小时才开始谈判。会上,荣赫鹏强令藏方代表道歉,并要求藏方在7月5日正午前撤走江孜炮台的藏军,否则和谈终止,诉诸武力。这些要求遭到藏方代表严正拒绝。
7月5日,英军在做好一切准备后向江孜宗政府发动进攻,西藏人民的江孜保卫战进入了决定性阶段。下午1时40分,英军用大炮猛烈轰击江孜城区和宗政府所在地的炮台。3时半,部分英军佯攻炮台以吸引藏军主力。半夜,英军兵分两路偷袭了江孜东南隅。翌日天亮后,英军分三路向城区发动全面进攻。守城藏军顽强抵抗,用礌石、滚木、飞蝗石坚持战斗,迫使敌人几次后撤。最后,守城藏军实在不能坚守,索性打开城门,冲出城去与敌军决一死战,西藏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每一寸领土。直到下午2时,英军才占领城区。7月7日午后,英军向江孜炮台发动总攻。炮台内约有五六千藏军,他们毫不畏惧,多次打退英军的进攻。到了下午7时,英军才用大炮将炮台城垣炸开一个缺口,从缺口冲进炮台。抗击到最后的数百藏军全部跳崖牺牲。西藏军民退守八角曲登。英军继续围攻八角曲登,西藏军民一直战斗到弹尽粮绝,才趁夜冲出了敌人防线。江孜宗山被英军攻陷后,白居寺又被攻占。英军旋即占领整个江孜。
江孜保卫战从1904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持续了约100天,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西藏人民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宝贵财富。
七、拉萨陷落
江孜保卫战后,英国侵略军于7月14日由麦克唐纳率军从江孜出发,长驱直入拉萨。这支侵略军携带大炮8门,马、步兵及运输、辎重人员各2000名。17日,当英军行至噶惹拉山时,遭到1000多名藏军的阻击。藏军在原有阵地修建了两道防御墙。18日,英军发动进攻,遭到藏军顽强反击。这次战斗中,藏军再次表现出英勇的大无畏精神,就连其敌人坎德勒也大加赞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目睹了藏人的英雄主义行为,这也大大改变了我对这些人的估价。”
7月27日,荣赫鹏照会驻藏大臣有泰,说英军已抵曲水,将入拉萨。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多次请求有泰赴曲水劝阻英军勿入拉萨,有泰也严词拒绝。7月26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召见噶厦主要僧俗官员,宣布“我已决定离藏,先去蒙古,再赴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我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想尽各种办法,保护佛法和政教宏业”。达赖喇嘛授权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主持政务,并要求大家不要告知驻藏大臣。7月28日,达赖喇嘛携带少数随员秘密离开了拉萨。
8月3日,英军进入拉萨。
八、“拉萨条约”
在到达拉萨之前,荣赫鹏已经意识到,他必须直接贯彻寇松的政策,因为寇松在1904年4月请假去了英国,到12月才能返回印度。而在向拉萨推进的最后关键阶段,庵士尔勋爵(Lord Ampthill)成了印度总督,他与寇松的个性大相径庭。此外,因麦克唐纳认为9月15日之前军队务必离开西藏,荣赫鹏为此与之发生了冲突。荣赫鹏不愿自己千辛万苦即将得来的成果付诸东流,坚持要等条约签订后才肯离开。
9月1日,荣赫鹏迫使有泰召集代理摄政、噶厦官员、代表举行会议。当时,英军全副武装经过拉萨市区到驻藏大臣衙门,进行武装示威。会上,荣赫鹏拿出早已拟好的条约十款(汉、英、藏三种文字)交给有泰,限其一周内与英方订约。条约内各款要求只许解释,不能讨论。荣赫鹏声称,条约中的赔款自英军在江孜受到“攻击”后算起,到条约签订后一个月为止。“每天五万卢比计算,如果明日可以签约,则总数为750万卢比;如果延长到9月3日签约,则为755万卢比;如再延长到9月4日,则为760万卢比,以下类推。”西藏代表表示,如此巨大数额藏方无法偿付。
9月4日,西藏地方政府被迫同意在英方所拟条约上签字,仅提出赔款限期3年付清,改为以每年10万卢比交付,75年偿清。5日,荣赫鹏与驻藏大臣、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讨论了签订条约的形式与最后手续。为显示英国在西藏的权力,荣赫鹏强迫西藏地方代表同意在布达拉宫举行签字仪式。
9月7日(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军在布达拉宫严密设防,并用大炮对准布达拉宫,城下之盟“拉萨条约”就这样被迫签订了,西藏代理摄政在条约上盖好了达赖喇嘛之印,其余噶伦、三大寺代表及僧俗官员会议代表分别被迫签字。
荣赫鹏提出的条约内容大致如下:
鉴于对1890年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1893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之含义与有效性,以及在这些条约之下西藏地方政府的责任有所怀疑并遇到困难;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给英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和理解造成了干扰;鉴于双方都希望重建和平与友好关系,解决上述所言疑虑与困难,英国政府已决定,就这些内容签署条约,以下条款由荣赫鹏上校全权代表英王陛下政府,由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仁波切、噶厦及色拉、哲蚌、甘丹等三大寺代表,以及国民大会(即春都)的僧俗官员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同意:
第一,西藏地方政府承诺尊重1890年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承认该条约第一款中所给出的对锡金与西藏之间的边界线的划定,并相应建立界石。
第二,西藏地方政府增开两个新的贸易市场,即江孜和噶大克为商埠,和在亚东所开商埠一样,所有的英人和藏人都有权自由进出这些口岸。
1893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适用于亚东贸易市场的条款规定,也应当在英国、西藏双方一致同意前提下,适用于上述新开辟的贸易市场。
除了在上述地方建立贸易市场,西藏地方政府必须保证,不可对已有贸易路线加以限制,如果贸易的进展需要,需考虑在同样条件下建立新的贸易市场之问题。
第三,1893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保留容后再议的问题,西藏地方政府必须保证任命完全授权的代表与英国政府代表就修改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协商。
第四,西藏地方政府保证,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
第五,西藏地方政府保证,务必保持通往江孜和噶大克的路途畅通,并从英方贸易代表处向中方以及藏方政府传递信件。
第六,藏赔偿英军费50万英镑,即750万卢比,每年年初交付10万,分75年交清,自1906年1月1日开始起付。赔款在英政府所指定之处缴纳。
第七,为保障赔款偿付的安全以及贸易市场的正常运作,英国必须占领春丕谷,直至赔款全部付清,及商埠妥立三年后为止。
第八,西藏保证拆除自英国边界至江孜、拉萨的所有防御工事。
第九,西藏保证,未经英国人的同意
(1)西藏领土的任何部分不得被割让、出售、出租、抵押或被任何列强占领;
(2)不得允许任何列强干涉西藏事务;
(3)任何列强的代表或列强的代理人都不得进入西藏;
(4)不得授权给任何列强铁路、公路、电报、开矿或其他特许权。在同意任何列强获得此类特许权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应当获得相似的或同等的特许权。
(5)西藏的收入,无论以现金或者以别的方式,都不得允诺或给予任何外国,或者任何外国的属国。
第十,本条约共缮5份,于1904年9月7日即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由商定之员在拉萨签字。
条约的附约为独立条款,允许英方驻江孜的贸易代理人在其认为合适的时候访问拉萨。
11月11日,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了“拉萨条约”,但对其中的条款作了单方面的修改:原约规定的75年还清750万卢比改为3年还清250万卢比。因此,英军占领春丕的时间也相应由75年改为3年。同时,英国驻江孜代表有权进入拉萨的附款也被废除。
20世纪初,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英国适时调整对西藏政策,进而修改“拉萨条约”,不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怜悯而突然大发慈悲;相反,英国修改条约是担心过于苛刻的条件会引发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从而在更长远的层面上影响大英帝国的利益。
“拉萨条约”一经公布就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在签约过程中,荣赫鹏多次诱迫有泰在条约上签字。有泰犹豫不决,何光燮劝阻其不要画押,认为其应当先向外务部请示。在有泰请示外务部之后,清廷立即于9月8日电告有泰:“英员开送十条,有损中国主权,尊处切勿画押。”接连几次电令有泰“切勿画押”。但有泰9月13日才收到此电报。所幸有泰当时没有画押,才未酿成大错。
“拉萨条约”是缺乏法律效力的非法条约。首先,“拉萨条约”并非主权国家代表签订,清朝驻藏大臣有泰并没有签字,故没有法律效力。何光燮认为有泰应当先向外务部请示。在有泰请示外务部之后,清廷几次电令有泰“切勿画押”。可见,中国政府并没有同意“拉萨条约”,而有泰也没有在条约上签字,仅西藏地方代表签字的条约是无法代表中央政府的。因此,在没有清朝中央政府授权,没有驻藏大臣签字,也没有十三世达赖喇嘛授权签约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等人擅自签订的“拉萨条约”,显然是非法无效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只有主权国家才有“缔结条约之能力”。其次,“拉萨条约”是英国武装入侵西藏后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条约,不符合国际法自由平等签订条约的规定。荣赫鹏等率英国军队在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非法侵略中国西藏,兵临城下,用武力威胁手段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条约,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粗暴践踏。
通过两场侵略战争,英国无疑扩大了其在西藏的影响。历史上西藏僧俗上层中亲英派的出现始于此时。此外,英帝国主义者经过侵藏战争之后,认识到无法靠武力来征服这片高原,因而在西藏僧俗上层中培植亲英势力,鼓动、怂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对抗,试图用这种办法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或者附庸,变为保护英属印度东北边境的一个“缓冲区”。这一切,正是当年帝国主义者所惯于采取的手段。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当年列强犯下的侵略罪行,怂恿、鼓动“西藏独立”的图谋,以及其注定失败的命运,已为世人共睹,也必然给当今世界带来深刻警示。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