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邹立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青藏高原东缘歇家、锅庄与旅马店等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互惠交换传统。互惠交换传统主要依托贸易伙伴关系,为藏族商人、农牧民与外来交易者通过贸易中介从事族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本土的物资交易逻辑和社会交往渠道。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同中有异,出入于经济与社会之间,分化出以歇家、锅庄为代表的区域类型。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族际贸易中介和各族商人群体习得、效仿互惠交换传统,走出城镇,将贸易伙伴关系反向运用于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开拓出双向的族际贸易途径。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互惠交换传统的发展趋势出现分化,产生出新的族际贸易中介。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揭示出青藏高原社会经济东向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历史进程,以及藏族与中华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深度交融的多元面向和地域特色。
【关键词】互惠交换传统;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经济;社会
青海歇家、康定锅庄和滇西北旅马店是历史上青藏高原东缘重要的贸易中介组织或中间人群体。这些贸易中介处在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地理分界、经济交汇的城镇内,长期承担着藏族商人、蒙藏农牧民与汉、回、纳西等族商人的贸易沟通作用。歇家和锅庄往往被视为明清以来“歇家牙行”经营模式在青藏高原东缘的表现形式,其经济属性、金融功能和政治职能受到普遍重视,被置于不同区域历史脉络中加以类型分析和横向对比。滇西北旅马店常在对比分析中被忽略掉。但是支撑旅马店的“房东伙伴”贸易或“藏客”借用的乃仓关系透露出:青藏高原的互惠交换关系应是促成族际贸易中介形成的重要动因。对于康定锅庄的新近研究进一步表明,非经济视角对于阐释此类贸易中介相当重要。既有研究为探索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演变和运作机制开拓出新思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拘泥于特定区域或具体案例,缺乏整体视角下的区域类型比较,对于青藏高原互惠交换传统与族际贸易中介的内在联系,及其族际共享关系有所忽视或论证不足。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区域类型与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密切相关,揭示出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在经济与社会之间:青藏高原的互惠交换传统
借助中介从事物资交易是青藏高原的传统贸易习惯。族际贸易中介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向南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北麓的半月形地带,特别是青藏高原东缘,比如歇家、锅庄、旅马店、乃仓、康马房东、帕里落脚住户、吉隆房东、阿里“敖协”等。不同区域的贸易中介商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有别,又有藏、回、纳西、蒙古、汉等民族身份的差异。商人或农牧民与交易对象按照惯例,通过委托有密切社会联系的中介,有条件地获取食宿、担保、借贷、仓储、资讯、运输等资源,向经纪人角色的中介支付约定报酬,完成商货交易。
以盐粮交换为代表的民间物资交易活动是青藏高原广泛存在的经济交往联系。由于高原环境的物质产出相对匮乏,资源分布的区域或阶层差异显著,历史上青藏高原长期普遍存在着获取生存资源的交换需求和互帮合作。历史悠久的盐粮交换是典型的民间物资再分配和互补交易活动。藏北盐粮交换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牧民利用驮畜优势,自发驮载食盐和剩余畜产品,季节性地远赴农区,交换粮食、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物资交易活动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互惠准则和交易传统。
农牧区之间的垂直贸易大多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路线和定向的交换范围。如藏北牧民每年春季赴盐湖采盐,到秋季从北向南沿着四大传统路线进入低海拔的藏南农区城镇、村寨,从事盐粮交换活动。近代安多牧民每年秋冬时节携带羊毛、畜产品等大致从西向东前往甘青交界处,或向南进入川西高原半农半牧和农区村镇交换粮食、茶叶、布匹等。具有亲属关系的家户是牧民抵达目的地后必选的落脚处,绕开亲戚另选农户的行为禁忌将损害亲属关系,但是亲属关系的延伸地域相对有限,贸易伙伴能够填补互助空缺,是定期、定向物资交换的重要合作者。因此,农牧民从事物资交换活动,通常与两类群体建立互惠的协作关系,即亲戚和贸易伙伴。
互惠是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深刻影响着藏族人的世界观和日常社会生活。农牧民与手工业者、商人基于互惠交换需求,“为了长期的贸易,在社会关系的保护下出现了‘贸易伙伴’机制”,形成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无声交易”。贸易伙伴关系属于个体间的社会交际范畴,在远距离的交易活动中颇为流行,构成了青藏高原互惠交换传统的重要维系力量。
贸易伙伴大多是自主选择或熟人推荐。20世纪50年代以前藏北牧区的贸易伙伴互称“夏波”(ཤག་པོ),意为朋友、熟人,引申为“住宿的人”。双方初次交易时“勾指起誓”,结为彼此信任的夏波关系,声称“盟友勾指会更近,亲缘勾指会疏远”。这一说法体现出贸易伙伴与亲属的实质区别。盟誓监督和互助原则杜绝了贸易伙伴随意更换的行为。双方信任关系可以代际传承,乃至结为世交或姻亲。这种社会关系影响了物资交易方式,双方一般按照约定比率进行物物交换,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场面。商人或农户灵活地采取延时等价交换:“头年向牧民分发货物后,来年方才收回所易畜产品,叫做‘留后’。”延时交换习惯受到社会规范制约,适应了农牧区多变的自然气候与生产周期规律,后来逐步演变为青藏高原东缘不同民族间的赊销贸易。
熟人推荐更易于贸易伙伴关系的建立。藏族社会属于典型的“熟人”关系社会。在历史上,行旅“没有熟人预先介绍的,可以说在草地是寸步难行”。安多牧区的外来者“经人介绍过或者带着某人的介绍来到帐房和主人建立正式的主客关系”。引荐者承担推荐的义务,“通过介绍受接待并建立主客关系”。主客关系是农牧区人际交往的日常社会联系,在交易活动中自然而然地与互惠交换传统结合。主客关系成为互惠交换传统的结构性要素。主客身份由于互访,时常发生转换。物资的跨区域流动通过接力式的主客关系,拓展了青藏高原经济地理空间的社会联系。
待客之道与礼物交换是维系互惠交换传统的动力。近年来人类学关于待客(hospitality)的研究表明,待客之道是一种规避社区风险的机制,产生出秩序和整合的力量,衔接和稳定外来陌生人与主人社区间的关系。主人起到容纳社区内外社会关系的缓冲阀作用,以待客之道联系起社区内部人际关系与社区外部互惠交换关系。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显示,安多牧民的待客之道由一系列规范主客关系的分享准则和交换行为构成。针对穆斯林商人在内的贸易伙伴,牧民需要妥善处理社交礼仪、安排食宿、安全保障、照料驮畜、向导护卫、协助交易等事务。“让出第一桶水让客人备饭用”是主客亲密关系的象征性表现。主客关系交织起的社交网象征着社会声誉和权力地位,“主客关系的网越大”,主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也越高”。因而代销、食宿和寄存等往往是待客之道的义务性功能。20世纪50年代初藏北牧民与农户贸易伙伴进行交易时,“牧民交换不出去的东西,或遇农区不好的年景,就把畜产品留放在房东家,第二年再来卖。房主人不一定是和房客交换的主要对象,但是可以通过房主人的关系,向其他农户,赊一些青稞运走,第二年再送还畜产品”。义务性功能未必同时具备,互助意义却远远大于盈利目的,具有社会道义和个体情感基础。
馈赠礼物主要是外来者履行主客关系的义务和途径,与待客之道互为表里,共同维持着礼物背后的人际关系。近代德格色普卡牧区与甘孜绒坝岔农区长期保持着陶器、豆麦等物资的交换习惯。绒坝岔富有的家户与牧民结为固定的主客关系,是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牧民驮队每年秋季到来,都会向房东赠送酥油、肉、奶渣等礼物。对于房东而言,由于缺乏燃料,最具价值的额外馈赠是易燃的牦牛粪。近代西藏商人也总会为旅途中遇到的贸易伙伴带些礼物,“时常邀请主人一起分享他们带来的丰盛食物”。馈赠礼物是稀缺物资通过赠予和接受来实现跨区域流动的途径。消费性的农牧副产品,特别是食物,构成了馈赠礼物的主要部分。这意味着礼物分享的互惠关系依然伴随着生存资源互补的需求。
尽管存在地域差异,青藏高原互惠交换传统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波兰尼关于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行为中的见解。物资交换活动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更触及青藏高原社会道德伦理、家庭生活、人情关系、权力声誉等不可物化的层面。
二、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
有关青藏高原东缘贸易伙伴关系转化为族际贸易中介的明确记载见于清代前期,这一时期也是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形成的关键阶段。在滇西北,康熙三十年(1691)和硕特蒙古巴图尔台吉颁给建塘独肯宗(今香格里拉中心镇)土司松杰衮执照,承认和保护其统治权力,理由是“独肯宗松杰衮家,过去为藏商房东(གནས་ཚང),对所有藏商(གཞུང་གི་ཚོང་པ),备极优礼关照”。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七世达赖喇嘛颁给土司松杰的执照中旧事重提,“建塘独肯中心属卡松杰者,自其祖辈松杰衮以前,纳西王(“འཇང”指丽江木氏土司——引者注)统治时期,即为藏商之房东,对藏商多有帮助”。“房东”即“乃仓”(གནས་ཚང),意为“借宿之家”。乃仓关系流行于川滇藏毗邻区域,主要是旅外者借宿的民间互助行为,尤其出现在农牧区的物资交换活动中。乃仓男性主人、女性主人分别被称为“乃布”(གནས་པོ)、“乃姆”(གནས་མོ),与“夏波”(ཤག་པོ)共同构成了青藏高原不同区域贸易伙伴的称谓。
在滇藏贸易拓展背景下,明末清初乃仓关系转变为接待客商的房东制。独肯宗松氏土司兼充藏商房东是其早期历史写照。乃仓房东起初是属卡制度下拥有门户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固定成员。外来商人受属卡制度禁约,需要依附属卡成员,才能入住或落户经商,房东制应运而生。雍正初年丽江改土归流后属卡制度趋于瓦解,乃仓房东操控商业交易的局面被打破。但是,滇西北城镇的乃仓房东面向藏族商人及鹤庆、丽江等地客商,逐渐发展为提供食宿、货栈、安全保护、代理购销和担任保人等服务,从中抽取佣金的贸易中介。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旅马店产生于清代前期,是商业化的乃仓关系随着藏商贸易活动向丽江推移,与滇西传统马店、堆店(即货栈)结合,衍生出牙行经纪功能的产物。旅马店店主与商户“匆爸匆沙”(ཚོང་པ་ཚོང་ཤག)、纳西族商妇(习称“潘金妹”)都是藏商在丽江的主要贸易伙伴,三者的身份时常重合。藏商将旅马店店主称为“嫩蚌”(即乃布)。“匆爸匆沙”应是藏商对贸易伙伴的特定称谓,也就是商人(ཚོང་པ)与“夏波”(ཤག་པོ)的合称。乃仓关系的嬗变可视为青藏高原东缘贸易伙伴关系与族际贸易中介之间内在联系的缩影。
这种嬗变的外在动力应是明代中叶以来的商业民营化趋势导致沿边贸易中“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出现。明末清初青藏高原东缘的官营茶马贸易逐步转变为商人自主营运为主导的民间贸易,形成与内地市场衔接的川藏、青藏、滇藏为主体的贸易网络。族际贸易亟需中介联络沟通。由于嬗变路径、环境的差别,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在内生、外源驱动力的影响下分化出以歇家、锅庄为代表的区域类型。
青藏高原东缘的族际贸易中介主要是藏商或蒙藏农牧民的落脚住处和交易场所。青海歇家“实为招待蒙番寄顿土货之所”。康定锅庄“如内地之洋行或饭店,盖即藏人栈房,代藏商买卖之所”。因而族际贸易深受青藏高原传统交易逻辑的影响。民国时期甘青地区“藏民忠厚重感情,对汉回商民人情交往上,往往养成‘认熟不认生’与‘认话不认人’之习惯”。即便在零售交易环节,普通藏族,特别是牧民经常倾向“直接到他相识而有往来的蛮商或汉商地方去讲生意,暗中交涉。以致一个新到此地的人,想从生产者的手中买到东西,那是不容易的事”。面对外来的交易者或流动商人,藏商或农牧民习惯于遵循熟悉的交易逻辑,即稳定、熟识的社会关系是开展交易的前提和保障。
青藏高原与内地之间的贸易联系主要基于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特别是在毗邻安多牧区的甘青沿边和川西北地区,歇家大多分布在农牧分界地带的城镇内,这也是安多牧民从事传统农牧物资交换的主要区域。自明初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的西北甘青沿边贸易空前活跃,不断吸引来自牧区的交易者远赴卫所、州县的茶马司或“番市”进行交易。牧区交易者习惯性地投宿于熟识之家,“自建茶马司以来,诸番悉假居民舍”。到康熙年间,前往甘青地区各城镇的牧区交易者“同其妇子,驱其马牛羊,挈其缨皮之类,而来市者,悉寓民房,称一家人”,以致“国朝初,诸番往来,尽居沙塄歇家”。“称一家人”的描述形象地反映出牧区交易者与市镇民众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亲密状态。从“假居民舍”到“尽居沙塄歇家”是贸易伙伴关系逐步被引入族际贸易,发展出歇家中介的早期实践过程。
为满足藏商或农牧民家居习惯,歇家一般由宽敞的院落、仓库、住宅、厨房和畜圈等功能性区域构成。康熙初年,西宁以西的多巴(今湟中多巴镇)互市之地“黑番、回回筑土室成衢,为逆旅主人。凡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为居垄断”。至道光年间,河州(今临夏)回民“于贵德城外典凭民房私做歇家”,“招留各番子住歇”。因此,歇家从无到有,大多因贸易而兴。回、汉、藏、蒙古等族歇家经营者主动迎合藏商或农牧民寻求贸易伙伴的交易惯例,仿照其居住形态,筑院落成旅店,充当家庭式的交易场所。
与歇家相比,康定锅庄原本是较有地位的家臣、头人等权力阶层为明正土司分担各项差务,接待来往的所属土职及朝贡使节,并代为交易他们所携货物的场所,本质上是土司政治体系运转的组成部分。明末清初,康定逐步发展为川茶输藏、汉藏贸易的重要集镇。乾隆《雅州府志》载:“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跋涉而来的商队逐步世代定向入住锅庄。清末曾任理塘粮务的查骞称,锅庄为“供明正土司役者”,“多以夷妇为主,经纪商务”。女性主人被称为“阿家”(ཨ་སྐྱ)或“纳摩”(即乃姆)。男性主人则被称作“乃补”(即乃布)。可知锅庄的贸易中介功能仍由主客互惠的乃仓关系衍生而来。
康定锅庄直到清末才作为贸易中介明确出现在文献记载中。这暗示锅庄政治职能的重要性最初远超其经济角色。而且,康定锅庄具备藏族家庭的基本组织功能,属于家屋社会性质。主客关系是“发源于关外某处,或祖上某些男人或女人是某几处人,他们来往的客人也以某几处人为主”。锅庄的继承和占有通过灵活的联姻和继嗣交替进行。交替继承的规则将主客关系内化于锅庄的亲属关系中。如1920年左右大园坝罗家锅庄绝嗣后,“由寡媳招关外人入赘。媳死,此赘婿娶妻,赘婿又死,此女再招夫。所招夫媳均昌都人,来往商人,也以昌都人为主”。由此,贸易伙伴关系与亲属关系交织在一起。锅庄主客的交易联系深深嵌套在家屋社会结构中,属于“家庭型的商业组合”。学者谭英华敏锐地指出,锅庄脱胎于“土著康人的家庭组织”,“是在西番土著中生长起来的社团,而非外来的其他社会的商店”。实际上,锅庄贸易中介的经济属性逐渐取代传统的家户农牧经济特质,主要是清末改土归流后锅庄主失去政治特权,愈加依赖贸易谋生手段,不断商业化,发展出经营性锅庄的转型结果。康定本地人通常将清末改土归流后兴起的经营性锅庄与传统锅庄严格区分开来。经营性锅庄趋同于内地货栈、邸店等中介组织,以营利为目的,已然失去传统锅庄根植于藏族家庭的社会属性和人际关系,改变了主客之间的内在联系。两者的差别体现出社会关系对于传统锅庄主客交易联系的意义。
从经济功能角度看,以往的调查研究简单地将康定锅庄等同于青海歇家,称“‘歇家’犹类康定之‘窝庄’”。上述分析表明,两者形成的社会基础、初始动机、运作机制和发展趋势同中有异,各具特色。这造成不同类型族际贸易中介商业化表现的差异,潜在地影响了近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族际贸易中介区域演进的不同发展轨迹。
三、互惠交换传统的族际共享与新的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
歇家、旅马店或锅庄并不只是在城镇内被动地等待远道而来的藏商或农牧民,有意或无意的回访是常有之事。康定锅庄即使无法完成交易,对于“康人过此住宿,亦均加以招待”。锅庄主“赴草地,彼等亦殷勤招待,除供宿处外且供食品”。作为客人,川西北杂谷脑(今理县)歇家“如果到番地时,也可歇在番商家中。这时番商就变成他们的歇家,也同样招待他们,替他们买卖货物”。所以在日常的族际贸易活动中,贸易中介与贸易伙伴实则难以截然区分,而是随着交易场景的变动而发生转换。
青海歇家更为重视贸易伙伴主客互动的商业潜力,将之转化为开拓高原区域市场的重要渠道。早在道光年间,青海回商定期外出贸易,住歇于蒙藏牧民帐房内,与之交好,乃至“结为兄弟”,学会蒙藏语言,以茶粮易换羊皮等,“遇有蒙古、野番进口时”,“私当歇家容留居住,为其置办口粮货物”。到民国时期,因应西北皮毛贸易的繁荣,不少青海歇家从平津、湟中等地购进商货,每年春季“派人运茶布等货,至青海内部,放账于各番户,言明秋后送毛若干斤,羊皮若干张。待至秋后,各番户以牛群或骆驼队运羊毛、羊皮等货来湟,偿还欠账,倘有剩余,则易为日用品以归”。“春放秋收”的赊销贸易与接待藏商、农牧民驮队的中介贸易成为青海歇家面向高原区域市场的双向交易方式。放账时,牧民赊取商货并不记账,只需要提前商定以物易物的交换比率,但是“放账与收账者必须原人情理,否则收账时可以置而不答,然一俟原经理人到幕,则又如数履行偿还债务,决无纠葛”。所谓“原人情理”,即遵循互惠交换传统中“认熟不认生”的交易者主体关系原则。歇家派出个体私商“客哇”(ཁེ་པ)充当“经理人”,完成赊销贸易。“客哇”根据歇家与牧区部落的关系,确定业务范围,抵达牧区后“彼等将各种货物,运至一处,即插帐以居,每至一处,即设法认识一该地夙有声望之人,为之介绍当地居民,作种种交易,谓之‘主人家’”。为适应近代转型的沿边贸易,青海歇家突破了等待客商到来的单向度中介经营方式,走出城镇,主动运用熟稔的贸易伙伴关系,以个体私商串联起同各个牧区部落的经济交往联系,将双向的主客关系转变为出入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的经商途径。
随着清初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贸易网络的形成,各族商人在长期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也逐步熟悉和意识到互惠交换传统的重要性,成为践行贸易伙伴关系的重要推动力量。青海循化、尖扎、化隆、贵德等地藏族与擅长经商的撒拉族、回族结为“许乎”或类似关系,是青藏高原东缘贸易伙伴关系族际实践的代表性事例。“许乎”是安多藏语ཤག་པོ(即“夏波”)的音译。不管是物资交换的产生根源,抑或待客、礼物交换和义务性功能等维系方式,“许乎”关系均与藏族物资交换活动中的贸易伙伴关系运作机制如出一辙。互惠交换传统已通过贸易伙伴的日常交往,内化为青藏高原东缘多民族共居区域内共享的社会经济惯例。在滇藏茶马古道上,清代中叶以来的纳西族“藏客”为了物资补给,会在沿途的每个村寨选择“主人家”(即乃仓),结为粮草供给、代购代销的互助关系。常年流动的“藏客”出入青藏高原,将互惠交换传统借用和融入跨区域的滇藏长途贸易活动中。
事实上,“走藏地”或“走口外”是各族商人自发深入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推动互惠交换传统实现族际共享的重要途径。“走藏地”的多数商人群体以私商、行商为主,通常会在旅途中合组商帮,抵达牧区后化整为零,各投主家,分散到固定的贸易伙伴家户中。民国时期甘南回、汉商人,特别是临潭西道堂穆斯林商人的经商地域遍布川甘青交界地带,远达甘孜、玉树等地。各族商人入乡随俗,“凡初赴藏地经商者,须有熟人为导,认定其中一家为主人曰‘认主家’,致送相当礼物曰‘按茶’。主家既经结认,以后即可自来,卖买均由主家介绍,极为方便”。川西北回、汉商人定期赴牧区收购皮货和鹿茸,“恒投止于土官或百姓之家,称为自己之主人。番人对之称之曰自己之汉人”。面对外来的各族商人,农牧民以互惠交换传统的信用原则和责任心态予以接纳,规范主人应尽的待客义务,“汉商是客,他们是主的地位,所以对于汉商特别优遇之外,自己不惜牺牲一切的替商人放账,同时介绍了许多陌生的顾客”。主客关系的责任共识和习俗惯例,对农牧民具有示范性的社会约束力。在某种程度上,农牧民贸易伙伴的待客行为不仅是为了获取粮布等生存资源,也有维护其社会声誉、权力地位和人际关系的考虑。
在近代安多牧区的贸易活动中,“来访人的身份和安全同样取决于客主关系的运作,而正是这种关系使得穆斯林商人能够在藏区旅行贸易”。以商为业的穆斯林商人总是“设法让自己努力适应藏族人的营地生活”。在川藏道上,陕商商号派遣的店伙进入农牧区前,须学习和掌握简单的藏语,熟悉藏族的生活习惯,“经人介绍以某处为宜,即携货前往,至则择主而居,房饭不出分文。盖藏俗买卖出入,有主人三分手续费,以致殷勤招待”。各族商人往往在衣食住行等外显文化表征上主动效仿和接近农牧民,尽量消除因族别不同而造成的文化与心理隔阂。一次次造访贸易伙伴家户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习俗不断接触、调适和交融的过程。贸易伙伴关系存在着被外来商人普遍习得和运用的反向过程。
由此,青藏高原东缘逐步呈现出一个有趣的族际贸易格局:藏商或农牧民从零到整,组建起成规模的商帮驮队,长途跋涉后走进城镇,受到歇家、锅庄、旅马店等贸易中介的定向接待;青海歇家、陕商商号等走出城镇,如同“走藏地”的各族商人,化整为零,分派“客哇”、店伙等个体商深入农牧区,得到固定贸易伙伴家户的款待和协助。藏商、农牧民或贸易伙伴家户及其所在的区域社会,以不同形式参与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商贸交流。
族际贸易活动从城镇拓展到农牧区的重要结果是,近代不同区域互惠交换传统发展趋势的分化与新的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由于城镇发育和商业化发展程度有别,川藏道沿线城镇的贸易伙伴关系不同于甘青农牧区,逐渐蜕变出新的贸易中介。作为贸易中介,锅庄实际上遍布于川藏道沿途重要村镇,“康定以西各县份早年商业中心,皆在锅庄,按锅庄即内地之行栈”。牧民赴村镇贸易,各有其世代相承的锅庄贸易伙伴。“走藏地”的商人若要打开贸易局面,需要“学会康语,多跑锅庄(康人的旅馆及交易所),结交一些如经纪人的蛮家,树立商场信用”。康定以西的锅庄以道孚最具代表性,类似于清末康定的经营性锅庄。道孚的十余家锅庄由陕商和少数藏商经营,充当中间代理商,将牧民运来的青海盐巴、康北畜产品等转销到康定、丹巴等地。至于锅庄的本土称谓,民国报刊插图标题“西康炉霍之锅庄主妇”,被翻译为藏文“ཤེས་ཁམས་ལའུ་ཧོ་གནས་ཁང་ནང་གི་གནས་མོ”。“གནས་མོ”即乃仓的女性主人。甘孜货栈主人家也被称作“里布”(即乃布),专门向外来商人提供堆放货物、代理购销和食宿之便。可知康定以西的“锅庄”在本土语境中对应“གནས་ཁང”或“གནས་ཚང”,同样是基于乃仓关系而形成。新的族际贸易中介是商业运营模式沿着川藏商道反向影响沿途互惠交换传统的集中体现,与甘青牧区、滇藏道上的“主人家”共同组成青藏高原东缘互惠交换传统族际共享的多元图景。
四、结语
从整体视角探讨历史上的青藏高原东缘的族际贸易中介,为我们重新审视歇家、锅庄、旅马店等的产生源起、区域类型和族际共享关系提供了不同的思考面向。这些贸易中介的出现并非只是迎合明清以来青藏高原与内地之间日趋兴盛的民族贸易需求,市场功能的经营形态和获利方式无法揭示其完整的历史面貌。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和发展与青藏高原的互惠交换传统息息相关。
青藏高原的定向物资交换活动主要依托贸易伙伴关系逐步发展出互惠交换传统。贸易伙伴作为交易中间人,以待客之道和礼物馈赠维系主客之间的社会交往联系,寓经济行为于社会关系之中,构成流行于青藏高原内部的中介交易形式。互惠交换传统成为青藏高原物资交换活动与内地商业市场对接的本土资源,导引和影响着藏商或农牧民参与族际贸易的交易逻辑。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同中有异,分化出以歇家、锅庄为代表的区域类型。前者因物资交易而主动构建符合藏族商人、农牧民贸易伙伴需求的家庭式交易场所,后者最初依附于土司制度下的传统家屋社会关系,逐步从中发展出贸易中介功能。
青海歇家通过个体代理商群体,与西行藏地的各族商人将贸易伙伴关系反向运用于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开拓出双向的族际贸易途径。互惠交换传统的族际共享关系从点到面,由城镇向西扩展到贸易伙伴家户散落的农牧区。商人的活动使得互惠交换传统回归到个体间的社会交往层面。交易过程流露出义务、道德、情感、文化模仿等非经济的动机目的和互为取向。青藏高原东缘变动中的族际贸易秩序,呈现为近代互惠交换传统发展趋势的区域分化与新的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蕴含着明清以来各民族在青藏高原与内地经济交流过程中,自发构建族际物资交换体系的社会传统和经济智慧,也是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借助既有的民间互惠交换传统主动东向发展的结果。研究、考察这一历史社会现象,对于了解这一区域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及今日这些地区商业贸易、经济政策的制订等,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4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购书请扫码进入中国藏学官方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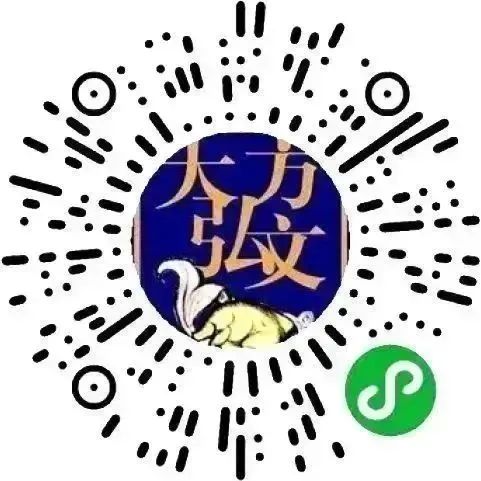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