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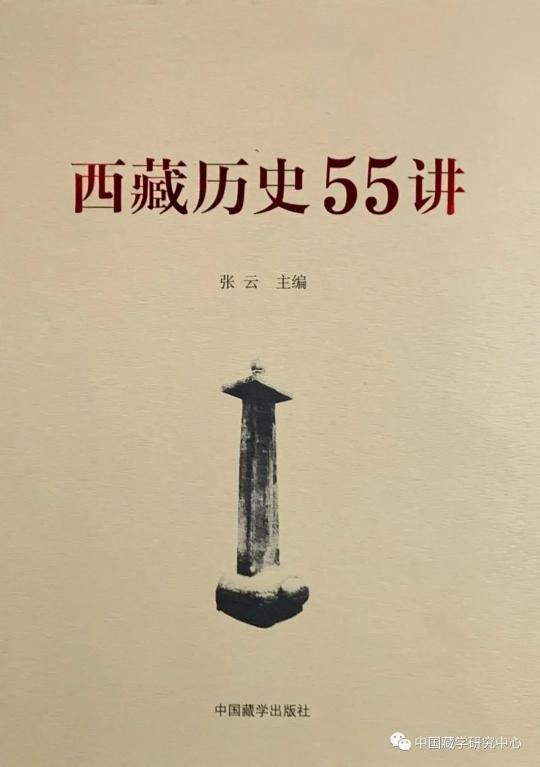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33讲 三世章嘉与乾隆皇帝
三世章嘉与乾隆皇帝,是藏传佛教高僧与清中央政府关系的缩影,他们君臣情谊深重,同谋大计,共同为维护边疆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三世章嘉的基本情况
章嘉呼图克图是清代格鲁派四大领袖(达赖喇嘛、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之一,被认为是西藏之东、漠北蒙古之南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其本寺是青海互助县的佑宁寺。“章嘉”初作“张家”,因一世章嘉扎巴沃色生于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而得名,由于康熙皇帝认为“张家”二字不雅,故将“张家”改为“章嘉”。章嘉呼图克图也是清廷四大呼图克图之首。
一世章嘉扎巴沃色(1578—1641),生于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明崇祯三年(1630)任佑宁寺法台,组织修建经堂,不断扩大寺院规模,为佑宁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崇祯十四年(1641)在佑宁寺圆寂。由于出生在张家村,在佛学方面具有杰出成就,因此人们尊其为“张家法王”,并由此开始了张家活佛转世系统。
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1642—1715)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因与其师西藏哲蚌寺高僧罗追嘉措(一世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一起前往蒙古喀尔喀部调解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之间的纷争有功,而受到康熙帝的推崇。康熙三十二年(1693)奉召进京,驻锡法渊寺,成为驻京喇嘛。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赐予二世章嘉活佛“呼图克图”封号,又封其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金印,被任命为驻京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掌管北京的藏传佛教事务,意在以其加强与蒙藏地区的联系。这是章嘉呼图克图任驻京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之始,也确立了章嘉呼图克图在驻京呼图克图中的领袖地位。整个清代,只有章嘉活佛系统一直被任命为国师。
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生于甘肃凉州(今武威),康熙五十八年(1719)被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意希认定为二世章嘉呼图克图的转世,经清政府批准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迎入佑宁寺坐床,二世却藏洛桑丹白坚赞活佛为其剪发并取法名阿旺却扎巴丹白坚赞。雍正二年(1724)正月因参与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而被清军俘获,然后被辗转押送到北京。因其年幼以及章嘉呼图克图在藏传佛教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清政府的处罚。雍正帝令其从二世土观活佛学习佛法。雍正五年(1727)雍正皇帝为其在多伦诺尔汇宗寺西南建善因寺供其驻锡。雍正十二年(1734),按照惯例,清政府正式册封其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金册金印,同年八月敕令随同第十七皇子果毅亲王允礼前往康区泰宁,迎请因避准噶尔叛乱而移居此地的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返回拉萨,向七世达赖喇嘛宣读了清廷册封的金册,并赠礼品,第二年三月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布达拉宫。同年十月抵达扎什伦布寺晋谒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意希,从其受比丘戒。
二、乾隆皇帝与三世章嘉的早年情谊
乾隆于康熙五十八年(1711)八月生于北京雍亲王府,本名弘历,为雍正皇帝第四子,年长三世章嘉5岁多。雍正二年(1724)三世章嘉到京后先暂住宏仁寺,后驻锡嵩祝寺,在雍正皇帝的安排下,经常与四皇子弘历同窗读书,学习汉、蒙古、满等文字,雍正皇帝还命三世章嘉认真学习大藏经《甘珠尔》经典,并命弘历同章嘉一起学经。弘历和三世章嘉共同学习,结下了儿时深厚友谊,为以后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驾崩,九月初三日,弘历继位,庙号高宗,年号乾隆,称乾隆皇帝或清高宗。三世章嘉闻雍正皇帝驾崩,遂于乾隆元年(1736)回到北京,朝见了登基不久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详细询问了三世章嘉前往西藏的有关情况。随后乾隆皇帝授予三世章嘉驻京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之职,令其掌管北京地区的佛教事务,开启了二位君臣共事、同谋政教大业的不凡历程。
不久,乾隆皇帝诏令章嘉:“如今佛教盛行于蒙古。遵照圣祖康熙皇帝之命已将《甘珠尔》译成蒙文刊行,然而蒙译全本《丹珠尔》前所未见。章嘉胡图克图宜董此事,将诠释佛语之所有论疏翻译成蒙语。”章嘉遵照圣旨,认真负责。在着手翻译前上奏乾隆:“大蒙古之各个地面,语音大致相同,然而细微差异仍有不少,特别是翻译经籍之名词、称谓尚未厘订。诸译者各随其意,译名各异,多不统一,致使闻修者难以理解,贻害匪浅。应将经典中名词的译法统一汇集,刊布发行,以利翻译。”皇帝大悦,降旨照此办理。于是章嘉活佛编写了题为“正字贤者之源”的凡例和译经规则,按般若、中观、上下对法(即集论与俱舍论)、毗奈耶(律藏)、宗派、密咒、因明学、声韵学、工艺学、医学、训诂学等类别,编写了前所未有的蒙藏两种文字对照的字典。以此为译经标准,由章嘉活佛和二世噶勒丹锡哷图(赛赤活佛)洛桑丹贝尼玛为主,汇集许多通晓经籍及蒙藏两种文字的大善知识,自藏历铁鸡年(1741)十月十五日起至水狗年(1742)十一月十五日止,全部译完。乾隆皇帝过目裁定,倍加赞赏,令御府付梓刊行蒙古文《丹珠尔》,流布于蒙古各个地方。
三、协助乾隆皇帝处理蒙藏边疆政教事务
由于乾隆和章嘉的特殊关系,自乾隆元年(1736)被任命为驻京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之职以来,章嘉已经成为乾隆处理宗教事务和蒙藏事务的顾问,经常受命协助清中央政府处理蒙藏地区政教事务,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请求乾隆赐匾,安抚青海寺院僧众。乾隆初年青海地区的一些蒙藏佛教寺院受到了当地汉族贪官和衙役们的破坏,为“使寺院受大皇帝颁赐的敕令的保护”,三世章嘉请求乾隆皇帝给塔尔寺、佑宁寺、广惠寺等寺院颁赐字匾。乾隆十四年(1749)三世章嘉返回青海讲经说法,将字匾颁赐各寺,其中,赐给互助佑宁寺“真如权应”金字紫匾一面,以及镶嵌珠宝的释迦牟尼佛像和敕书等;赐给塔尔寺“梵宗寺”匾额;赐给大通广惠寺“法海寺”匾额等。乾隆赐匾,使青海各寺受到尊重和有效保护,并促进了青海地区各民族间的和睦与团结。
助推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发生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诱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下属洛桑扎西等人闻讯后率众数千围攻驻藏大臣衙署,七世达赖喇嘛派遣众僧救护,未能如愿。拉布敦被杀,傅清重伤自尽殉国。叛乱引发西藏地方政局动荡。乾隆震怒,改革藏政,欲在西藏实行内地的政治制度,设置总督并委派各级官员,强调“西藏的一切大小事务均由汉官处理”。章嘉跪奏乾隆:“西藏乃教法之发源地。如果按圣上所下的旨令,藏地的佛教必将衰微,万望陛下无论如何以恩德护持佛教。”乾隆听取了章嘉的意见,于乾隆十六年(1751)初派四川总督策楞、驻藏大臣纳穆扎尔等率兵500余名到达拉萨,西藏地方局势得以稳定。清中央政府废除西藏郡王制,令七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共同办理西藏地方事务。同年,乾隆赐予章嘉“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
奉命平息喀尔喀部叛乱事端。乾隆二十一年(1756),漠北蒙古达尔汗亲王因触犯清廷法规,欲率喀尔喀部叛乱,三世章嘉在京遵照乾隆皇帝的指令致信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讲述不能叛乱的道理,又奉旨亲赴喀尔喀平息事端。哲布尊丹巴接信后晓谕喀尔喀各部首领,不能违背大皇帝之旨意,成功劝导达尔汗亲王等放弃了叛乱图谋。章嘉中途得到喀尔喀局势已平稳消息后奏报乾隆,乾隆降旨令其返回。
奉命认定八世达赖喇嘛,促成六世班禅东行朝觐。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三世章嘉奉乾隆皇帝之命入藏主持政教事务,按圣谕委任六世第穆活佛为摄政,形成了西藏摄政制度;主持认定了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乾隆二十五年(1760)返回北京。在藏期间与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益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他的积极活动下,为祝贺乾隆皇帝七十万寿,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大师东行来到北京,他是负责接待六世班禅大师的主持者之一,并在六世班禅大师到雍和宫为乾隆皇帝说法和传授灌顶时担任翻译。
四、奉乾隆皇帝之命在京城建寺弘法
三世章嘉不仅是乾隆皇帝的宗教和边疆政治顾问,也是祖国内地和边疆之间文化交融的使者,为藏传佛教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章嘉是清代驻京呼图克图之首,在京建寺弘法,业绩卓著。
奉命将雍和宫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乾隆皇帝继位后,为给父皇雍正祈求冥福,于乾隆九年(1744)命三世章嘉将其父皇居住过的府邸雍和宫正式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三世章嘉奉命于雍和宫外筑起围墙,于宫内建成大经堂、依怙殿、授戒殿、白伞盖佛殿、药师殿、天王殿、钟鼓楼等寺院建筑,内供大量经、像、塔三所依,经堂及僧舍内各种日用品亦由府库配备齐全。乾隆皇帝赐寺名“噶丹敬恰林”(藏语意为“兜率壮丽洲”),寺院始成,成为清代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理藩院直属的重要的皇家寺院之一。该寺在内地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历史上以规模宏大、学经组织完备、驻锡高僧众多并实施“金瓶掣签”制度设有“金本巴瓶”而闻名,是内地藏传佛教的宗教中心和管理中心;目前是北京保存至今且最为完整、佛事活动完备、宗教文化独特、有僧人驻锡的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尤其在当今蒙古佛教诸寺中具有核心地位和重要影响。
奉命在京城建造满族佛教寺院。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大皇帝询问章嘉国师:‘我们满族人自博克多汗居住莫顿的时期起,直到现在,虽然信奉佛教,却没有出家之习惯。如今想在京师西面的山脚下建立一座寺院,内设一所全部由新出家的满族僧人居住的扎仓,你看如何?’章嘉国师回答说:‘博克多汗与格鲁派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以后,在莫顿建有僧团和佛堂,后来迁都北京,历辈先帝和陛下都尊崇佛教,建立了寺院和身、语、意所依止处,成立了僧伽,尽力推广佛教。如今又想创立前所未有之例规,建造佛寺,振兴佛教,自然是功德无量,圣恩浩荡。’圣上闻言,龙颜大悦。于是,按照皇帝的旨意,由国库拨款,修建了一座形式与雍和宫相仿的佛教大寺院,内有佛殿和僧舍。章嘉国师主持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担任这些初出家的满族僧人的堪布,为他们传授居士戒和中间戒(即沙弥戒)。皇帝谕令:‘在此寺聚诵时全都必须用满语诵经,因此所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国师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书籍。并因为西藏诵经语调不适合用满语念诵,于是专门为满语诵经者制定了新的诵经语调。”
章嘉若必多吉在香山所主持修建的这座满族喇嘛寺院究竟是哪座寺院,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乾隆十五年(1750)建造的宝谛寺,也有人认为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兴建的宝相寺,而清代的汉文史料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因宝谛寺、宝相寺不是香山第一座满族喇嘛寺院,宝谛寺仿五台山菩萨顶建造,而宝相寺仿五台山殊像寺建造,并不像上述记载所言是仿照雍和宫建造。故为此二寺其中之一的可能性不大。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位于香山山麓东南方向万安山山脚下团城演武厅西北侧的实胜寺。实胜寺是香山第一座满族喇嘛寺院,是乾隆皇帝为纪念第一次平定金川而建,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梵香寺虽于同年建造,但晚于实胜寺。此点符合上述记载中在香山首创满族喇嘛寺院的说法。同时,上述记载虽未明确交代时间,但在前一章即第十二章“莅临佑宁寺弘法”中说明“当时他刚到三十三岁”。章嘉若必多吉圆寂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享年70岁。33岁时是乾隆十四年(1749),正与建造实胜寺的时间吻合。有可能乾隆皇帝为颂扬第一次平定金川之功,由于有清军精锐部队健锐营和金川战俘居住的“番子村”,出于某种政治考虑,早有于其附近建造满族佛寺的打算,因此以另一种方式向章嘉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获得这位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支持,并由他来完成这项工作。
以后随着梵香寺、宝谛寺、长龄寺、宝相寺、方圆庙等满族佛寺的相继建成,形成了香山演武厅附近满族佛寺文化圈。
约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开始,为配合满族喇嘛寺院开展佛事活动,乾隆皇帝又命章嘉国师负责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及部分藏汉文的论疏翻译成满文,乾隆皇帝还亲自参加了校审的工作。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乾隆皇帝认为,满族人口众多,佛教信仰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语言文字与别族不同,以前也没有译成满文的佛教经典,若将《甘珠尔》译成满文,实在是造福于后代之善举,遂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译成满文。于是从学府成绩优异的人员和在京的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的人员,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组织在一起开始翻译经卷。每译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逐卷进呈乾隆审阅,乾隆在审阅中又更正了一些有疑问及不妥当之处。乾隆皇帝还作有译后记,因此经过多年,始告全部译成。满文大藏经《甘珠尔》的翻译完成,为宝相寺等北京满族佛寺正常开展诵经等佛事活动以及寺院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满藏民族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奉敕主持建造佛香阁。佛香阁是举世闻名的北京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以其建筑形式新颖独特而享誉中外。实际上,佛香阁为著名的藏传佛教建筑,是清乾隆年间(1736—1795),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由三世章嘉主持建造的。乾隆十六年(1751),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皇太后(1692—1777)六十大寿,乾隆皇帝为了给母亲祝寿,改北京西郊西湖为昆明湖,改瓮山为万寿山,并效法明成祖朱棣在江宁为母祝寿而建报恩寺的做法,在万寿山前明代圆静寺旧址上建造了大报恩延寿寺。
三世章嘉活佛遵照乾隆皇帝的命令,参与了建造大报恩延寿寺工程,并主持建造了寺内著名的佛香阁等建筑。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乾隆皇帝在京师的后面修建了一座三层佛堂,内塑一尊白伞盖佛母像,以作为社稷的保护神。章嘉国师亲自指导塑造,并举行了开光典礼。每遇节日由僧众举行献供仪轨。又在佛殿右面修建一座九层佛塔,建至第八层时,从天上落下一团火,烧毁了整个佛塔,以后在此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名为“大西天”的印度式佛堂,由章嘉国师举行了开光典礼。所谓“大西天”佛堂即是今日的佛香阁。
乾隆在修建大报恩延寿寺时,仿照明成祖朱棣为母祝寿建大报恩寺塔的做法,仿照杭州六和塔式样建造延寿塔为母祝寿。乾隆有《新春游万寿山报恩延寿寺诸景即事杂咏其二》,诗文为“宝塔初修未克终,佛楼改建落成工。诗题志过人皆见,慈寿原同山样崇”。乾隆在诗后注释:“先是欲仿浙江六和塔式建塔,为圣母皇太后祝釐。工作不臻而颓。因考《春明梦余录》历载‘京城西北隅不宜高建窣堵’,乃罢更筑之意,就基改建佛楼。且作志纪实,题曰《志过》云。”而乾隆在《志过》中则说:“延寿仿六合,将成自颓堕”。意即延寿塔是自行倒塌的。但从《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的记载看,拆塔建阁的原因系由火灾引起。因此,该塔在遭受火灾之后,乾隆从《春明梦余录》中考证出京城西北不宜建高塔之说,由此则由三世章嘉活佛主持建成了名扬后世的佛香阁。佛香阁是该寺的中心建筑,阁高41米,八面三层四重檐,在我国木结构古建筑中,其高仅次于山西应县木塔。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焚毁后,光绪时按原样重建。阁内原供奉白伞盖佛母,现供有千手千眼观音。
奉敕建造须弥灵境的香岩宗印之阁。须弥灵境位于颐和园万寿山山阴,即佛香阁以北山坡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是汉藏合璧的寺院建筑,是供皇家自己供奉祭祀之用的场所。寺院后半部分香岩宗印之阁仿照西藏桑耶寺建造,属皇家苑囿中的藏传佛教建筑。
须弥灵境中的香岩宗印之阁建筑群是由三世章嘉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设计建造的。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乾隆皇帝曾询问章嘉国师有关在西藏为佛教建有殊勋的杰出人物的情况。章嘉国师列举作答,其中讲到了大译师仁钦桑波创建托林寺的情况,言此寺依密乘立体坛城设计建造。乾隆皇帝提出:“在朕的京城中也要建一座那样的佛殿。”于是,由章嘉国师负责,在内城右方建造了一座四层金顶佛殿,内置密乘四续部佛众造像。顶层殿内塑有密集金刚像,第三层内塑有大日如来现证佛像,底层殿内作为各扎仓僧众修证三重三昧耶仪轨的道场。这座由章嘉国师负责建造的佛殿就是香岩宗印之阁。上述记载称仿托林寺建造,由于托林寺是仿照桑耶寺建造的,故该寺实际上是仿照桑耶寺建造的。
须弥灵境也可以说是一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整体建筑坐南朝北,因山顺势,就地起阁,建筑在四层高台上。前半部包括牌楼、广场、大雄宝殿、配殿等,后半部是仿照西藏著名古庙桑耶寺的形制建成的庞大的宗教建筑群。香岩宗印之阁象征须弥山,四大部洲环绕四周,即北俱芦洲、南赡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在阁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是代表“四智”的绿、红、黑、白四座喇嘛塔,另有八小部洲、日台、月台。智慧海众香界牌坊用五色琉璃瓦装饰。在牌坊的正、反面石额和智慧海的前后石额上分别为“众香界”“祇树林”“智慧海”“吉祥云”。牌坊顶装饰着覆钵塔。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颐和园,须弥灵境大殿、香岩宗印之阁等建筑被大火吞没。从光绪十二年(1886)开始,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水师经费重修颐和园,在万寿山修复了香岩宗印之阁等建筑,虽然长宽与原来相同,但已缩减为一个单檐歇山琉璃顶的一层大殿。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钦定驻京喇嘛班第,左翼头班章嘉呼图克图,二班敏珠尔呼图克图;右翼头班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二班济咙呼图克图,皆列于雍和宫总堪布、避暑山庄普宁寺总堪布之上。因此,这四大呼图克图被称为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在驻京呼图克图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章嘉成为驻京喇嘛之首。
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三世章嘉圆寂于五台山,享年70岁。圆寂之日,他对乾隆说:“我自入寂之后,又有转世,请勿忧虑。”乾隆十分悲痛,赏银一千五百两为其熬茶唪经,并制金塔存放其肉身舍利,其舍利供奉于五台山镇海寺。
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听命中央,怀柔边疆,出使西藏地方及其他蒙藏地区,宣谕中央政府指令,奉命处理政教事务,在联系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充分发挥了政治纽带的作用,进一步巩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关系。维护稳定,化解纷争,根据清中央政府的指令,针对蒙藏地区敬信佛教的传统,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调解蒙藏地区的纠纷,为维护蒙藏地区的和谐和安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帮助清廷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三世章嘉还为清代北京藏传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在宫廷内外讲经弘法外,不仅主持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而且主持修建了嵩祝寺,参与修建了颐和园佛香阁等寺庙建筑,帮助雍和宫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经组织,开启了雍和宫祈愿法会制度,又亲率四百僧众参加每年一度的西黄寺正月祈愿法会。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还将“噶尔”和“羌姆”等西藏宗教舞蹈传入北京,推动了藏传佛教深入北京民间,促进了藏传佛教与北京民俗文化的融合。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