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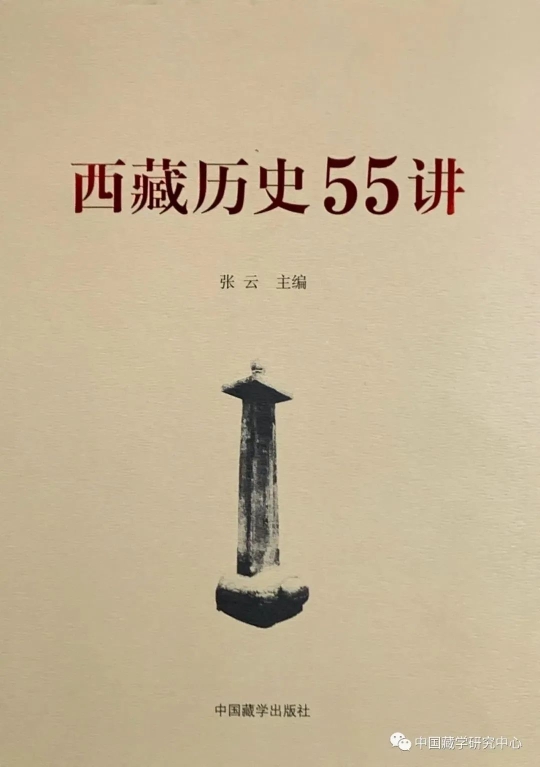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27讲 摄政制度
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藏传佛教格鲁派采用由噶玛噶举派创立的活佛转世的传承方式来解决继承人的选择问题,达赖喇嘛圆寂后,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学经、受戒,直到18岁亲政,中间至少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若无人主持西藏政教事务,就会形成权力真空。
清廷为防止噶伦等人“擅权滋事”,遂命西藏地方当局从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及四大林(丹吉林、功德林、策墨林、锡德林)中推选学识渊博、声望卓越之大活佛为摄政候选人,由驻藏大臣奏请清廷任命,清廷视其出身及勋绩赏给呼图克图、诺门汗、禅师等名号,颁给金册、银印,在达赖喇嘛新灵童未寻获及灵童坐床后尚未达到执政年龄(18岁)之前,暂行代理达赖喇嘛主持西藏政教事务,这便是摄政,藏文称“杰曹”(rgyal-tshab)。
一、摄政的产生与第一任摄政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乾隆皇帝降旨:“现在确认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至关重要。章嘉呼图克图须去西藏,寻访认定其转世。朕虽不愿遣呼图克图去远方,然此次之事关系西藏佛教大业,甚为重要。你去后不必久留,一经认定转世灵童,即可返回。”章嘉国师此次前往西藏,还与乾隆皇帝恩准噶厦奏请、任命第穆诺门汗·阿旺江白德勒嘉措为摄政有关,摄政“掌办商上事务”,即在达赖喇嘛新灵童未找到及灵童坐床未达到亲政年龄之前,代理达赖喇嘛政教职权,这在后来形成了一项制度,这就是摄政制度。摄政第穆诺门汗·阿旺江白德勒嘉措在今西藏拉萨大昭寺西北修建寺院,即丹吉林(bstan-rgyas-gling),乾隆皇帝御赐“广法寺”匾额,成为第穆呼图克图的府邸。
二、摄政的地位及其政教作用
第穆德勒嘉措担任摄政期间(1757—1777),创建了摄政的办事机构“雪嘎”,负责传达摄政的命令,“雪嘎”由四品僧官南卓负责,设有五品俗官8名,侍卫2名,联络僧官1名。各级呈报摄政公文及其批示,由南卓向噶厦下达执行。以后,凡摄政执政期间,都建有这一办事机构。
作为当时新创立的制度,摄政只是掌办达赖喇嘛的宗教事务,还是掌办达赖喇嘛的政教一切事务是存在争论的,突出的问题依然是噶伦擅权,他们希望把摄政的权力限制在代理达赖喇嘛宗教事务范围内,由噶伦来办理达赖喇嘛原来承担的行政权力。
显然,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喇嘛圆寂让建立未久的噶厦制和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都面临考验。同年二月四日,驻藏大臣伍弥泰等转呈公班第达等噶伦的藏文奏折称:“今达赖喇嘛圆寂,章嘉呼图克图系达赖喇嘛之大弟子,为达赖喇嘛之呼必尔罕快出,请其祈祷佛。”二月二十七日(4月15日),乾隆皇帝朱批:“朕即由此处派遣章嘉呼图克图”,答应了公班第达等的请求。
二月十五日,驻藏大臣伍弥泰、萨喇善转奏西藏地方噶伦、堪布等的意见:“我地之喇嘛甚多,事亦繁杂,原来由达赖喇嘛一人独自办理,今达赖喇嘛圆寂,办理众喇嘛事务,不可无有一总为首办理之人。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札木巴尔德勒克嘉木措经好、为人明白,今年三十五岁。达赖喇嘛在时,亦称赞其比他人出众,常召至身边行走,故皆知我喇嘛之事务,而全藏上下人等亦皆恭敬。若诚能令其为首办理我喇嘛事务,于黄教颇为有利。”驻藏大臣伍弥泰、萨喇善等也认为第穆呼图克图为人明白稳重,受人尊敬,尚能办理众喇嘛之事务,拟依其所请,“命第穆呼图克图总其首,达赖喇嘛身边守护之堪布达尔汉格隆噶拉桑云丹、罗布藏策凌、罗布藏纳木札尔、札克巴提崖、阿旺钦则辅助办理此地喇嘛事务”。奏请获得乾隆皇帝批准。
乾隆二十二年(1757)4月29日,乾隆帝又下一道诏书,强调“前此伍弥泰等奏到达赉(赖)喇嘛圆寂,朕念卫藏地方紧要,曾于折内批谕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此特因卫藏不可无为首办事之人,原系抚恤伊等之意,今噶隆与众堪布等既同推迪(第)穆呼图克图为首办事,即毋庸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但是,考虑到驻藏大臣们是否接到前批谕旨,是否已向噶隆、众堪布宣告,均不清楚,故而又云:“今发去谕旨二道,若前批发之旨已向噶隆等告知,即将停止章嘉呼图克图,另准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之旨,向噶隆等宣谕。若前旨尚未向众告知,即毋庸言及,只照伊等所请,著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伍弥泰等接旨后,将用哪一道圣旨宣谕,务须据实奉闻。
西藏地方噶伦、堪布改变立场,表面上并无异样之处,只要维护现行体制,保障地方安定,诚如事实所展示的那样,均会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批准。乾隆皇帝还收回成命,拟不再派章嘉国师前往西藏主持达赖喇嘛灵童转世等事。
然而,在乾隆皇帝的圣旨里和西藏地方噶伦的奏折里,第穆呼图克图的地位并不相同,乾隆帝拟派的章嘉国师或恩准的第穆呼图克图均是西藏地方“为首办事之人”,即政教首领,而噶伦们所要求的只是“办理喇嘛事务之人”,即宗教首领,这就关乎体制问题。
章嘉国师首先发现了这种歧异,他在接到皇帝令其无须进藏的圣旨后,于三月十七日呈上奏折,陈明己见,谓:“我详看过伍弥泰等为依噶布伦、堪布等所请命第穆呼图克图为首暂办各寺庙喇嘛事务之奏折,小喇嘛我尚记得,按唐古特地方旧例,卫藏各地所属唐古特官员、喇嘛人等之一切事务,原来皆由达赖喇嘛承办。后来颇罗鼐依凭圣上之仁化,渐渐办理一切事务,效力行走,故圣上接连施恩,升至郡王任用。从此,达赖喇嘛仅办理喇嘛事务,颇罗鼐所属地方人等之事务,不报达赖喇嘛闻知,独处专之,长此日久,至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时,不仅不思感激国家之恩,反而傲慢乖张,胡乱妄行。为西部卫藏地区永远太平,圣上明鉴,不准噶布伦班第达等擅权,以消弭彼等内部相互争斗猜疑,将卫藏各地之喇嘛等一切事务,均交达赖喇嘛主持办理。这几年来,颇为太平安逸。今达赖喇嘛圆寂,伍弥泰等所奏,仰副圣上仁爱之意,为彼处人等利益,命第穆图克图克暂理达赖喇嘛事务,并请赐号者,甚好,实合圣上好生之至意。唯所奏折内,仅将喇嘛事务交第穆呼图克图办理等处,并不明白,似稍有含糊。伏思噶布伦等岂有擅权之心呢?今若依彼等含混之请,仅命办理喇嘛事务,那么,卫藏所属众人等之事务,必至自然由噶布伦等办理。日久之后,彼等之唐古特恶习兴起,则不能消弭相互掣肘争斗之弊。以小喇嘛之愚意,此次所降彼等之上谕内,仍照前不准噶布伦等擅权,卫藏喇嘛人等所有事务,均照达赖喇嘛在时所办,命第穆呼图克图全部暂理。如此,下属喇嘛人等皆知达赖在时没有怀疑(疑处?),也可消弭噶布伦等相互争斗掣肘之弊端。为此,请将命第穆呼图克图按达赖喇嘛所办暂理喇嘛人等所有事务,写入上谕内。小喇嘛我将微知之处惶恐奏闻,合与不合,祈圣上明鉴。”看了章嘉国师的奏折,乾隆皇帝朱批:“呼图克图之思甚是,阅之颇悦。除照此降旨第穆呼图克图外,亦秘密降旨(晓谕)驻藏大臣。”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壬子二十一日(1757年5月8日),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卫藏之人性好擅权滋事,颇罗鼐故后,办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时,曾降旨,将卫藏一切事件,俱告知达赉(赖)喇嘛办理,噶隆等惟令遵办达赉(赖)喇嘛所交事件,是以数年以来,甚属安静无事。兹达赉(赖)喇嘛圆寂,览噶隆等请将迪(第)穆呼图克图为首之奏,只称请掌办喇嘛事务,所奏殊属含混。噶隆等颇有擅办喇嘛事务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权柄,是以朕赏迪(第)穆呼图克图诺门汗之号,俾令如达赉(赖)喇嘛在日,一体掌办喇嘛事务。除明降谕旨外,再谕伍弥泰、萨喇善务宜留心,遇有一切事务,俱照达赉(赖)喇嘛在时之例,与迪(第)穆呼图克图商办,毋令噶隆等擅权滋事。”同时仍令章嘉国师携密函至藏督办各项事务。
乾隆二十二年(1757)藏历十二月,章嘉国师经昌都等地到达拉萨,第穆呼图克图、各大活佛、色拉寺和哲蚌寺的执事喇嘛、两位驻藏大臣、噶伦、仲科等所有布达拉宫和噶厦各机构的官员,都乘马到城外远迎。章嘉国师首先解决第穆呼图克图的地位问题,据称,先前第穆呼图克图虽为摄政,但并未受到西藏地方上层应有的尊重,在举行宴会时,座次低于两位驻藏大臣,章嘉国师认为他是达赖喇嘛的摄政,会见时亲自下马执手,并与之互换哈达,“从此,第穆活佛地位日高,大小事体均如噶丹颇章政权之例规”。
摄政是由西藏地方推荐皇帝任命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乾隆四十二年(1777),摄政第穆诺门汗去世,乾隆帝命策墨林·阿旺楚臣为摄政。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帝命八世达赖喇嘛亲政。认为“藏中诸事务必须一晓事大喇嘛帮同达赖喇嘛办理方为有益”,仍命策墨林·阿旺楚臣继续掌办商上事务,协助达赖喇嘛管理田产、办理政务。其目的“为藏内大臣耳目,使达赖喇嘛不致擅权自恣。”
乾隆五十六年(1791),阿旺楚臣去世,乾隆帝又命达则诺门汗(即功德林济咙呼图克图)益西洛桑登白贡布继续掌管商上事务。嘉庆元年(1796),清军参赞公海兰察巴图鲁等捐资为济咙在拉萨磨盘山南麓修建私庙竣工,皇帝赐匾“卫藏永安”,即“功德林寺”。嘉庆九年(1804),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圆寂,嘉庆皇帝命掌办商上事务的功德林济咙呼图克图益西洛桑登白贡布任摄政。嘉庆十六年(1811),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去世,嘉庆帝命第穆呼图克图洛桑土登晋美嘉措任摄政。
嘉庆二十年(1815),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在布达拉宫暴亡,只活了11岁。嘉庆皇帝下令一面寻访转世灵童,一面命第穆呼图克图洛桑土登晋美嘉措任摄政。嘉庆二十三年(1818),第穆呼图克图去世,嘉庆帝又命策墨林呼图克图阿旺江白楚臣嘉措摄政。
道光二年(1822),楚臣嘉措经金瓶掣签被确认为第十世达赖喇嘛,并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大典,摄政仍为策墨林呼图克图阿旺江白楚臣嘉措。道光十七年(1837),楚臣嘉措又在布达拉宫暴亡,只活了22岁,到去世为止,十世达赖喇嘛一直没有亲政,西藏政教大权握在摄政之手。
咸丰十年(1860),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同治元年(1862),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因西藏内部僧俗官员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被革职,同治帝即派诺门汗夏札·汪曲杰波协办商上事务。同治三年(1864),夏札·汪曲杰波去世,同治帝又命达赖喇嘛的师父罗桑钦热汪觉协办商上事务。同治十二年(1873),代理摄政罗桑钦热汪觉病死,同治帝命令达赖喇嘛亲政。光绪元年(1875),十二世达赖喇嘛突然又在布达拉宫暴亡。只活了20岁,亲政时间也只是刚刚一年。成烈嘉措圆寂后,同治帝又命功德林济咙通善呼图克图阿旺白登曲吉江措继任摄政。
三、与摄政相关的几个重大事件
道光二十一年(1841),凯珠嘉措经金瓶掣签被认定为第十一世达赖喇嘛,二十二年(1842)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大典,仍由策墨林呼图克图阿旺江白楚臣嘉措摄政。二十四年(1844),驻藏大臣琦善(1786—1854)与摄政阿旺江白楚臣嘉措失和,驻藏大臣向道光皇帝参奏摄政夜郎自大,诸事专擅,妄作威福,肆行无忌,道光皇帝即谕军机大臣:“该诺门汗噶勒丹锡热图萨玛第巴克什(即策墨林呼图克图)现在掌办商上事务,如果实有狂妄贪奸各情,于黄教大有关系。着琦善会同班禅额尔德尼,并率同第穆、济咙呼图克图、热征诺门汗等,逐款确查,据实参办。”结果奉旨“历得职衔名号全行褫革,追敕剥黄,名下徒众全行撤出,庙内查封,发往黑龙江安置。所有财产,查抄变价,赔修藏属各庙宇。旋命释回,交地方严加管束”。
摄政策墨林呼图克图被革职后,琦善又奏请道光皇帝,由七世班禅丹贝尼玛掌办商上事务。道光皇帝降旨:“其商上事务着照议准令班禅额尔德尼暂行兼管,第穆、济咙、热征三人并令随同学习,俟一、二年后,由该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酌保一人掌办商上事务,将此谕令知之。”
七世班禅开始不愿意担任摄政,后来因为不能违抗圣旨,才勉强担任了8个月摄政。道光二十五年(1845)3月,七世班禅辞去摄政职务。道光皇帝命热振呼图克图阿旺益西楚臣江村担任摄政。咸丰五年(1855),咸丰皇帝命达赖喇嘛亲政,还不满一年,突于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暴亡,只活了18岁。十一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咸丰皇帝又命热振呼图克图担任摄政。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位俗人出身,后来在扎什伦布寺出家的人物担任摄政,他便是夏扎·旺曲杰布。道光二十一年(1841),森巴人侵入阿里,曾奉命随索康率藏军驰援,并参加停战谈判。咸丰五年(1855),尼泊尔袭据聂拉木和吉隆,深入后藏,率藏军收复聂拉木要隘。道光二十七年(1847),还曾奉命解决过乍丫(察雅)两大呼图克图之间的争端,颇著功绩。担任噶伦,后因与掌办商上事务之热振呼图克图不和,于咸丰八年(1858)辞噶伦职,剃发为僧,在扎什伦布寺出家。热振被革职后,由僧俗公举,于同治元年(1862)复起用,掌办商上事务,代达赖喇嘛管理政务,赏“诺门罕”名号。二年,奉命办理征中瞻对酋工布郎结事宜。担任摄政两年。
光绪三年(1877),土登嘉措经光绪皇帝批准免予金瓶掣签,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光绪五年(1879)6月13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大典。光绪十二年(1886),摄政济咙通善呼图克图去世,光绪皇帝命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桑赤烈饶杰担任摄政。光绪十九年(1893)9月7日圣旨称:“恳如商上葛布伦三大寺僧俗大众等请,仍饬第穆呼图克图再行掌办商上事务五年。从之。”
按照过去惯例,历代达赖喇嘛年满18岁,即应亲政,接管政务。但自九世达赖喇嘛以来,都是青年夭亡,政权握在摄政手中。光绪二十年(1894),十三世达赖喇嘛年届19岁,光绪帝曾下令要他亲政,但达赖喇嘛以自己年纪尚幼,同时正在学经,恐亲政以后,政教两误为由,推辞未就,只把历代达赖喇嘛的三颗印玺接受过来,交给噶丹掌管。十三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以后,三大寺和噶厦僧俗官员,借口“神意”,压迫第穆呼图克图辞职,要求达赖喇嘛亲自掌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8月,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向达赖喇嘛提出辞呈,达赖喇嘛接了辞呈后,交给三大寺和全体僧俗官员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要求达赖喇嘛批准摄政的辞呈,自己出来执政。是年8月8日,在布达拉宫司西彭措大殿举行亲政大典。卸职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则回寺参禅。光绪二十五年(1899)7月,西藏发生“第穆事件”。刘家驹所著《西藏政教史略》称:“藏政府假护法神之口,诬藏王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桑称勒阴谋不轨,诅咒达赖,旋将第穆佛禁毙狱中,查抄阐宗寺财产。同时加罪丁结林(即丹吉林)之臣僚罗布顿珠等,先后被杀,达赖于是威服全藏,莫敢有违。”
四、摄政与达赖喇嘛、驻藏大臣的关系
摄政与达赖喇嘛、驻藏大臣之间存在复杂的权力交错关系。有良好的合作,也有矛盾斗争。
乾隆六十年(1795),八世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松筠的授意下,决定减免百姓赋税,除应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猪等项”外,其余应交粮各项,“普免一年”。将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旧欠粮石,乃牛羊猪各项钱粮四万余两,概行豁免”。将失散百姓招回,“给予银两修补房屋,给予籽种各务农业,三年之内,免除钱粮杂税”。同时告示各处营官第巴头人,除朝佛熬茶来藏及达赖喇嘛有事所需乌拉之处,其余一切差事,须持有驻藏大臣发给的执照,不得滥行应付乌拉。八世达赖喇嘛还响应皇帝号召,将他库中积存的布施银三万两交出用于救济各处穷苦百姓。最后乾隆皇帝批示:“据松筠等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请将伊等所属唐古忒等应交粮石及旧欠钱粮宽免,并赈济贫人,修理倒坏房屋之处请旨等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一闻朕降旨蠲免天下钱粮,伊等亦请将唐古忒等抚恤办理,实属善举,朕深为嘉悦。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著各赏给哈达一个,紫金俐玛无量寿佛各一尊,碧玉手串各一挂,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三对。松筠等接奉时,即转为赏给。但前藏地广,所交之项较多。达赖喇嘛既请宽免一年,即著照所请办理。后藏地狭,所交之项较少,恐不足班禅额尔德尼一年之用,即著免其一半。但赈济贫人,修理倒坏房屋等项,由达赖喇嘛之商中拨银三万两,由班禅额尔德尼之商中拨银几万两之处,并未声明。达赖喇嘛等仰体朕意,既将唐古忒等抚恤办理,自不必拨用达赖喇嘛银两,著即动用该处正项,赏给前藏银三万两,后藏银一万两。松筠等务须悉心办理,毋致一人遗漏,以副朕一体轸恤番仆之意。”
这是驻藏大臣遵照皇帝圣旨办理的优抚事项,也是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合作愉快的案例。事实上,驻藏大臣、达赖喇嘛与摄政三者互相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到了清朝走向衰落时期尤为明显和激烈。
摄政制度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建立到1951年终止,历时195年,共15位摄政,其中两人是代理摄政,即十三世达赖喇嘛光绪三十年(1904)因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而出走蒙古、内地,宣统二年(1910)因驻藏川军逃亡印度时自行任命过两个摄政。在名义上由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治体制中,摄政占据了特殊乃至极为重要的位置,历代达赖喇嘛亲政的时间只有65年,摄政执政的时间则长达130年。也就是说,在这195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由摄政掌管西藏地方政教事务。
摄政的长期执政固然与达赖喇嘛需要18年左右的成长过程有关,但无疑也与西藏地方上层贵族特别是与摄政的争权夺利有关。九世达赖喇嘛、十世达赖喇嘛均未及亲政便夭亡;十一世达赖喇嘛咸丰五年(1855)亲政不满一年就在布达拉宫暴亡;十二世达赖喇嘛同治十二年(1873)亲政不到两年,又于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日在布达拉宫暴亡。在三百年的政教合一西藏地方政权中,只有两位达赖喇嘛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执掌地方政教大权,这就是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他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嘉庆九年(1804)亲政2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33年亲政38年,后者更是历代达赖喇嘛中亲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但是在他两次逃出拉萨期间,曾委任第八十六任甘丹赤巴罗桑坚赞和第八十七任甘丹赤巴、三世策墨林活佛罗桑丹贝坚赞担任摄政,如果除去这一段时间,达赖喇嘛掌政时间更短。权力倾轧和激烈斗争是严重影响达赖喇嘛亲政掌权,乃至健康成长的因素之一。十三世达赖喇嘛与第穆呼图克图之间白热化的斗争,既是这种关系的一种体现,也是这种残酷斗争的真实写照。与其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固然工于心计,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毋宁说是当时政治生态下一种求生自保的本能和强力反击。
摄政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摄政是在与驻藏大臣一起主持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达赖喇嘛圆寂后,受命代行达赖喇嘛政教职权的高级官员。
其二,摄政是由驻藏大臣参照西藏地方政府或者政教首领的意见选择的,经奏请皇上批准,获得封号与印信,取得合法地位。
其三,摄政主持政教事务的权力,在达赖喇嘛成年(一般年满18岁),获得皇帝谕令“亲政”圣旨后,即转交给达赖喇嘛,摄政仍可协助达赖喇嘛办理政教事务。
其四,摄政基本为第穆、策墨林、功德林和热振等几大活佛转世系统所掌握,形成一定的政教势力。同时还有一位长期担任俗官的夏扎·旺曲杰布担任过摄政,此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尼玛也曾受皇帝之命担任过8个月摄政。
其五,摄政是由皇帝依西藏地方僧俗上层的请求委任的,也由皇帝依其功绩予以奖励或处罚,违制者甚至被剥夺名号,绳之以法。免职或死亡,要收回印信。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