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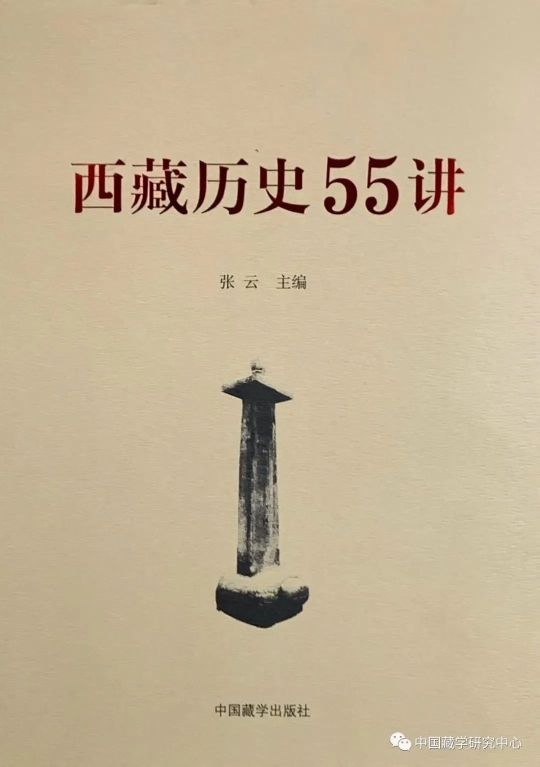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24讲 郡王主政制的兴废
清朝任命噶伦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本来就是地区各势力平衡的产物,自开始便存在矛盾,前藏贵族阿尔布巴、隆布鼐和扎尔鼐等并不认可颇罗鼐。尽管朝廷多方协调,最后任命康济鼐为首席噶伦,阿尔布巴协理办事,依然没有化解冲突,最终引发清朝管理西藏地方体制的再度变革。
一、噶伦内讧与卫藏战争
在蒙古和硕特部管理西藏的75年里,西藏地方的高层官员多数由前藏地区的人来担任,而后藏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势力因受到藏巴汗政权垮台的这一历史原因的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根据《颇罗鼐传》记载:任命颇罗鼐为噶伦时,多位噶伦和官员说,按照甘丹颇章政权的旧例,后藏人不能担任这样高职位的官员。尤其是颇罗鼐台吉,确实是拉藏汗的亲信,担任噶伦时机尚不成熟。
康熙六十年(1721),康济鼐被清廷封为贝子,成为噶伦之首,但其他两位前藏噶伦是甘丹颇章政权中心地带的大贵族,有雄厚的政治实力,因此对康济鼐的权力予以很大限制。雍正元年(1723),颇罗鼐和扎尔鼐成为噶伦后,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权力才逐渐转移到以康济鼐与颇罗鼐为代表的后藏派手中。根据鄂齐报告:“首领办事之人互相不睦,每每见于词色。达赖喇嘛虽甚聪敏,但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索诺木达尔扎之处。康济鼐为人甚好,但恃伊勋绩,轻视众噶隆,为众所恨。阿尔布巴赋性阴险,行事异于康济鼐,而索诺木达尔扎因娶隆布奈二女,三人合为一党。若调唆达赖喇嘛与康济鼐不睦,必至争竞生事。”
岳钟琪、鄂齐、颇罗鼐等人的奏稿和达赖喇嘛对康济鼐被杀原因的解释等均提到诸噶伦相互猜忌、相互倾轧的情况。当时鄂齐的建议是“噶隆甚多,反增繁扰。隆布奈行止妄乱,扎尔鼐庸懦无能。应将此二人以噶隆原衔解任,则阿尔布巴无人协助,自然势孤,无作乱之人矣。”由于动作过大,没有被完全采纳。
康济鼐和颇罗鼐都是来自后藏的贵族,代表着后藏地方的利益;阿尔布巴、隆布鼐为前藏地区的大贵族,代表着前藏地区的利益;扎尔鼐为达赖喇嘛的强佐,加上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父亲索诺木达尔扎两人的影响,代表着格鲁派。因此,西藏上层统治者形成三股势力,即卫、藏和格鲁派。康济鼐为阿里地方首领,往来于卫藏与阿里之间。他在阿里时,西藏事务由噶伦阿尔布巴总领办理。
康济鼐和颇罗鼐分别到南北两面巡逻时,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三人对后藏人民加大税收,后藏的大小人物都泣喊康济鼐。他细查拉萨贪污腐败情况,发配近两百名不守规矩者。在拉萨有很多穷人在重税之下苦难不堪,但富人们在历代赞普时期想尽办法拿到特令不缴一分税收,仅拉萨一城执行许多不同制度,康济鼐见不公平之后规定400余权势人物同百姓一样缴纳税收,引发阿尔布巴、隆布鼐为代表的前藏贵族的不满。他也十分担心前后藏之间互相倾轧,思想不统一,在此情况下撤驻军,对藏不利。事实果然如此,驻藏官兵被撤之后,前、后藏噶伦之间的矛盾随之趋向尖锐。
雍正三年(1725),康济鼐要求辞职试图以退为进。后又想联合达赖喇嘛向清朝中央政府请求恢复“第巴制”。雍正四年(1726)正月二十五日,清雍正皇帝给达赖喇嘛的谕旨中称:“因噶伦内不可无为首之人,以康济鼐为首,辅佐阿尔布巴与其他噶伦同心协力办事等因……使康济鼐般可信赖之人办理藏务与由朕处派遣之官员并无异。”
以为确定了首席便可以让其他噶伦打消非分念头,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颇罗鼐传》记载:“那时,西藏的权臣们互相倾轧,各自结党营私,惹是生非,嫉妒他人富贵,把小事闹大。动辄发怒,口出恶言。即使好言相劝,也都怀恨在心。”
雍正五年(1727),清廷准备派员亲自到拉萨解决相关事项,但派遣大臣事宜被阿尔布巴等人得知后,阿尔布巴等害怕清朝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康济鼐,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来个先斩后奏,待钦差到藏之前解决以康济鼐为主的后藏势力。
雍正五年(1727)六月十八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利用噶伦会议之机,在大昭寺内杀害了康济鼐。
六月十八日,在大昭寺觉卧佛殿侧的办公室三界台阁,康济鼐和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扎尔台吉等相聚,一同坐了很久,商量事情。因为显得很亲热,康济鼐丝毫没有怀疑大祸即将临头。他对大家笑容满面,轻松愉快,说了许多兴高采烈的话,并且放声大笑。
这时,拉雪的总管阿沛洛桑来到,向康济鼐呈上一封长长的公文。正当康济鼐在审阅的时候,送信人洛桑顿悦从背后扑上来抓住康济鼐的发辫,阿沛洛桑、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和扎尔鼐台吉等抽出刀来砍杀。内库里面,门房外头,他们的随从们一哄而上,刀如雨下。这时,真像是百名屠夫宰杀牲畜。
康济鼐拚命向门房奔去,但是,身体和双手被许多人抓住,刀子无情地砍来,伤口鲜血直流。他们乱砍乱杀,并且还破口大骂道:“过去,你凭着一身本领,权势显赫,飞扬跋扈,从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你的威风,原来如此,该是倒霉的时候了。”
虽然力不敌众,康济鼐仍拚死拚活地挣扎反抗。最后,喉咙里发出咕噜噜的响声,一命呜呼。康济鼐的无辜仆从也都被杀。聚众砍杀一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用不着担惊受怕。不过,那些砍杀康济鼐的人,穷凶极恶,在忙乱中竟互相砍伤了身体。
经过后来审判了解到,杀了康济鼐之后,阿尔布巴等三噶伦立即上书大皇帝,“说坏蛋康济鼐表面上最为敬信黄教,而实际上,却追随着罪恶的准噶尔,一点也不信奉达赖喇嘛佛爷。并且政教上的种种事务,康济鼐不懂装懂,还和边域莫卧儿王打得火热,互相通信,很少敬畏大皇帝。又同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打得火热,互通书信,如此等等,说了许多假话,写了许多假函,计有七十条之多。呈送大皇帝的原文,已被将军们所掌握。于是追问每一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三个噶伦及其同党等,仍然在厚颜无耻地捏造谎言”。犯上、不信佛教和通敌成为三噶伦给康济鼐捏造的三大罪名。
接着,阿尔布巴等派前藏军仲科尔吉巴塘巴和嘉康巴等头目率三百名前藏军,到后藏颇罗鼐庄园追杀颇罗鼐。颇罗鼐联合阿里总管噶西鼐等人率后藏军民与前藏军进行交锋,卫藏战争全面爆发。颇罗鼐在后藏即可准备相关事宜,“再次与后藏起兵,联合康济鼐之兄噶西鼐等,率后藏及阿里精兵数千人,向阿尔布巴等人宣战”。据《颇罗鼐传》记载,当时颇罗鼐准备了避难、暂时放弃、战争等三个方案,但最后选择了战争。
雍正五年(1727)8月初,隆布鼐、扎尔鼐率领大军开往江孜。颇罗鼐先在日喀则附近扎营,尔后命将军江洛金巴率领3000人走年楚河南道,自己亲率大军走年楚河北道,一并向江孜前进,在仲孜击败前藏军。几天后,隆布鼐组织起卫区、塔工、霍尔蒙古等各路兵丁,分三路向颇罗鼐发起全面进攻,后藏军队大败。
颇罗鼐率领亲兵突出重围,退兵萨嘎。随后又进军江孜,战争出现相持局面。据载,“隆布鼐的军队在拆散扎什伦布寺的僧侣,在伤害班禅佛爷,在破坏纳塘寺。他们所到之处,不仅拆毁寺庙,破坏佛像,掠夺装藏,且焚烧无辜的百姓的房屋,因为贪图妇女的手钏,竟然砍下了女人们的手臂,使后藏的百姓痛苦不堪”。
随着时间的拖延,前藏军队给养断绝,粮草缺乏。此时,班禅大师和萨迦法王的使者又来进行第二次调解。双方进行和谈,交换了未盖章的停战撤军草约后,隆布鼐撤至浪卡子,颇罗鼐撤至白朗。
雍正六年(1728)五月,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军队9000余人兵分两路向拉萨进击。南路由其长子珠尔默特车布登率兵从江孜经羊卓雍湖到拉萨南部,以惑前藏兵;北路由颇罗鼐亲自率领,迂回北上,占领羊八井,对拉萨形成战略包围之势。七月二日,颇罗鼐率部越澎域山口,进至拉萨近郊的喀巴一带。三日黎明,攻入隆布鼐大营,直趋拉萨。阿尔布巴、隆布鼐等逃入布达拉宫。五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被擒获。历时一年的卫藏战争结束。
二、清军再度进藏处置
康济鼐被杀后,清廷即派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等入藏解决争端。雍正六年(1728),颇罗鼐集结后藏、阿里兵力突袭拉萨,围困阿尔布巴等人于布达拉宫并将其擒获。清廷即派都察院左都御史查郎阿和护军都统迈禄、西宁镇总兵周开捷率兵入藏。由陕西、四川、云南各地兵马15400人,于雍正六年(1728)5月初,分北、南两路进军西藏,8月北路的两支清军到达拉萨。
颇罗鼐在达木八旗帮助下,雍正六年(1728)打败阿尔布巴。颇罗鼐将阿尔布巴等人交给清军,经审判后,阿尔布巴等17人被处决。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噶伦传》中写道:“不久,〔雍正〕皇帝派阿里汗阿巴查大人(a-li-khan-a-pa-tsa-ta-bzhin,侍郎查郎阿)和米任努藏吉迈大人(mi-ring-nu-dzang-gi-me-tva-bzhin,副都统迈禄)等所率大军已经到来,连日严厉审问罪犯,辨别真假,分别处理该杀和该驱逐的人。后来的另一天,在帕玛日(bar-ma-ri)山脚下把重大罪犯置于行刑架上,火炮三响时,即行处以极刑,凌迟问剐。我在场目睹此状,真是毛骨悚然,魂不附体。”
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三位噶伦等被当众处死。
清朝起初采取分散权力和集体领导的方案,清朝只令颇罗鼐管理后藏和阿里两地区的事务,前藏事务则由颇罗鼐推荐的两名贵族噶锡巴纳木扎勒色布腾、策凌旺扎尔(策仁旺杰、次仁旺杰)负责,任命他们为噶伦,同时要颇罗鼐暂时统管前后藏事务。
朝廷所派大员查郎阿向班禅宣读雍正皇帝的敕旨,将后藏直到阿里地区都赏赐给班禅管辖,班禅一再辞谢,最后勉强接受了拉孜、昂仁、彭措林(今属拉孜)三地,自此西藏地方政权分为前藏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后藏的班禅政权,但后者管辖区有限。
三、颇罗鼐受封郡王
颇罗鼐(Polhanas,1689—1747),今西藏江孜人。本名琐南多结。康熙五十九年(1720)时为拉藏汗下属的颇罗鼐配合阿里总管康济鼐出兵策应进藏清军,击退入侵的准噶尔军。清廷平乱后,以颇罗鼐为四噶伦(总理西藏政务官员)之一,任孜本(审计官),掌管财政。雍正五年(1727)噶伦阿尔布巴杀首席噶伦康济鼐。颇罗鼐发后藏、阿里军讨击。六年,阿尔布巴兵败被执,清廷任命颇罗鼐协助驻藏大臣总理政务,并封其为贝子。
颇罗鼐执政期间,实行了安定西藏社会秩序,促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他设置常备军,练兵设卡,整修驿站,发展贸易,合理摊派差役﹑赋税﹐尊重西藏佛教各派,修复各派寺院。西藏“政教蕃盛,人物庶富,百姓安乐”,多次受到清廷嘉奖。乾隆四年(1739)颇罗鼐被封为郡王,十二年(1747)病故,享年58岁。
颇罗鼐推行赋税清理和改革。以法令的形式进行了规范管理,规定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前百姓拖欠的款项,不能还清者,一律勾销。同时,为了减轻邻里百姓的负担,改变了邻里负担逃跑人杂税的规矩,注销了逃跑者的户籍等。他还设置驿站,缩短递送公文的时间,从一个月减为9天、10天,大大减轻了百姓支差的负担。
在雍正八年(1730),颇罗鼐支持创建了纳塘寺经院。他还召集藏地的能工巧匠千余人,主持刻印了大藏经《甘珠尔》108部,佛经疏注的《丹珠尔》215部。
《颇罗鼐传》记载,“颇罗鼐王爷献出自己和长子的耳饰,以及家眷的项饰等,折合成一千多两银子,为小昭寺的不动金刚佛制作那镶满珍宝的胸饰。为大昭寺五门之一的无量光佛制作天冠和嵌满珍宝的金胸饰,为觉卧仁波钦的头顶制作那价值三百多两黄金的华盖、珍珠璎珞、金制曼遮轮王七宝和珠宝玉石的八吉祥徽,为异常灵验的三域(界)法王文殊怙主宗喀巴大师像制作镀金佛座背光,还为大昭寺佛菩萨像制作肩帔和裙围等服饰,以及宝盖、幔帐、宝幢、飞幡、香囊等物”。
颇罗鼐忠于朝廷,屡建战功,安辑地方,怜悯百姓,支持发展宗教文化事业等事迹,赢得了朝廷的认可和百姓的拥戴,在乾隆四年(1739)被封为郡王。
策仁旺杰曾求学于敏珠林寺,才华出众,先后在拉藏汗、达孜巴、颇罗鼐父子当政时期任职,还担任噶伦,他留下了名著《颇罗鼐传》《噶伦传》,其中对颇罗鼐生平事迹有比较翔实的描述,值得参考。
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逆及被杀
乾隆十二年(1747),西藏地方郡王颇罗鼐去世。颇罗鼐非常偏爱他的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求立为继承人,使之得以袭爵为郡王。乾隆帝曾晓谕傅清说:“颇罗鼐更事多,黾勉事中国(朝廷)。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
傅清上疏说:“颇罗鼐在时,长子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出驻阿里克夏,当令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帅师出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今仍遣珠尔默特策布登驻阿里克夏,令别遣宰桑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又因为准噶尔部入藏熬茶,请求增兵分路防护。乾隆帝命他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商榷,千万不要张扬。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命提督拉布敦代替他的提督之职,傅清回京。又被授为天津镇总兵,迁古北口、固原提督。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求撤出驻军,乾隆帝同意了他的建议。不久以副都统纪山代替了拉布敦。
乾隆十四年(1749),纪山上疏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与达赖喇嘛之间有嫌隙,请求将达赖喇嘛移置泰宁。乾隆帝知道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性情乖戾且胡乱作为,命曾经驻藏的两位大臣重新进藏,赐予傅清都统衔,自固原前去西藏。
纪山此时又上疏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说他的兄长珠尔默特策布登将举兵攻打他,乾隆帝命傅清在途中调查其虚实。傅清上疏说:“珠尔默特策布登未尝构兵,特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妄言,藉以夺其兄分地。臣至藏,即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惩治。”当时乾隆帝已派遣侍郎拉布敦代替纪山,于是晓谕傅清,令他详细地搜集并密奏。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暴戾恣睢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根据曾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打猎的多喀尔·策仁旺杰《噶伦传》叙述,就像名人所说的:残暴者一旦登上了王位,就叫人不得安宁,如此生活在欲坠屋顶和欲崩的悬崖之下,时常提心吊胆。“王爷(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所做所为,如像鬼迷心窍,不能自制;暴戾恣睢,矫诳杜撰,遇事不调查,为所欲为,草菅人命,无所顾忌。正如比喻所说的:见人就杀,闻者便跑,真是令人发指。我们自己虽然毫无过失,但战战兢兢地跟随着,谁要是说明事情的真相,他马上就怒气冲冲,怀恨在心,令人恐怖。对那些把坏说成好的假话,只说他对,不说他错,以及许多阿谀奉承的话,他听了就笑逐颜开。看见他在寻欢作乐时,不许我们像冬天的杜鹃样,闷不作声。他总是千方百计地用各种借口害人。”
“在最后的一次打猎中,没有出什么差错的事。但又借口我没有把好猎物,王(译者按:即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有意对准我射了一箭,打在马脖子上,鲜血直流。接着又射了一箭,射到佣人平措顿珠(phun-tshogs-don-grub)身上。他是我的一个年轻的有射术的佣人。中箭之后,从马背上掉下来,夺走了他的生命。王以此感到心满意足。我这才脱离了危险。我想,那天免遭杀害,可能是因为我身上穿了尊师珠白旺秋顿约克珠的一个背心,这背心起了护身符的作用,避开了射来之箭吧!下午,来到行营时,王叫人送来银子三品(rdo-tshad),作为死者平措顿珠的所谓善业费,把人弄得分不清敌我。真不知他使的什么花招。”策仁旺杰在与卓尼私下交流中,还谈到了因果报应怎么没有在干尽坏事的郡王身上呈现的问题。
乾隆十五年(1750),傅清与拉布敦先后到达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迫害其兄长珠尔默特策布登至死,然后驱逐他兄长的儿子,并遣使勾结准噶尔,反迹日趋明显。乾隆帝命副都统班第到西藏,与傅清、拉布敦密图制止叛乱,仍诏傅清、拉布敦不要轻举妄动,并密谕四川总督策楞勒兵为备。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谋愈急,绝塘汛,军书不得达。傅清与拉布敦未得乾隆帝的诏书,商量后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且叛,徒为所屠。乱既成,吾军不得即进,是弃两藏也。不如先发,虽亦死,乱乃易定。”10月,他们召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至通司岗驻藏大臣衙署,说皇上有诏书,让他上楼,宣读乾隆帝的诏书。趁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跪下之际,傅清在后面挥刀将其斩首。其党羽罗卜藏札什始率众围楼数重,发枪炮,并纵火烧毁房屋,傅清中了三枪,估计自己难以活命,就自刭而死。拉布敦死楼下。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皆自杀。通判常明中矢石死。从死者千总二、兵四十九、商民七十七。
在得知两大臣除掉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后,多喀尔·策仁旺杰对多仁班智达说:“西藏公众对这个魑魅大恶,不能容忍,如今二位钦差大臣大胆将他翦除,好比刺破脓疮,实在太好了。那些傲慢诡诈的家伙(按:指罗卜藏札什等人)杀害两位大臣,两者皆毁,自取灭亡。”得到多仁班智达赞同的答复之后,他觉得犹如痛饮甘露,心情格外舒畅。
乾隆皇帝对傅清、拉布敦的做法在予以肯定的同时也十分惋惜:“是二臣之心甚苦,而其有功于国家甚大。应特建双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丕昭劝忠令典。”
乾隆十六年(1751),在拉萨八廓街通司岗两位大臣遇难处和北京分别建立了“双忠祠”,乾隆亲自前往北京双忠祠(在今北京外交部街)祭奠,追授两人一等伯爵。
五、郡王制度的废除
在剪除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后,傅清和拉布敦曾派把总一人传令箭给噶伦公班第达,许诺事成之后让他做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任职期间,公班第达遭到压迫陷害,家产被查抄,母亲逃往深山,其妻分居,儿子被作为人质随侍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左右。事变发生后,班第达逃到达赖喇嘛处,有上千人请求他出来平息罗布藏札什等叛军。10天之后他将被劫掠的饷银追回,逐渐平息叛乱。傅清、拉布敦“二位已故大臣,死前把皇帝授予的令箭给了诺门班智达,要他当主持人”。同时,“达赖喇嘛授他印章,让他负责行使政教二制,他执行严法,下达了逮捕罪犯的通令,抓到所有犯人后,关押赤门家。不久皇帝派来了班阿利堪钦差(ban-a-li-khan-am-ban,班第)。他对以罗卜桑扎西为首的许多大小人物进行了详细的查问,根据他们的罪行在江洛金的院子里分别依法惩办”。所以,达赖喇嘛在给皇帝汇报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逆事件及被平息的奏折中,也请求朝廷册封班第达为郡王。但是,乾隆皇帝决意要废除郡王制度,不仅没有同意班第达的请求,表彰他的功绩,还以其未能救护两位驻藏大臣而加以责备。同时劝告他,设立郡王未必不会再出一个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本意是厚待,结果是伤害。郡王制度由此被废除。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