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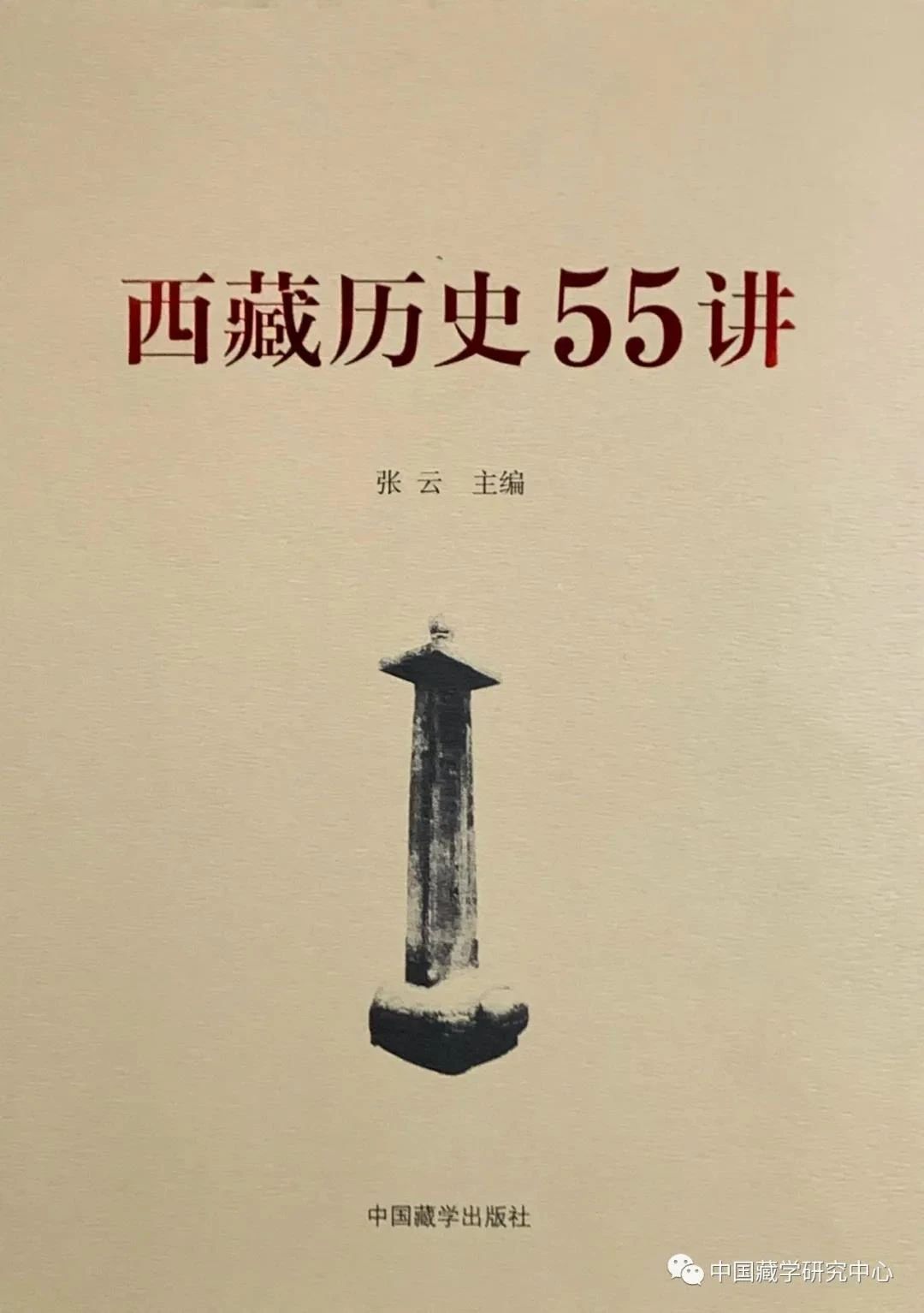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22讲 册封与管理西藏地方政教首领
中国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不能将近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等同混用,中国内地中原王朝的历史有分有合,中国边疆地区同样如此,分是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合是中国历史的统一时代。在新旧王朝更迭、群雄割据之际,显得尤为突出,强大的各地各族政治势力整合力量,逐鹿中原,叩问九鼎,弱小的政治势力纵横捭阖借以自强图存。明末清初之际正是这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清朝定鼎及其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各个政教势力的互动,成为波澜壮阔的历史一页。
一、蒙藏联合政权的建立
公元16世纪,西藏地方政局一直处在一个持续动荡的状态,帕竹政权内争不断,后藏地区贵族仁蚌巴、第悉藏巴相继兴起并展开混战,宗教上仁蚌巴家族和第悉藏巴家族在噶玛噶举派和觉囊派等教派的支持下,持续加力限制和打压正在崛起的格鲁派。1498年,帕竹掌握实权的仁蚌巴·措杰多吉(1450—1510)下令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由格鲁派创立人宗喀巴倡建的一年一度的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在这种形势下,格鲁派一方面采用活佛转世办法,建立以根敦珠巴的转世根敦嘉措为权威的新体制,以加强教派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除了更加紧密依靠帕木竹巴家族和拉萨地区的贵族吉雪巴(skyid-shod-pa)的支持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争取新的外援。1577年根敦嘉措(dge-vdun-rgya-mtsho,1475—1542)的转世索南嘉措(bsod-nam-rgya-mtsho,1543—1588)应移牧青海并希望向涉藏地区扩大自己影响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Altan-Khan,1507—1582)的邀请,前往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俺答汗举行了会见。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索南嘉措则回赠俺答汗“咱克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索南嘉措和俺答汗的会见,不仅是一种宗教上的联系,而且是格鲁派和北方的蒙古势力的政治结合,并借此与明朝建立了关系,被明朝皇帝封为“朵儿只唱”,获得了向明朝朝贡的资格。明万历十六年(1588),索南嘉措在蒙古地区圆寂后,蒙藏双方认定俺答汗的曾孙云丹嘉措(Yon-tan-rgya-mtsho,1589—1616)为他的转世,成为唯一的一位蒙古族出身的达赖喇嘛。
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底,年仅28岁的四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突然去世,这被第悉藏巴视为进一步打击格鲁派的契机,随即下令禁止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力图用取消格鲁派领导核心的办法,进而削弱和控制格鲁派。
五世达赖喇嘛幼年之际,第悉藏巴彭措南杰(phun-tshogs-rnam-rgyal,1586—1621)已控制了拉萨地区,而以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却英多吉(chos-dbyings-rdo-rje,1604—1674)为首的噶玛噶举派和觉囊派、萨迦派的僧人又承认和尊奉第悉藏巴彭措南杰为前后藏地区最高统治者,使其有很大的权力,这让格鲁派的发展举步维艰。
格鲁派不得不借助蒙古土默特部军事力量的支持,迫使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对格鲁派寺院集团作出让步,答应交还以前夺占的哲蚌(vbras-spungs)、色拉(se-ra)两寺的庄园,并把拉萨河下游地区交给格鲁派班禅额尔德尼管辖。同时,同意格鲁派继续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于是,五世达赖喇嘛得以在1622年在哲蚌寺坐床,并由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Blo-bzang-chos-kyi-rgyal-mtshan,1567—1662)为其削发并取法名阿旺罗桑嘉措(Ngag-dbang-blo-bzang-rgya-mtsho,1617—1682),格鲁派达赖喇嘛系统顺利得以延续。
明崇祯三年(1630),土默特部的拉尊和古如洪台吉在拉萨发生内讧,匆忙撤回了青海。而且紧接着喀尔喀蒙古的一部在却图汗的带领下南下青海,统治了在青海的土默特部众。在这种情况下,格鲁派的这一重要支持者退出了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斗争舞台。
在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Chos-kyi-dbang-phyug,1584—1635)的撮合下,却图汗、林丹汗和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组成了一个反格鲁派的联盟,他们计划由林丹汗带兵到青海与却图汗会合,共同进兵西藏,铲除格鲁派。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以额哲为首的蒙古十六部的49个封建主在盛京(今沈阳)集会,一致决议给皇太极上尊号为“博格达·车辰汗”,从此漠南的蒙古各部正式归附了后金,皇太极就在这时改国号为“大清”,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王朝清朝开始形成。
在喀尔喀部与卫拉特部之间发生战乱的一段时期,固始汗(Turubaikhu-Nomin,又译顾实汗,1582—1656)冒生死风险,前往喀尔喀部,通过巧妙而高超的调解活动,平息了双方的战争,给二部人民带来了和平。东科尔呼图克图和喀尔喀部的封建主们对此十分满意,共同赠给他“大国师”的称号,后来他通常所用的“固始汗”的称号即是“国师汗”的音转。
明崇祯八年(1635),格鲁派派出的人员到达卫拉特部时,正是卫拉特四部兵戈扰攘的动乱年代。一方面,固始汗与沙皇俄国地方当局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和畜群的增加,加上准噶尔部哈喇忽喇之子巴图尔浑台吉做了准噶尔部的部落长以后,欺凌其他各部,使得卫拉特蒙古的一些部落开始向新的草场转移,寻找新的牧场。
固始汗和巴图尔浑台吉带领少数随从化装成商人,经柴达木盆地到长江上游考察高原的地理交通。崇祯九年(1636)秋末,固始汗率自己的和硕特部众,加上巴图尔浑台吉所派的部分准噶尔部军队,自伊犁地区出发,穿越塔里木盆地,进入青海。到崇祯十一年(1638),固始汗的和硕特部众陆续移牧青海境内。崇祯十年(1637)秋,固始汗本人带领1000多人到了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和索南饶丹等人会见。五世达赖喇嘛赠给固始汗“丹增却吉杰波”(bstan-vdzin-chos-kyi-rgyal-po,执掌教法法王)的称号和印章,还给固始汗的儿子和手下官员赠予称号。固始汗给索南饶丹(又作索南群培,bsod-nams-chos-vphe,1595—1658)和仲麦巴·赤列嘉措(grong-smad-pa-vphrin-las-rgya-mtsho)等达赖喇嘛的主要随从赠予“达赖强佐”“宰桑第巴”等各种称号。同时决定三件大事:首先,共同派遣专人到盛京与当时尚未进关的清朝联络关系。其次,由固始汗进兵康区,消灭康区的白利土司,保证双方的交往和在康区发展格鲁派。再次,在消灭白利土司以后,共同对付第悉藏巴政权。
崇祯十二年(1639),固始汗以康区白利土司崇信苯教、迫害佛教僧人为由,从青海进兵康区,蒙古骑兵行动迅速,经过近一年的战斗,击溃白利土司,占领其统治区域,白利土司被俘获处死。五世达赖喇嘛得知此事后感慨道:“我没有想到笛声(表示和平)已经变成了箭声(表示战争)。”
崇祯十四年(1641)5月,固始汗的大军抵达当雄,在格鲁派的全力帮助下,固始汗集中大部分兵力,在第悉藏巴没有来得及逃跑时,就将其包围在桑珠孜(bsam-vgrub-rtse)城堡中。到崇祯十五年(1642)3月,桑珠孜城堡终于被固始汗和格鲁派的联军攻破,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被俘。固始汗已经成为统治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的汗王,他决定效法藏文史籍中所说的元世祖忽必烈对帝师八思巴三次供养的故事,将卫藏十三万户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他将五世达赖喇嘛迎请到后藏日喀则,举行了隆重的献礼仪式。
在双方都认识到必须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格鲁派上层集团与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联合统治西藏的格局终于形成。在统治方式上,是由固始汗本人设汗庭于西藏,以长子达延鄂齐尔(?—1668)和第六子多尔济(亦称达赖洪台吉)辅佐,以得到五世达赖喇嘛承认的“丹增却吉杰波”(执掌教法法王)的汗王身份君临于甘丹颇章政权之上,直接控制着西藏的权力中心。此外,他对作为他的和硕特部众的大本营的青海湖地区也作了精心安排。自崇祯十一年(1638)和硕特部众陆续移牧那里后,他给他的10个儿子划分牧地和属民,让他们继续率部在那里驻牧,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同时他还命第五子伊勒都齐的儿子罕都(mkhav-vgro)总管康区,带兵在康区驻扎,用康区的赋税收入作为和硕特部收入的补充,即所谓征收康区赋税,以养青海之众,“令子孙游牧青海,而喀木纳其赋,唯以藏、卫二部给达赖、班禅”,使得青海湖地区成了和硕特部众的游牧地,并保证他们在新的住地能够衣食无虞。
在西藏地区,固始汗用“奉献十三万户”的名义,将地方行政事务交给格鲁派管理,甚至将这一联合政权的名字以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宫“甘丹颇章”(dgav-ldan-pho-brang)命名。
但是在人事安排上,固始汗绕开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将甘丹颇章政权权力的实际行使者第巴一职的任命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任命索南饶丹为首任第巴,也就是掌握了主要的人事任命权。
固始汗还不断清除第悉藏巴势力范围内以及后来叛乱地区的敌对教派的寺院,强迫那些支持第悉藏巴的噶玛噶举等教派的寺院改宗格鲁派,并在这些教派僧人的手上打上印记交给格鲁派寺院管理。
固始汗和蒙古首领负责军事行动的指挥,他留下一部分部众驻牧于藏北当雄(dam)草原。遇到战争时,由蒙古军和从西藏各地征集的藏族军队联合行动。军队由固始汗直接指挥,其长子达延鄂齐尔和第六子多尔济有时也领兵担当一个方面的统帅,而第巴索南饶丹等人也有带兵协同作战的责任。在宗教事务方面,则由五世达赖喇嘛和格鲁派上层负责,五世达赖喇嘛除了管理格鲁派的僧人和寺院以外,在固始汗的支持下,也取得了对其他教派寺院的管理权。顺治三年(1645),固始汗赠给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不仅在前藏,也在后藏巩固格鲁派的地位。
早在崇祯十六年(1643)3月,格鲁派决策人物之一的林麦夏仲就提出应在拉萨的布达拉山修建一座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规模巨大的城堡,将格鲁派的色拉寺和哲蚌寺连成一线,使格鲁派在拉萨的防御稳固可靠。布达拉宫从顺治三年(1645)4月破土动工后,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索南饶丹等人始终关注着工程的进程,到顺治六年(1649)底建成白宫部分。在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历辈达赖喇嘛的灵塔也建在布达拉宫。
固始汗看到囚禁中的第悉藏巴仍然对格鲁派构成威胁,还有可能死灰复燃,于是下令把第悉藏巴用牛皮包裹,抛入拉萨河中,以绝后患。清顺治十一年(1654)6月,固始汗在同五世达赖喇嘛巡视前后藏的途中突然患病,藏历十二月八日在拉萨的噶丹康萨(dgav-ldan-khang-gsar)去世,享年73岁。固始汗于崇祯十五年(1642)领兵进藏时已经61岁,在西藏统治了12年。
仲麦巴·赤列嘉措早年随侍五世达赖喇嘛左右,深得五世达赖喇嘛的赏识和信任。第巴索南饶丹去世后,五世达赖喇嘛力排众议,推选赤列嘉措担任第巴一职,“赐给他掌管全部领地的权力,给予达尔罕的印章”,并于顺治十七年(1660)藏历七月十三日,在哲蚌寺甘丹颇章为其举行了就任第巴的仪式,五世达赖喇嘛在这个仪式上把原来赠给达延汗的“丹增多吉杰波”的汗号改为“丹增达延杰波”,达赖喇嘛的权势凌驾于达延汗之上。清康熙元年(1662)四世班禅去世,格鲁派中再没有可以和五世达赖喇嘛相提并论的领袖人物,西藏地方政教两方面的权力就这样都集中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手中。
顺治十三年(1656)的战争并没有解决不丹和甘丹颇章政权之间的矛盾,经过20多年后到康熙十八年(1679)更扩大为不丹和拉达克联合起来与甘丹颇章政权的战争。
二、清廷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与固始汗
固始汗和甘丹颇章采取了巩固政权的各项措施,除派兵镇压各地叛乱外,一是在拉萨与喇嘛人多势众的哲蚌、色拉两寺紧密联系,二是动工重新修建宏伟的布达拉宫,三是寻求新近入主中原的清廷作为靠山。而入关不久的顺治皇帝,一方面还顾不上直接统治西藏这类边远地区,另一方面又需应付尚未很好归附的蒙古各部的威胁。如能拉拢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使之归附朝廷,则于清朝实现其对笃信格鲁教派的蒙古、藏两族广大群众的统治,扩大朝廷之影响至边远的西藏和蒙古各部,都有莫大好处。在这种双方均有策略上的深谋远虑的情况下,遂出现了顺治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和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入京朝见顺治皇帝的重大历史事件。
顺治九年(1652),固始汗上书清朝,称“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在得到朝廷许可之后,班禅额尔德尼、第巴、固始汗等纷纷奉表劝请达赖喇嘛朝觐,奉表奏闻,并贡方物。达赖喇嘛起行之时,固始汗还亲自送了一程。
五世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3000人,经过长途跋涉,于顺治九年(1652)底到达北京,受到顺治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隆重接待。五世达赖喇嘛在京共停留两个月。清廷对之多方优待,专门修建黄寺供其驻锡。顺治皇帝还在太和殿大摆宴席,宴请五世达赖喇嘛。
顺治十年(1653)春,五世达赖喇嘛离京返藏,顺治皇帝赐予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二千两、大缎一百疋及其他贵重礼品,皇太后也赏赐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大缎一千疋。清廷还命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兵士护送其返回拉萨。同年四月,行至代噶(岱海,今内蒙古凉城县)地方。清廷又派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札等颁赐金册金印,对五世达赖喇嘛进行正式册封。顺治皇帝给五世达赖喇嘛金印的印文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顺治皇帝同时授予固始汗金册金印,封“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望其“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分别确定了达赖喇嘛和固始汗在西藏地方政教两方面的统治地位。
三、册封与处置第巴桑吉嘉措
第巴,又称第司,是藏语sde-pa或sde-srid一词的音译,本义为“部落酋长”“头人”。明永乐皇帝钦封仁蚌巴(ring-spungs-pa,明代译为“领思奔”,在今日喀则市仁布县)的南喀杰波为都指挥佥事,给诰命,封为昭勇将军,后其家臣篡立,沿用旧封,史称藏巴汗。其第二代名为丹迥旺波(bstan-skyong-dbang-po,1606—1642),称为“第司藏巴汗”(sde-srid-gtsang-pa),简称第司或者第巴。
康熙八年(1669),“七月里,我(五世达赖喇嘛)派索南旺杰前去青海,主要商议如何决定汗王的人选,顺便也商议一下关于委任第巴的情况。当天良辰,我派尚察官却南杰向他(却本洛桑图多)传达需由他担任(第巴)的缘由。他虽请求认真考虑,但也不便推托……由吠陀论师塔尔巴囊索日吉宁波仔细推算,择定闰八月初一是木曜和轸宿会合的吉日,为第巴就任的日子。于是立即在(布达拉宫)大殿中由却本洛桑图多向我献了汉地产的无量光佛像、绸缎、马匹、茶叶等。然后他就座于第巴的座位时,我交给他大小两颗印章、锦匣、钥匙等”。五世达赖喇嘛得以掌管第巴的任命大权。
1679年,第巴仲麦巴·赤列嘉措的侄子桑结嘉措(sang-rgyas-rgya-mtsho,1653—1705)受五世达赖喇嘛任命担任第五任第巴。1682年二月二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病逝于布达拉宫。桑结嘉措鉴于当时自己所面临的复杂局势,特别是与和硕特蒙古汗王激烈斗争的局势,作出了“秘丧不报”的决定,以继续借用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对外则宣称五世达赖喇嘛已入定,闭关修行,概不见客。同时将长相与五世达赖喇嘛酷似的布达拉宫南杰扎仓的僧人翟热控制起来,软硬兼施地逼他扮作五世达赖喇嘛,以便应付来西藏的朝廷官员或是蒙古重要施主。至于达赖喇嘛的手谕、信札,则由第巴桑结嘉措仿达赖喇嘛的笔迹亲手撰写。
康熙三十二年(1693),桑结嘉措借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请求康熙皇帝加封,《清圣祖实录》记:“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辛未,达赖喇嘛疏言……臣已年迈,国事大半第巴主之,已在睿照中。即第巴向亦仰体圣意,实心行事……乞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康熙三十三年(1694)四月丙申,赐第巴金印,印文曰: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用汉藏满三种文字。“瓦赤喇怛喇”,梵文,意思是“金刚持”;“布忒达”,梵文,意思是佛,也就是“桑结”的意译;“阿白迪”梵文,意思是“海”,就是嘉措的意译。王森先生认为,“布忒达”是梵文(buddha,印文稍讹),意为“觉”,相当于藏文的“桑结”,“阿白迪”是梵文(abdhi,印文作apati讹,或系蒙古人读法),意为“海”,相当于藏文的“嘉错(措)”,“布忒达阿白迪”就是“桑结嘉措”(把藏文换写为梵文,是蒙古人的习惯,清朝也往往沿用这种办法)。
康熙击溃噶尔丹以后,从准噶尔人口中了解到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去世,以及桑结嘉措秘不发丧的事实。于是下了一道诏书,其中说道:“厄鲁特降人告曰,达赖喇嘛久已脱缁矣”,“尔以久故之达赖喇嘛诈称尚存!”“达赖喇嘛者,乃至大普慧喇嘛,本朝为护法之主,交往六十余年;则其讣音即当奏闻于朕。”还提出了严厉的警告:“朕必问尔诡诈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助噶尔丹之罪,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尔,或遣诸王大臣讨尔。”
第巴桑结嘉措看到大皇帝天威震怒,连忙派了桑浦寺上院堪布尼玛塘巴作为代表赴京,向大皇帝密奏。但他隐瞒五世达赖喇嘛去世消息,与当时对抗朝廷的准噶尔首领勾连,受到朝廷的严厉警告和斥责。
在西藏地方,桑结嘉措与蒙古汗王之间的冲突趋于白热化。1701年拉藏汗继位,康熙皇帝册封为翊法恭顺汗。“对于和硕特首领处于无权的状况再也不忍心看下去”,“想在西藏复兴其祖先为本家族取得的统治”。拉藏汗始终怀疑是第巴桑结嘉措主谋毒死他的父亲达赖汗,又怀疑他是不是正在对自己下毒手。拉藏汗还利用噶尔丹事件,加深了康熙皇帝对第巴桑结嘉措的不满与不信任,以至产生恶感,同时,不断上报仓央嘉措行为不端,是假达赖。一种说法认为,桑结嘉措曾买通汗庭的人给拉藏汗的饮食下毒,被其他人员发现。1703年藏历新年传大召法会期间,拉藏汗借机杀掉了桑结嘉措的几个亲信,桑结嘉措则纠集兵力迫使拉藏汗退出拉萨,后撤到藏北达木。在双方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拉萨三大寺的代表,特别是拉藏汗的经师嘉木样协巴出面进行调解。桑结嘉措被迫让出第巴职位,由其儿子阿旺仁钦继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西藏的蒙藏统治阶级冲突以后,拉萨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的代表和安多地区的高僧、拉藏汗的经师嘉木样协巴出面调停,双方在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前达成协议,规定拉藏汗撤回青海,第巴桑结嘉措退居山南(今西藏泽当一带),双方脱离接触。但是调解终归无效,拉藏汗从藏北达木兵分三路攻打拉萨,双方的主力在拉萨以北盆域(今彭波)的郭拉山口展开了决定性的一战,第巴桑结嘉措统率的藏族民兵,抵挡不住拉藏汗蒙古骑兵的凌厉攻势,死伤众多,全线崩溃。第巴桑结嘉措兵败后乘牛皮船沿拉萨河逃到曲水,但是最终还是被蒙古军队生擒,送至拉藏汗的王妃才旺甲茂军前。才旺甲茂正在堆龙(今堆龙德庆区)准备进攻拉萨,第巴桑结嘉措被擒获的当天,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被处死在堆龙德庆宗的囊孜,据说行刑者是拉藏汗的妻子才旺甲茂。在文化和重修布达拉宫等方面有建树的桑结嘉措就这样结束了他富于传奇的一生。
四、纷争之中的“六世达赖喇嘛”
清朝初年西藏地方蒙藏上层贵族的内讧,给地方政治局势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也引发了达赖喇嘛废立不常问题。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圆寂,终年66岁。五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使五世达赖喇嘛一手提拔起来的第巴桑结嘉措面临一个严峻的局面,甚至有失去一切权势的危险,因此,为了驱赶蒙古和硕特部的势力出西藏,巩固自己的实权,第巴桑结嘉措采取了匿丧,即封锁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既不让外界知道,又不向清廷奏报,同时,桑结嘉措于康熙二十一年秘密地在门隅找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即仓央嘉措。他还积极联合活动在今新疆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力量,试图应对和打击在西藏的和硕特部汗王势力。此外,他还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请求清廷册封。清廷给予封号,但只限于宗教事务。
康熙三十五年(1696)噶尔丹兵败自尽,反清之乱结束。康熙帝从噶尔丹俘虏中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已圆寂多年,第巴桑结嘉措匿丧不报,又勾结噶尔丹,于是致书怒斥桑结嘉措。桑结嘉措向康熙帝上书,对这些责问作出辩解,并奏报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和寻获转世灵童的情况。
清廷考虑到刚打败噶尔丹,内地需要休养生息,同时为了安定西藏,因此未对桑结嘉措深究,并准许转世灵童仓央嘉措正式坐床,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10月25日迎入布达拉宫成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但是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六世达赖喇嘛厌烦修道,不听第巴桑结嘉措和五世班禅的教诲,不愿意受比丘戒,甚至将原先所受沙弥戒还给了五世班禅,进而公开声称自己不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公然声称:“我本无占据五世达赖喇嘛之位之意,亦无骗人讲经授戒之意。所以对修学之事不甚用心。”甚至还要“将退还从前所受之沙弥戒。如不答应,我将谢世”。
拉藏汗在打败桑结嘉措后,派人前往北京,指责仓央嘉措是“假达赖”,请求清廷予以废黜,另立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康熙帝对桑结嘉措不满,对他擅自所立的仓央嘉措也不放心,于是采纳了拉藏汗的建议。清廷担心仓央嘉措留在西藏会引起动乱,于是下令将仓央嘉措解送北京。康熙四十五年(1706)5月,仓央嘉措被废黜,并被解送北京。10月,行至青海湖附近圆寂,年仅24岁。
在仓央嘉措被废黜后,拉藏汗另立一个年轻喇嘛为六世达赖喇嘛,取法名意希嘉措,康熙帝依据五世班禅和拉藏汗所奏,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赐给意希嘉措六世达赖喇嘛的册命。但并未得到僧俗各界的承认,后又被进入拉萨的准噶尔军人所杀(一说送往内地)。因此,拉萨三大寺上层坚持为六世达赖喇嘛寻找转世灵童。
三大寺僧人从仓央嘉措的一首诗歌“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理塘就回来”中得到启示,在今四川理塘找到了转世灵童即格桑嘉措。清廷坚持格桑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是接替被废黜的仓央嘉措的法位。在驱除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军,平定西藏之后,康熙皇帝“赐今胡必尔汗册印,封为第六辈达赖喇嘛,安置禅榻,抚绥土伯特僧俗人众,各复生业”。至今保存在西藏拉萨龙王潭的康熙帝《平定西藏碑》(康熙六十年,1721年立),仍称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
五、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
班禅世系始自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像达赖喇嘛世系一样,前三世班禅也是追认的。
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是为格鲁派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由于争夺权利,西藏地方首领藏巴汗不让达赖喇嘛转世,罗桑却吉坚赞治好了藏巴汗的病,才说服其准许寻找转世灵童。当然土默特蒙古部的压力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后来罗桑却吉坚赞与五世达赖喇嘛商议,于1641年(明朝崇祯十四年)将从新疆进入青海的蒙古势力固始汗部引入西藏,一举消灭了藏巴汗。清朝顺治三年(1646),固始汗赠予罗桑曲吉“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
康熙四十九年(1710),清朝根据拉藏汗和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贝桑布(1663—1737)之请赐给意希嘉措六世达赖喇嘛册命,但也了解到西藏僧俗各界不拥护拉藏汗之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以及人心浮动的情况。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廷派专人到西藏,正式册封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名号,并颁金册金印。清圣祖谕理藩院:“班禅胡土克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甚属可嘉。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金印,封为班禅额尔德尼。”
钦差大臣策楞在扎寺宣读的圣旨中称“……班禅呼图克图历代勤勉宗喀巴教……不趋附横逆之事,每年恭派使臣请安进贡,自始至终,虔诚如一,甚属可嘉……为保障扎什伦布寺所属寺庙原征赋税,永不为他人侵占,兹封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颁给金册金印”。
清朝之所以要册封五世班禅,是因为格鲁派的达赖喇嘛系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为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局势。这样,如果西藏一旦发生意外变故,除了有争议的达赖喇嘛意希嘉措外,还可由清朝正式册封的班禅来主持格鲁派的事务。从此,班禅的宗教领袖地位得到了清朝的确认,历世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权的册封,并成为定制。
雍正六年(1728),清军入藏平息“阿尔布巴之乱”后,雍正帝派遣钦差查郎阿进藏,要把后藏和阿里地区封给五世班禅管辖;五世班禅考虑到前、后藏地方势力间的关系,以西藏内部团结为重,拒不接受;后经查郎阿说服,五世班禅最终还是接受拉孜、昂仁、彭措林三个地区归班禅系统管辖。从此,班禅系统的拉章成为归清廷领导、受驻藏大臣监督的所属领土及辖区的地方政权,而不接受拉萨的噶厦管辖。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阿音娜:林芝访古——碑与墓|“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课题组成果
喜饶尼玛、邱熠华:民国时期拉萨测候所的建立及历史意义
魏文:瀛国公赵㬎与合尊法宝——从末代皇帝到雪域高僧的传奇一生
魏文、谷新春|从玛哈噶喇庙到普度寺:从旧影与遗存重构北京普度寺慈济殿的原貌
刘星雨:绿营视域下的帝国边疆——图解“营制总册”《云南标下元江营》
阅读 230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