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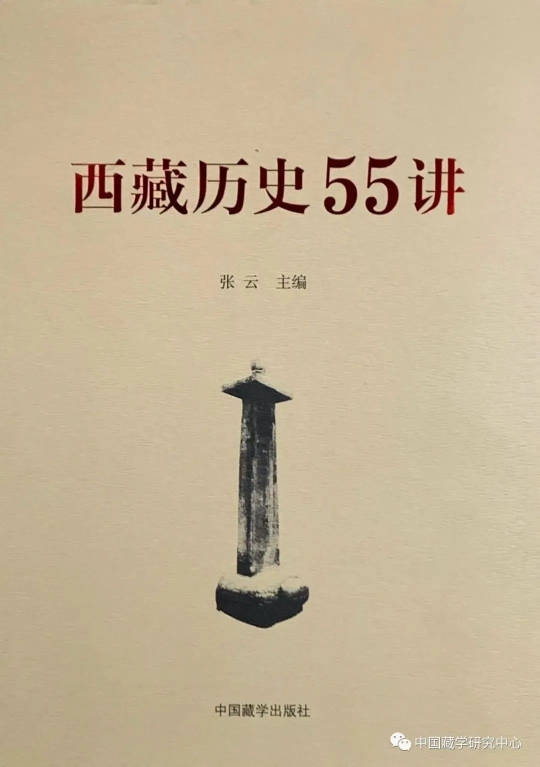
第2编 元朝西藏历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统一、隋唐统一之后第三个大一统时期,为中国历史版图的奠定、中华民族的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元朝时期将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在中央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任命官员、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建立驿站、驻扎军队,实施了充分有效的行政管辖,让西藏地方更加密切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有许多人物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许多事件感人肺腑,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壮怀激烈的伟大情怀,看看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第12讲 社会变革者帝师八思巴的故事
在元代西藏巨大的社会变革中,萨迦五祖八思巴是变革时代产生的历史名人,他一生的活动也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变革。
一、早年经历
八思巴于藏历第四饶迥阴木羊年(1235)三月六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据说他因此而有一个小名叫类吉(lug-skyes,意为羊年生人)。八思巴的父亲桑察·索南坚赞生于阳木龙年(1184),是萨迦班智达的弟弟。他娶了5位妻子,长妻玛久衮吉是朵格察地方人,于1235年生八思巴,1239年生恰那多吉,第二个妻子玛久觉卓于1238年生仁钦坚赞,第五个妻子多吉丹(原是第三个妻子的侍女)于1238年生意希迥乃,第二个妻子玛久觉卓还生了一个女儿多岱,第三个妻子拉久则玛生女儿索南本和尼玛本,第四个妻子觉摩霍江生女儿仁钦迥乃。这样,八思巴同父的兄弟姐妹共计8人,八思巴是家中的长子。藏历阴土猪年(1239)十二月二十二日,桑察·索南坚赞在拉堆地方去世。此时八思巴年仅5岁,恰那多吉刚出生不久,教育和抚养幼小的八思巴兄弟的责任就由伯父萨迦班智达承担。
据记载,八思巴自幼聪明颖悟,加上有萨迦班智达这样的名师悉心教导,他在佛学上的进步很快。《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三岁时,能记诵莲花修法等,众人惊异,说:‘他果真是一位圣者!’由此名声远扬,故通称其名为八思巴(vphags-pa,藏语意为圣者)。八岁时能记诵佛本生经。九岁时,在萨迦班智达举行的预备法会上,八思巴讲说萨迦派道果法的主要经典《喜金刚续第二品》,大众惊异,众学者也抛弃傲慢之心而听受,八思巴声名远扬。”《元史·释老传》也记载:“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班弥怛。”八思巴于赴凉州的途中在拉萨地方(有的说是在拉萨大昭寺觉卧佛像前)从萨迦班智达和苏浦巴受沙弥戒出家,起法名为洛追坚赞贝桑布(bl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成为一名学经僧人。关于八思巴随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后的生活情况,直接的记载不多。我们只知道按照阔端的安排,八思巴继续跟从萨迦班智达学习吐蕃教法即西藏佛教,恰那多吉穿着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语言。由于萨迦班智达的精心教诲,加上八思巴的勤奋和聪颖,他的学业进步很快,到17岁(1251年)时八思巴已学完萨迦班智达教授的所有教法,掌握了担任萨迦派教主必须具备的知识。1251年藏历十一月,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去世,授衣钵给八思巴。这样,年仅17岁的八思巴就成为萨迦派的新教主。
1248年,阔端的哥哥贵由汗在横相乙儿地方病死,1251年6月,蒙古在阔帖兀阿阑之地召开大会,推选蒙哥继大汗位,蒙古皇室内部的这一次权力转移,对当时西藏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哥汗从阔端手中接管西藏的统治权之后,即派人入藏清查户口,也即是进行括户,将西藏各地重新分配给他本人和同母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作封地。五世达赖喇嘛认为,这先是诸王子在西藏各自取得了一块封地,再选择封地内最有影响的教派作为自己的福田,也就是供奉的上师,该教派也就依靠这一层关系在该王子的封地内取得了控制权。由于蒙哥汗的分封,在西藏各封地内出现一个占优势的教派,逐渐从政治经济上趋向于集中。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诸弟后,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内按蒙古投下制度委派官员管理,这种官员藏文称为达鲁花赤(dar-ga-che),或意译为yul-srungs(意为守土官、守护地方官)。从此以后,西藏无论哪一个教派和地方势力,要想取得对其他势力的优势地位和掌握西藏地方政权,都必须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这就迫使西藏宗教和政治领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与内地建立密切关系上来,而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也需要扶植这些人作为代理人,保证疆土的完整和边疆的安宁。蒙哥汗的作为,实际上是通过分封和结交宗教上层领袖的方式,达到了统一西藏的目的。
1252年7月,蒙哥汗命忽必烈率西路大军远征大理,绕道至湖北与中路军会合,以控南宋后背。当时南宋还控制着四川,忽必烈只能穿过甘青、川西藏族地区直捣大理,在此情况下藏族地区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公元1252年夏天,忽必烈率大军抵达六盘山、临洮,大约因为即将进入藏族地区,忽必烈派人就近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军营,以备咨询。八思巴利用在凉州时学到的历史知识,包括对汉文史籍《唐书·吐蕃传》的了解,以及吐蕃、西夏王朝尊信佛教的历史传统来影响忽必烈,使忽必烈从利用西藏佛教转变到崇拜西藏佛教。八思巴巧妙的宗教宣传,很快就对“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一家人产生了作用,使他们认识到要得到佛教徒的拥护,还需要仿照历史上崇佛帝王的先例,与八思巴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在忽必烈的王妃察必的带动下,忽必烈答应从八思巴接受喜金刚灌顶。但是,当忽必烈请求八思巴传授喜金刚灌顶时却遇到了困难。八思巴提出灌顶之后忽必烈应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的礼节来尊奉上师,“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这一条件实质上会导致将佛教的教权置于世俗王权之上,当然使忽必烈感到难以接受。这时,又是王妃察必出来调解:“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命。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要讲论及请求。”在这一折中条件下,八思巴于19岁的阴水牛年(1253)新年时在军中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正式成为当年已38岁的忽必烈在宗教上的老师。忽必烈当时只是一个宗王,但是他尊八思巴为上师,并赐羊脂玉印,还奉献黄金及珍珠镶嵌的袈裟、僧衣、金座、伞盖等作为灌顶的供养,足见忽必烈对于他与八思巴的宗教关系的重视。1253年忽必烈从八思巴接受密宗灌顶一事,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及中央王朝对藏族地区实行的政策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对八思巴执弟子之礼,可以说是后来元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设立帝师制度的滥觞。而王妃察必所提出的处理皇权与教权关系的原则,后来也都一一付诸实行。
本来八思巴要按萨迦班智达的遗言返回萨迦跟从伍由巴大师等人受比丘戒。当他到达朵甘思(今四川甘孜、西藏昌都)地方时,从来往各地的客商口中听到伍由巴大师已经去世的消息,于是中途折回,与1254年初奉蒙哥汗之命从云南军中返回的忽必烈会合,一同前往汉地。《萨迦世系史》所说的听到伍由巴大师去世的消息可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八思巴在朵甘思得到了西藏形势变化的某些消息,促使他下定决心投奔忽必烈并追随忽必烈到汉地。1254年初蒙哥汗已完成在西藏的户口清查和划分兄弟诸王封地的工作,并委任各地方首领担任万户。由于萨迦派是划给阔端的后裔掌管的,所以在这次权势的重新分配中萨迦派从领先于其他教派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此时蒙哥汗已召请帕木竹巴派的多吉贝、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到他的宫廷,而萨迦派却没有人接到召请,形势的发展显然会对萨迦派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八思巴如果返回萨迦,难以有所作为,对萨迦派的发展也不会有大的帮助。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八思巴才决然改变计划,重新回到忽必烈的身边,决心利用与忽必烈已建立的关系,等待时机,改变萨迦派面临的被动局面。
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关系日益密切,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八思巴年轻聪明,勤恳好学,谦逊平和,学识渊博,是忽必烈喜爱他的重要原因。另外,八思巴善于传教,不拘泥于佛教经典中的条文,巧妙地将忽必烈一家与佛教连在一起,以佛教的形式道出忽必烈内心的愿望,将佛教“慈悲护持众生”的思想与忽必烈的“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思想结合起来,使忽必烈相信要治平天下,君王必须争取佛教的护佑,因而受到忽必烈一家的敬重。这也是忽必烈很快就将他奉为精神上的导师的决定性因素。
1258年8月,蒙哥汗亲率大军分路南下,进攻南宋。蒙哥汗自领西路军,由陕西入四川,起用忽必烈总率东路军渡淮河攻打鄂州。1259年初,蒙哥汗进迫合州城下,久攻不克,于7月病死军中。忽必烈得到察必王妃传来的消息,说留守漠北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准备召集王公大会,夺取蒙古大汗位,于是忽必烈与南宋丞相贾似道匆忙约和,渡江北返,于11月底到达中都(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大约与忽必烈返抵中都同时,八思巴也与忽必烈的眷属一起抵达中都,八思巴著作《赞颂之海——诗词宝饰》一篇的题记中说:“说法比丘洛追坚赞贝桑布阴土羊年(1259)冬十一月于汉地无数帝王出世之地、为众多吉祥之相严饰之中都大城写就。”《为大乘经藏开光而作》一文也记为“洛追坚赞贝桑布阳铁猴年(1260)春正月二十一日写于汉地中都城”。因此可见八思巴这时是到了金朝的中都即后来的元大都、明清时代的北京城,也可以说八思巴是第一个到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
二、担任国师
1260年3月,忽必烈召集支持自己的蒙古宗王在开平府举行忽里台大会,通过例行的选举仪式,宣布即蒙古大汗位,建年号为“中统”。5月,阿里不哥另召集一批亲附于自己的宗王在阿勒台的驻夏之所举行大会,也宣布即蒙古大汗位,随即率漠北蒙古军分路南下,与忽必烈争位。1260年12月,忽必烈在初步战胜阿里不哥之后返回中都,立即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释教。作为国师,八思巴首要的任务是为皇帝、后妃、宗王、皇子们传法授戒,传授灌顶。在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影响下,忽必烈宫廷的生活逐渐充盈佛教的内容。为了实地了解蒙哥汗去世后西藏各教派的实际情况,同时祈求佛教的护佑,忽必烈于1262年派遣金字使臣入藏,向各教派的寺院奉献布施,并举行法会,这大约也有宣谕新即位的大汗对西藏的德惠的含义在内。忽必烈的这一行动,也得到八思巴的大力配合。1262年2月8日,八思巴在大都写了一封致乌思藏诸大德的信。信中首先向乌思藏的僧众遥致问候,接着写道:“我们的上师法主具有无量智慧及慈悲,不顾自身的安乐利益,为了整个佛陀的教法及众生的利益,前来皇子驾前,其利益大众之事业众人皆心中明知。继他之后,我亦尽我之所能服事佛法,利益众生。尤其是当今大皇帝的心中怀有以公正的法度护持整个国土、使佛法弘扬之善愿,我留住于他的驾前,并非为了一己之利,而是为了使其理解佛陀教法、明辨取舍、善为区分佛法及冒充佛法的邪说,使其如先前所有的法王那样成为教法之王。我曾多次奏请利益整个佛法及所有众人之事,请求颁发有益之诏命,众人心中当已明知。特别是由于我先前多次奏明佛教根本戒律清净、有讲经听法之规,应大利佛法,故此次皇帝派遣金字使臣送来举行法令之资具。望各位大德及僧众合力祈愿大皇帝长寿、顾念佛法,为使教法弘扬,有情众生平安幸福,随时说法听经、修习禅定、依法念诵、讲论,成就善业。望僧众齐心和睦清净祈愿。举行法会之后,亦愿在一切时中努力说法听经。我将尽力使你们所有僧众能够安心听经说法,完成诸法事。”
八思巴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向忽必烈举荐佛教方面的人才,其中有一些人是先依八思巴学佛,然后被推荐到朝廷任职的。另外,八思巴作为萨迦教派的领袖和昆氏家族的首领,当然会引进其亲属和门下弟子。八思巴的同母弟恰那多吉大约也于此时来到大都,受忽必烈喜爱,后被封为白兰王。八思巴的异母弟仁钦坚赞大约也在至元年间到达大都,继八思巴之后担任忽必烈的帝师,另一异母弟意希迥乃到大都后被忽必烈之子忽哥赤迎去藩邸,奉为上师,忽哥赤受封为云南王时随往云南,在那里去世(一说逝于朵甘思)。这样,由于八思巴受封为国师,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对忽必烈一家的影响日益增大。1264年,忽必烈为国师八思巴在朝廷中设置了一个称为“总制院”的机构。后来这个机构改称“宣政院”,其职责是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总制院”受国师八思巴领导,八思巴还可以举荐总制院的官员。这样就使八思巴具有了行政官员的身份和职权。
八思巴参与管理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忽必烈建立藏族地区的驿站,开通西藏到内地的驿路。藏族居住的青藏高原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气候条件恶劣,交通十分不便。无论是藏族本身建立的王朝还是中原王朝为实现对藏族地区的有效控制,都必须建立一个严密的驿站系统来传递消息、维持交通、接待过往人员、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吐蕃就在青藏高原的各个主要地区之间设置过驿站,用以维持王室和派往各地的官员和军队的联络,指挥数千里外的军事行动。忽必烈即位后,为加强对藏族地区的实际控制,在西藏推行政令,在中统年间派遣了一个名叫答失蛮(das-sman)的官员进藏,从青海开始一直到朵甘思、乌思藏,清查沿路人口、物产、道路情况,设置驿站,召集地方首领,宣布八思巴的法旨和皇帝的札撒(诏书),建立了一条直接通到萨迦的驿站。元代乌思藏的这条驿路上,有11个大站,有不少在现在的地名中还可以找到。其中索驿站(sog)显然是今天那曲市索县县城所在地,索驿站后面的夏克驿站(shag),其地名也至今犹存,在今比如县西北部的夏曲镇。从索县到夏曲镇路程为100公里多一点,因此可以推测元代西藏的各大驿站之间的距离大约是100公里。后藏的达驿站(stag),其地名也至今犹存,即今日喀则市和南木林县交界的大竹卡(stag-gru-kha),意为达地方的渡口。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仍然是南木林到日喀则必经的渡过雅鲁藏布江的渡口。再下一个驿站春堆驿站(tshong-vdus)在大竹卡以西100多公里(即今天的日喀则市区附近),藏文史籍记载历史上年楚河下游就有一个叫作春堆的著名的贸易市场。元代藏族地区驿路的开通,对驿路沿线的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乌思藏地区各个万户要承担维系驿站的义务,派遣人员到驿站承担差役。
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就将诸王在西藏的封地全部收回,只有在反对阿里不哥的战争中为争取旭烈兀的支持而保留了旭烈兀在西藏的封地。当时忽必烈已经考虑到要设置中央王朝的机构对西藏进行统治,同时也认识到藏传佛教僧人在统治西藏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把实现新王朝对西藏的统治、在西藏建立新的行政体制的重任交给了他最信任的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经过认真考虑和准备,1264年,忽必烈决定派八思巴及其弟白兰王恰那多吉返回萨迦去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在八思巴临行时,忽必烈赐给他一份诏书,藏文史籍中通常称之为珍珠诏书,具有委派八思巴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建立行政体制的授权证书的性质。从此以后,元朝历代皇帝给帝师颁赐珍珠诏书成为一种惯例,珍珠诏书也成为帝师和萨迦派在西藏的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元史·释老传》说:“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南村辍耕录》诏西番条则说:“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绘,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所居处。”
八思巴回到西藏时,当时西藏是封建农奴制度发展巩固的时期,各地的世俗封建领主占有许多庄园,各教派的寺院和宗教领袖也占有庄园和农奴,僧俗封建领主之间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农奴的隶属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已建立起来,但是这种关系只是封建领主凭借自己的势力完成的事实上的占有,封建农奴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并不完全确定,特别是随着僧俗封建领主间的斗争和战乱,对农奴的占有关系仍然在不断地变动。随着西藏纳入元朝中央的行政管辖,西藏在政治上开始走向统一,这就需要建立稳固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秩序,明确封建领主对农奴的占有关系。八思巴为此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第一个步骤是划分俗人民户和寺属民户,也就是藏文史籍中所说的划分米德和拉德。米德(mi-sde)是世俗领主所占有的农奴,在人身上要依附于自己的领主,世代保持着这种依附关系。在元代,米德不仅要向自己的领主承担劳役和贡赋等封建义务,还要为元朝承担维持驿站等劳役和交纳税赋,因此国家对米德也有一定的管辖权。米德对国家承担的劳役,藏语是用一个蒙古词“乌拉”来表达的,这正说明对国家承担劳役在当时的藏族社会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拉德(lha-sde)是佛教寺院和宗教领袖所占有的农奴,人身依附于寺院或宗教领袖,世代要向寺院和宗教领袖承担封建义务。在元代,佛教寺院和僧侣是免除兵役、劳役和赋税的特权阶层,甚至寺院的属民也是免差免税的。寺属民户的任务是供养僧人和寺院,使僧人和寺院能够“祝延圣寿”,为皇帝效力,这与元朝皇室在汉地建立佛寺、赐给土地和民户的用意是一致的。划分拉德和米德在西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以牢固的世代领属关系为元朝统治下的萨迦派的政教合一统治奠定了基础。从西藏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八思巴划分拉德和米德,实际上是代表元朝取得对西藏僧俗封建领主占有农奴的封授权。吐蕃王朝崩溃后的400年藏族地区分裂时期,各地的大小封建领主分裂割据、自相混战,农民被迫沦为某一领主的农奴,或自动依附于某一领主充当农奴,自由农民这一阶层已基本不存在,藏族社会由农奴主和农奴两大阶级组成。封建领主占有农奴,不是依据某种法律或某一政权的封赐,而是依据自己的实力,因此僧俗领主争夺农奴的战乱接连不断。八思巴划分拉德和米德,是在元朝实现对西藏的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掌握对封建领主封授和没收农奴(包括土地)的权力,把领主和农奴的阶级关系纳入统一国家的法律和行政制度之中。然而这正构成了元朝统一西藏的政治基础,也成为西藏历史的转折点。元朝以后,西藏无论哪一个封建领主或教派建立起地方政权,都要争取中央王朝的承认,并在内部重新确认和封授农奴和土地,也是沿袭了元代西藏的政治体制。
在划分米德和拉德的基础上,八思巴又主持划分十三万户,调整和确定各万户的辖区,委任万户长和千户长,建立万户的管理机构。在十三万户中,拉堆洛、拉堆绛、曲弥、夏鲁、绛卓、羊卓、甲玛、嘉域、达垅等万户没有控制政教权力的教派,绛卓、羊卓是为有功的萨迦本钦而分设的万户,嘉域是“由嘉域地方的1000户人家、主巴地方的950户人家共计1950户人家组成一个万户”,这说明它们都主要是地域性的行政机构。止贡、帕竹、蔡巴、雅桑4个万户虽然有控制万户政教权力的教派,但也并不完全是按教派组织的万户。八思巴划分十三万户,在西藏历史上是一个进步,是从家族和教派政治走向地域政治必然要迈出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触及一些教派和家族的权益,引起矛盾和冲突。八思巴划分十三万户,是经过复杂的斗争才最终完成的。
在划分米德和拉德、十三万户的基础上,八思巴在萨迦建立起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萨迦地方政权,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政权。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即是八思巴。八思巴以后是历任帝师,当帝师住在大都时,萨迦政权即由萨迦寺的住持或通常所说的萨迦法王负责。萨迦政权首领的职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据元朝皇帝的封授,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首领对各教派的寺院、僧人、拉德行使管辖权,帝师颁布法旨与皇帝诏旨并行于西藏,即是这种管辖的一种方式。二是依据元朝皇帝的授权,掌管西藏行政机构如万户、千户的设置划分,给有功人员赏赐农奴、庄园等,对反抗元朝和萨迦政权的贵族和寺院,则没收其庄园和农奴。三是举荐和委任西藏各级官员,萨迦政权的本钦、朗钦和各万户长,由帝师举荐皇帝任命,千户长以下官员以及萨迦的拉章和勒参的官员由帝师任命。四是通过萨迦本钦处理西藏的行政、户籍统计及诉讼等事务。在帝师和萨迦寺住持之下,设置本钦一员,掌管萨迦政权的行政事务。萨迦政权还设立过管理萨迦政权内部事务的朗钦和一些管理专门事务的机构勒参,《后藏志》记载,江孜法王帕巴贝桑布在任萨迦朗钦之前,曾受命掌管萨迦设立的管理朵甘思地区事务的4个勒参(机构)中的夏喀勒参,因而其家族后来被称为夏喀哇家族。这种勒参即是清代西藏地方政府的各个勒空(机关)的雏形。
由于萨迦政权是以佛教僧人为最高首领,在行使职权时又与藏传佛教各教派密切相连,而且这种行政体制得到元朝皇室的承认和支持,因此八思巴为便于行使自己的政教管辖权力,创设了一个叫作“拉章”(bla-brang)的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官员在当地都算是贵族,有官阶品级和官俸、官服。
八思巴按照忽必烈的旨意在西藏建立的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管辖十三万户,同时受白兰和西平王监督,西藏这种行政体制基本上沿用到元末。这一体制建立之初就是遵循在元朝中央政府治理下既适应西藏社会特点又尽量与全国行政制度相一致的原则。八思巴去世后,元朝又在西藏增设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但是八思巴建立的西藏行政体制的主要部分并没有改变,这说明它确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对元朝统一西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像这样设置衙署、赠给藏传佛教上层人士各种官衔、出行有大批前导随从的宗教领袖,在藏传佛教史上八思巴还是首次,因此他也遭到一些主张摈绝尘世潜心修习的僧人的讥讽。八思巴批驳了这些人的责难,提出了按照情势教化众生的思想,代表了当时藏传佛教各派的发展潮流。
八思巴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在1267年在进京途中,还在拉萨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即兴建萨迦大殿(亦称萨迦南寺)。萨迦南寺在建筑形式上,选择了城镇与寺院结合的外形为城堡、中心为佛殿的设计,因而使萨迦南寺在建筑上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同于以往西藏的任何佛教寺院建筑。八思巴决定兴建萨迦南寺,不仅对萨迦派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萨迦地方政权建立的标志,也是这一政权通过向十三万户征派物资、劳役显示自己在中央朝廷的支持下所取得的权威地位的重要途径。萨迦南寺的建成,不仅显示了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西藏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表现了西藏统一于祖国之后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迅速进步。
三、创制文字
1268年底或1269年初八思巴一行抵达大都,受到隆重欢迎。《拔思发行状》说:“甲戌,师年36岁,时至元十一年(行状作者王磐将八思巴生年误为1239年,故记年有误),皇上专使召之。岁杪抵京,王公宰辅士庶离城一舍,结大香坛,设大净供,香华幢盖,天乐仙音,罗拜迎之。所经衢陌,皆经五彩,翼其两旁。万众瞻礼,若一佛出世。”《萨迦世系史》则说:“当八思巴到达朝廷时,大皇帝的代摄国政的长子真金、后妃、大臣等众人前来迎接,仪仗有背上安设珍宝璎珞装饰宝座的印度大象,飘扬着珍贵锦缎缨穗的伞盖和经幡、旌旗以及盛大的鼓乐,用大供养迎入宫中,请教各种博大精深的教法,使佛法犹如明月在莲园中升起。”
1270年,八思巴向忽必烈献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下诏颁行,诏书中说:“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例。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遂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时至元七年,诏制大元国字。师独运摹画,作成称旨,即颁行。朝省郡县遵用,迄为一代典章。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呈献的字样是用蒙古新字书写的一份优礼僧人诏书,可见这种蒙古新字在呈献时已达到可以使用的程度。忽必烈1270年封八思巴为帝师与他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一样,也是为改国号正式建立新朝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也就在1270年,八思巴的弟子、四川汉族僧人元一(藏文记为一讲主,yi-gyang-ju)刻印佛教经藏完成时,八思巴为之题写赞语,其中说:“蒙古之主自太祖起,第五传为具足功德之皇帝汗,其在位时之至元七年,法主萨迦巴所传八思巴帝师之弟子、生于四川地方之一讲主,悉心学习佛法,对汉地、吐蕃、尼泊尔、印度等地区之圣地及学者生起正见,从彼等处获受恩德,思有以报答,乃将佛法经论刻印完毕,成就一大善业。愿因此善德使教法遍弘、佛陀之意愿成就、皇帝陛下长寿、依教法护持国政、国土清净安乐。此文乃因一讲主一再劝请,比丘八思巴为善业之故写成。愿各方一切吉祥!”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八思巴的著作中唯一的一次称自己为帝师,说明他在至元七年已有帝师的封号。八思巴的弟子胆巴在至元七年冬至后二日为八思巴奉诏所撰《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所写的序文中说:“爰有洞达五明法王大士萨思迦扮底达名称著闻,上足苾萏发思巴,乃吾门法王,大元帝师,道德恢隆,行位叵测,授兹仪轨,衍行中原。”可以此证实八思巴受封帝师是在1270年。帝师作为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同时也是皇室在精神上的支柱,又是全国佛教僧人的领袖和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首领,所以其地位是极其高的。
四、荣归故里
约在1271年夏初,八思巴离开大都出居临洮。临洮在宋金时为熙州,宋朝曾设熙河路。1235年,阔端由秦、巩一路南下四川,曾招降这一带的藏族部落,后元朝设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成为在蒙哥汗时期设置的吐蕃宣慰司(朵思麻宣慰司)以外的西北主要藏族地区。从至元初年开始,蒙古进攻南宋的四川的军事行动中,巩昌路成为元朝西路重要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八思巴到临洮,一种可能是用帝师的威望安定甘青藏族地区,保证元军攻蜀的胜利;另一种可能是协调在甘青的阔端后王、朵思麻宣慰司、巩昌总帅府之间的关系。八思巴的政治活动又总是与宗教活动相联系。《安多政教史》说八思巴在临洮时派四大弟子把朵思麻南部地区的苯教分别予以改宗萨迦派,在其地建立寺院和香火庄。在临洮城里有八思巴的弟子达温波奉师命创建的香衮大寺,最盛时有数千僧人,寺内还有八思巴指示塑造的八思巴像,直到清代,临洮还有8座属于萨迦派的寺院。著名的卓尼禅定寺,也是八思巴派遣弟子喇嘛格西巴在卓尼土司家族的资助下兴建的。八思巴通过一系列的传法建寺活动,扩大了萨迦派在甘青藏族地区的势力,同时也使元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1274年3月,八思巴又在皇太子真金的护送下,离开临洮向萨迦进发。但是关于真金太子护送八思巴回萨迦的说法,在汉文史料中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八思巴自己所著的《彰所知论》的赞语中说:“种相富具足,睿智皇太子,数数求请故,慧幢吉祥贤(即八思巴),念往日藏论,起世对法等,依彼造此论。”又在题记中说:“彰所知论者,为菩萨真金皇太子求请故,法王上师萨思迦大班弥达足尘顶授比丘发思巴慧幢吉祥贤,时壬寅(1278年)仲秋下旬有三鬼宿直日,于大吉祥萨思迦法席集竟。持经律论妙章并智师子笔授。”从真金1273年立为皇太子到1278年之间,真金能够向八思巴“数数求请”佛法,也只能是因为真金沿途护送八思巴到萨迦才能做到。八思巴曾经到内地多年,长期跟随忽必烈,见多识广,当时蒙古宫廷接待来自各地的人物无数,八思巴自然亦有参与。而且他主持总制院(宣政院),总领天下释教,与宗教有关的事务都少不了他的指导。故而我们可以说,《彰所知论》尽管只是一部综合佛教教理与历史传承的简明读本,但它显然具有非常特别的史学意义。尤其它第一次正式地把印度、西藏、蒙古的王统历史与佛教史加以并列,将眼光从青藏高原转向更大的空间。
八思巴离开大都后,照例在每年年底写一篇新年吉祥祝词寄献忽必烈。1276年12月25日,八思巴在萨迦寺写祝词寄献忽必烈,这说明约在当年年底,八思巴和真金皇太子一行抵达了萨迦。1277年正月,由八思巴发起,在后藏的曲弥仁莫(今日喀则市曲美乡)地方举行了有乌思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萨迦世系史》说:“此后,在阴火牛年春正月,由汉地之王真金担任施主,在后藏曲弥仁莫举行大法会,法王八思巴向七万多僧人供献丰盛的饭食,为每名僧人发放黄金一钱,三衣(指僧人参加法会时所着之袈裟)一件,并广为宣讲佛法。参加法会的僧人有七万,可以讲论几部经典的格西数千,加上一般民众,总数达十万人之多。法王八思巴授予他们走向成佛大道的大乘殊胜菩提发心,众人亦立愿只做能获得无上正果之菩提行。”《汉藏史集》说八思巴为这次法会捐献了黄金963两3钱,白银9大锭,锦缎41匹,彩丝缎838匹,绸子5858匹,茶叶120大包,蜂蜜603桶,酥油13728藏克,青稞37018藏克,炒面8600藏克,其他零碎物品不计其数。皇太子真金向参加法会的七万余名僧人分三次发给每人一钱黄金。这次大法会在曲弥寺举行,为期14天。显然,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法会是为了明确显示八思巴在元朝支持下取得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共同领袖的地位,显示元朝的经济实力,吸引各派僧人拥戴八思巴和元朝皇帝。真金皇太子到达萨迦寺后,立即出资用金汁书写佛经,1278年10月,八思巴还为这部佛经的写成题写了赞语。在八思巴的重视下,加上元朝提供的经济支持,元代的萨迦寺成为规模宏大的藏书中心。据记载,萨迦寺的许多殿堂都有“经墙”,即靠墙的存放经书的橱架,藏书很多。萨迦北寺大经堂的经墙藏书3000多函,乌则宁玛殿的经墙藏书2500余函,北寺上师寝宫还专门设有藏书室,藏有天文、历算、医药、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藏文书籍3000多函。现在保存完好的萨迦南寺大殿的经墙,藏书达两万多函。
八思巴在回到萨迦后所做的另外一件大事是确定萨迦教主和昆氏家族的继承人。本来八思巴回到萨迦时也只有四十几岁,还没有太大的必要确定一个继承人。但是在八思巴的兄弟中,与他同母所生而且关系最密切的恰那多吉已于1267年去世,只留下一个遗腹子达玛巴拉。他的异母弟仁钦坚赞在朝廷任帝师,没有成家,另外一个异母弟意希迥乃,当了云南王忽哥赤的上师,1271年忽哥赤被部下毒死,意希迥乃也于1273年或1274年逝于云南(一说逝于朵甘思)。意希迥乃娶妻生有一子,名叫达尼钦波桑波贝。这样,八思巴的下一代中就只有达玛巴拉和达尼钦波桑波贝两个男性成员。达尼钦波桑波贝生于1262年,达玛巴拉生于1268年正月,达玛巴拉要年幼6岁。按照萨迦昆氏家族的继承习惯,达尼钦波桑波贝和达玛巴拉一个出家继承萨迦教主,一个娶妻生子继承昆氏家族,不会出现什么矛盾。但是问题就出在这本来不成问题的地方,意希迥乃的母亲多吉丹本来是八思巴的父亲桑察·索南坚赞的第三个妻子拉久则玛的侍女,后来成为桑察·索南坚赞的第五个妻子,从母亲方面的地位来说,意希迥乃在八思巴兄弟中就要低一些,到了达尼钦波桑波贝和达玛巴拉这一辈,两人的悬殊就更大。对于八思巴来说,当然是恰那多吉之子达玛巴拉更亲密一些,对于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皇室来说,恰那多吉是白兰王,娶过蒙古公主,因此达玛巴拉与他们的关系更亲一些,达玛巴拉的母亲是夏鲁万户之女,因此夏鲁万户也希望达玛巴拉继承萨迦的权力。从希望达玛巴拉牢固地掌握萨迦派和昆氏家族的继承权,进一步就会发展到将达尼钦波桑波贝排斥出继承者的行列。因为萨迦派在忽必烈的扶植下取得了空前的权势,达尼钦波桑波贝无论取得教派或家族的哪一项继承权,就有可能受封为帝师或白兰王,成为与达玛巴拉权势相等的人物,他又比达玛巴拉年长6岁,脾气暴躁,在萨迦派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支持,会较快形成与达玛巴拉竞争的势力。出于这样的考虑,自然就有人提出了当八思巴正在壮年时即决定由达玛巴拉继承萨迦派教主和昆氏家族,从而在事实上剥夺达尼钦波桑波贝的继承权的主意。
这次八思巴在萨迦期间,还发生了著名的贡噶桑布之乱。首任萨迦本钦释迦桑布在1268年萨迦南寺动工修建后不久就去世了,此时八思巴正在赴京途中,即举荐原来担任萨迦朗钦的贡噶桑布继任本钦。贡噶桑布是从赴京途中返回萨迦就任,还是本来就留在萨迦,也不清楚。《汉藏史集》说:“他一共任本钦六年,在这期间,建成了萨迦大殿的底层、顶层、外围墙和内围墙,建了黄金制成的屋脊宝瓶,还建了纪念萨迦班智达的观音菩萨镀金像,并完成了大殿回廊的绘画。他还管理修建仁钦岗拉章、大屋顶北殿、拉康拉章的事务。贡噶桑布卸去本钦职务后,在甲若仓住了六年。”贡噶桑布任本钦时,或者因为八思巴远在大都、临洮,通信困难,或者因为八思巴听到有关贡噶桑布办事独断的报告,八思巴和贡噶桑布产生意见分歧。《汉藏史集》说,当八思巴住在临洮,萨迦派大众委派萨迦班智达的大弟子夏尔巴·意希迥乃的孙子意希仁钦(后来当过帝师,《元史》作亦摄思邻真)到临洮去迎请八思巴回萨迦,大约即有向八思巴禀报萨迦派内部情况之意。因此八思巴从临洮动身时,即已免去贡噶桑布的本钦职务,由八思巴荐举尚尊、秀波岗噶哇相继担任萨迦本钦。八思巴1276年底回到萨迦时,贡噶桑布早已退居甲若仓,但是他在萨迦派中的影响仍然不小,贡噶桑布又因自己尽力效劳却被免职而愤愤不平,可能在言语行动上有顶撞八思巴的现象。萨迦派的这种内部冲突,被护送八思巴回萨迦的真金皇太子察觉,真金返回大都后,立即向忽必烈奏报,于是忽必烈派遣总制院使桑哥领兵前来查处,镇压贡噶桑布。
1280年,当贡噶桑布之乱已经平定,八思巴在萨迦派内部以及藏族地区的领袖地位空前巩固之时,他却于当年11月22日在萨迦南寺的拉康拉章盛年谢世,享年四十有六。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