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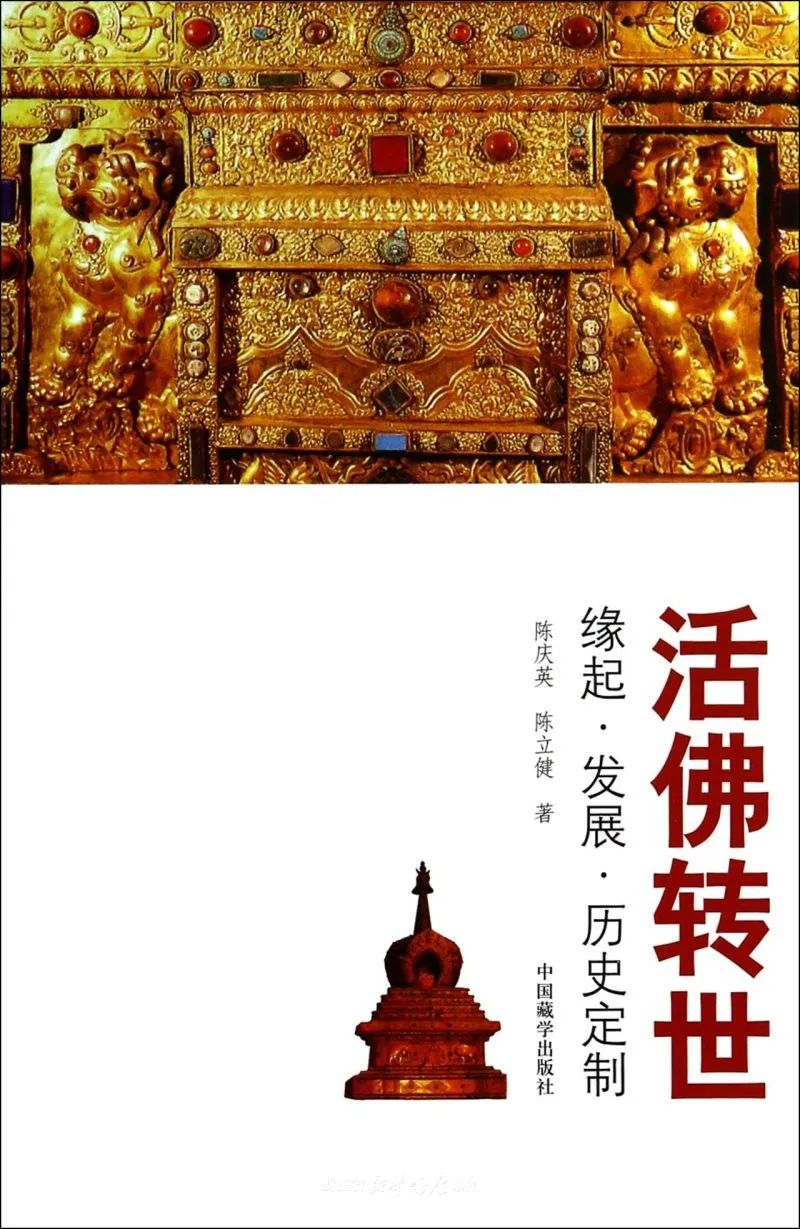
第三节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的发展
据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1542年藏历三月根敦嘉措圆寂后,格鲁派中立即有许多人议论他的转世问题,并请求一些高僧占卜和护法神降预言。1542年藏历十一月索南嘉措在堆龙德庆县的康萨贡地方出生,其父是当地一个小贵族。他出生后,先是在他的家庭和当地的一些僧俗人士中传出关于他的种种灵异事迹的传说,值得注意的是,《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的这些灵异事迹,父母和一些高僧的梦境占有很大的分量,这与前面提到的噶玛噶举派的活佛转世时的情形差不多,在后来的历辈达赖喇嘛转世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形式。康萨贡的这些传说很快就引起哲蚌寺法台班钦索南扎巴和一些地方首领的重视。1545年,班钦索南扎巴在觉莫隆寺举行的一次法会上首先见了三岁的索南嘉措,以观察他是否“灵异”。据说当索南扎巴拿出一幅根敦嘉措送给他的怙主像问小孩是否认识时,小孩说这像还是我给你的,这使得索南扎巴认为这个小孩就是根敦嘉措的转世。接着哲蚌寺又派根敦嘉措的侍从仲乃仁波且带领几个随从到康萨贡去专门察看,并让灵童辨认根敦嘉措在世时随身携带的度母像和念珠等。通过这些考察,班钦索南扎巴和仲乃仁波且等人都认为这个灵童就是根敦嘉措的转世。而且哲蚌寺的乃琼护法降神师也发表了一些认定转世灵童的意见。由仲乃仁波且与哲蚌寺的堪布等商议后,经过请示帕竹政权的首领,取得帕竹第悉(明朝所封的阐化王)的同意,于1547年3月将灵童迎请到哲蚌寺。索南嘉措到哲蚌寺时,全寺僧众出寺列队欢迎,在根敦嘉措的住所甘丹颇章设立两个座位,由索南扎巴法台和索南嘉措并坐,帕竹政权首领和全寺僧众、施主向灵童献了礼品。灵童以索南扎巴为师受了居士戒,起名索南嘉措。这是达赖喇嘛活佛转世中第一次出现查访、认定、坐床等程序。而且哲蚌寺的乃琼护法降神师也第一次参与了寻访和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事务。不过这些都是由哲蚌寺自己进行的,而且是由哲蚌寺的住持班钦索南扎巴主持的,主要是依据他和哲蚌寺的僧众的意见,虽然有请示帕竹政权首领的过程,而且帕竹政权的首领还出席索南嘉措的坐床仪式并做了指示,但是并无帕竹政权首领正式批准转世灵童的说法。所以,可以说对三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坐床等,与当时噶玛噶举派决定其活佛的转世并没有大的区别。索南嘉措当时继承的是哲蚌寺高僧根敦嘉措的法座,所以这时的索南嘉措只是被称为是哲蚌寺活佛根敦嘉措的转世。
1552年,年仅十岁的索南嘉措在班钦索南扎巴的操持下担任哲蚌寺住持,并在1553年主持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在这里,班钦索南扎巴实际上开了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的几个先例:一是由上一世达赖喇嘛担任哲蚌寺住持的弟子主持转世事宜,并且为转世灵童授戒,负责对新的转世活佛的培养教育;二是认定转世时请示西藏地方政权首领;三是将哲蚌寺住持的职务尽快交给新的达赖喇嘛;四是扶持索南嘉措在十一岁时就主持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这几项措施都反映了当时格鲁派上层急于把索南嘉措树立为格鲁派教派领袖的迫切愿望。索南嘉措之后,除了在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一段时间因为第悉藏巴政权禁止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而由四世班禅担任过哲蚌寺的住持外,哲蚌寺的住持只能由达赖喇嘛担任,其他人不能担任此职务,后来色拉寺的住持职务也照此办理。这样将哲蚌寺和色拉寺的住持职务固定在历辈达赖喇嘛身上,这显然是为了强化历辈达赖喇嘛格鲁派领袖的地位。由于班钦索南扎巴对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的这些功绩,加上他担任过第十五任甘丹赤巴和哲蚌寺、色拉寺住持,所以在他圆寂后格鲁派也为他寻访转世灵童,在哲蚌寺里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森康贡的活佛转世系统。这种酬报在活佛转世过程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高僧的形式,推动了格鲁派的许多高僧为自己的上师寻访、认定转世灵童的积极性,促进了格鲁派众多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同时也说明格鲁派的活佛转世从一开始就具有数量逐步增多且发散的趋势。
格鲁派的高僧们努力抬高索南嘉措的格鲁派领袖地位,在教派内部树立他的权威,以此加强格鲁派的团结,起到了稳固格鲁派的作用。此外,从1557年开始的十几年中,发生了第悉藏巴家族兴起并打败仁蚌巴的事件,使格鲁派的外部环境得到一个缓冲阶段。索南嘉措利用这一时机,周游前后藏各地,和各个地方的僧俗首领建立关系,扩大格鲁派的影响。后来索南嘉措甚至把格鲁派教法传播到蒙古族之中。
1576年,率部众移牧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派人到拉萨邀请索南嘉措到青海相见,是格鲁派和索南嘉措地位发生转变的一大契机,索南嘉措及时抓住了这一机遇,不顾格鲁派内部一些人的反对,毅然接受邀请。1577年他从拉萨动身去青海,1578年夏天在青海湖边一个叫做察卜齐雅勒的地方与俺答汗举行会见,使俺答汗等蒙古首领信奉了格鲁派。俺答汗还专门赠给他一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圣”,是超凡入圣,即超出尘世间之意;“识一切”,是藏传佛教对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称;“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译成藏语是rdo-rje-vchang(多吉绛),译成汉语是执金刚,这是藏传佛教对于在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称。“识一切”和“瓦齐尔达喇”结合起来,是说索南嘉措在显宗、密宗方面都取得了最高成就。“达赖”,蒙古语是大海之意;“喇嘛”,藏语是上师之意。可能是俺答汗询问过索南嘉措名字的含意,当他知道“索南嘉措”的意思为“福德大海”之后,于是在给索南嘉措的尊号中加上了“达赖”两个字,以与藏语的“嘉措”相对应。由此,格鲁派的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得到了“达赖喇嘛”这一特别的蒙古语与藏语相结合的称号,成为得到蒙古各部首领信奉的活佛。索南嘉措得到达赖喇嘛的尊号后,因为他是作为根敦嘉措的转世而成为格鲁派的领袖的,而根敦嘉措又是作为根敦珠巴的转世而在格鲁派中建立起他的地位的,所以格鲁派寺院集团的上层僧侣自然地将索南嘉措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第二世是根敦嘉措,第一世是宗喀巴晚年所教诲过的弟子、扎什伦布寺的建立者根敦珠巴。过去有人说,是由宗喀巴的两个弟子传出达赖喇嘛、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达赖喇嘛的名号出现在宗喀巴大师圆寂一百六十年之后,班禅大师的名号出现得更晚。是在出现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后,为了与宗喀巴大师建立上关系,往前追认宗喀巴弟子辈的人作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第一世班禅大师的。
俺答汗曾经与明廷长期对立,但是在他到青海以前已经与明廷和好,得到了明廷给他的“顺义王”的封号,索南嘉措还通过与蒙古俺答汗的关系,与明朝建立了联系,应邀到甘州与明朝的地方官员会见。据记载,索南嘉措在甘州时还通过甘州的都堂给明朝当时的首相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请求明朝准许他向朝廷进贡,也就是请明廷承认他的格鲁派教派领袖的地位。由于索南嘉措按明廷的要求,劝说俺答汗从青海返回土默特,所以得到明廷给他的“朵儿只唱”的封号。明廷还应他的请求,准许他以西藏宗教首领的身份定期向明廷进贡。索南嘉措在会见俺答汗以后,在安多和康区活动,新建和扩建理塘寺、塔尔寺等格鲁派寺院,扩大格鲁派在康区和安多的势力,他还利用到呼和浩特去参加俺答汗超度法事的机会,沿途传法建寺,在呼和浩特兴建格鲁派寺院,剃度蒙古族僧人,将格鲁派传播到蒙古察哈尔、喀尔喀等部。三世达赖喇嘛带到蒙古去的弟子随从中,有一个担任色拉寺住持的东科尔·云丹嘉措,他和他的转世后来成为在蒙古活动的一个著名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还通过将一些蒙古王公贵族子弟认定为本派高僧的建立活佛转世系统的办法,在蒙古各部建立起许多活佛转世系统,以此取得蒙古各部军事力量的全力支持,巩固和提高了格鲁派和达赖喇嘛的地位,尤其是使达赖喇嘛在格鲁派中的领袖地位空前巩固。索南嘉措的这些活动,使得格鲁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后来格鲁派取得西藏的地方政权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以后的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务加入了新的政治因素。
1588年3月,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应明廷之邀到北京的途中,在内蒙古圆寂。在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圆寂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589年,俺答汗的一个孙子苏密尔台吉的夫人(系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尔十六世孙诺诺和·卫征诺颜之女,名拜罕·珠拉)生育了一个儿子。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由于当时当地的特别的历史背景,很快就成为关系到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一件大事。1589年1月,苏密尔台吉的妻子生了儿子后,立即在土默特部贵族和三世达赖喇嘛的随从中传出这个孩子是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说法,当年10月,三世达赖喇嘛的索本楚臣嘉措(gsol-dpon-tshul-khrims-rgya-mtsho)等写信给在拉萨的格鲁派人士,报告了这个孩子出生及灵异情形。当时拉萨的格鲁派的领导集团已经着手寻找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并进行到正在考察在止贡地方出生的一个儿童是否是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的阶段,在收到内蒙古方面的报告后,就放弃了在止贡地方的寻访。格鲁派派出以三世达赖喇嘛的襄佐贝丹嘉措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内蒙古考察,代表团中有帕竹政权的首领和拉萨地方贵族的代表和拉萨三大寺的代表,代表团出发时卸任甘丹赤巴班觉嘉措给孩子起名为云丹嘉措(yon-tan-rgya-mtsho),可见拉萨方面事实上已经确定在内蒙古出生的灵童为四世达赖喇嘛。拉萨的代表团到达内蒙古时,灵童已经被迎请到呼和浩特,受到僧俗人众的供奉。所以拉萨方面的代表团变成了迎请转世灵童从内蒙古进藏的代表团。据五世达赖喇嘛的《四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在得到灵童将动身进藏的消息后,帕木竹巴政权的首领在1603年写了祝福和叮嘱转世灵童努力学习的偈颂,代表了西藏地方政权(尽管当时帕竹政权早已岌岌可危)对四世达赖喇嘛的承认。作为西藏的格鲁派的最权威的宗教首领的达赖喇嘛,转世转到了蒙古族的王公之家,这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格鲁派作出的一个重要选择,同时也是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五世达赖喇嘛对此所作的一大段解释,说明了当时的格鲁派领袖们对于活佛转世与政治需要的关系的认识:“众生怙主夏仲仁波且(指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法王八思巴心绪相通,而俺答汗乃是忽必烈汗的转生,由于福田施主在当时大发善愿之法力,作为使佛法在蒙古地方传播开来的缘起,又因誓愿之力,使达赖喇嘛转生于成吉思汗的王族中,掌握政教相结合的权力,成为引导有缘众生走上大乘善道的吉祥怙主,这正是达赖喇嘛的不可改易的金刚遗言。正如《噶当书》中所说:“在以王者为模范的西藏,王者维持着藏地的安定。”像雪域西藏这样的地方,最初也难以仅用佛法进行教化,必须依靠政治的方法,这在蒙古也是同样,因此达赖喇嘛会在蒙古王族中降生。早在前辈达赖喇嘛时期,蒙古人对宗喀巴大师的教法便产生了虔诚的信仰,在与佛法结下善缘的基础上,他们说过后一世达赖喇嘛将在我们蒙古人中诞生的话。他们对于世间的政治感到淡漠,而对佛法则愈加崇信。这与《遍知一切白玛噶波传》中所记载的主巴活佛嘉旺曲杰为其主巴教派着想,转生到甲玛万户的万户长家庭中的情形虽然是一样的,但是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主巴白玛噶波护持利他徒众的发心则有大小的不同,索南嘉措是为了东起大海之滨的所有广大蒙古疆域中黄帽派政教遍布盛行,白玛噶波只是为了在涅、甲玛区区一小片地方流行主巴教法,这正如苍天与手掌之殊别!另外,在达赖喇嘛的遗嘱中还说道:“天命之人生喜乐,声誉远播功德具,增盛犹如上弦月。”这里的天命之人一词即指成吉思汗的后裔王族,达赖喇嘛转生在该王族中,将使彼方有情众生皆大欢喜。“功德”指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名字前面的两字。“增盛,一词犹如言如大海汇纳百川而增溢(后两句遗言中隐有转世灵童的名字‘功德海’,即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1603年四世达赖喇嘛到达拉萨,受到拉萨僧俗人众的欢迎,在哲蚌寺登上了三世达赖喇嘛的法座,在大昭寺由卸任甘丹赤巴桑结仁钦和甘丹赤巴根敦坚赞为他剃度,并授沙弥戒,由他们给四世达赖喇嘛讲授经典。由于格鲁派内部存在的一些个人矛盾,不久桑结仁钦辞去为达赖喇嘛讲经的职务,根敦坚赞以自己年龄大为由不愿接任,当时由他提议,请来当时任扎什伦布寺法台的洛桑却吉坚赞(1570-1662年,即四世班禅)担任云丹嘉措的讲经师傅。这是班禅大师给达赖喇嘛当师傅的第一例。这一件看来很普通的为达赖喇嘛选择老师的事情,后来却发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以洛桑却吉坚赞担任四世达赖喇嘛的老师为契机,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由此走上西藏历史的中心舞台,并逐步成为格鲁派中另一个重要的活佛系统。
1604年,云丹嘉措和洛桑却吉坚赞等一起去曲科杰寺朝礼。1614年12月,四世达赖喇嘛以班禅洛桑却吉坚赞为师在哲蚌寺受了比丘戒。受比丘戒是佛教僧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洛桑却吉坚赞给云丹嘉措授比丘戒是班禅和达赖喇嘛两大活佛系统之间互相授比丘戒的第一次,以后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之间互相授戒的情况多次发生,成为他们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和格鲁派高僧们的教育下,云丹嘉措很快就适应了自己达赖喇嘛的生活。作为达赖喇嘛,他在1604年主持了拉萨的祈愿大法会,并给格鲁派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云丹嘉措到西藏时,带来了一些蒙古武装力量,对处境困难的格鲁派是一种重要的帮助和支持。尽管当时取代了仁蚌巴家族地位的第悉藏巴支持噶玛噶举派,对格鲁派的压制和仇视更甚于仁蚌巴,但是由于有了云丹嘉措背后的蒙古武装力量的支撑,云丹嘉措作为格鲁派的领袖使得敌对的第悉藏巴政权不敢轻易对格鲁派摧残打击,格鲁派在各方面力量的高压下仍然保持了稳定和发展的势头,但是这同时也深化了格鲁派和噶玛噶举派之间的宗教矛盾。
1616年,明朝万历皇帝派专人进藏,赐予四世达赖喇嘛“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和印信,《四世达赖喇嘛传》记载说:“火龙年(1616)三月,明朝万历皇帝派来了以喇嘛索南罗追为首的许多汉人,赐予达赖喇嘛‘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印信和僧官制服。他们将达赖喇嘛迎请到哲蚌寺的甲吉康(汉人公所)里,向达赖喇嘛奉献了礼物,演出了很多奇特精彩的娱乐节目,转达了明朝皇帝邀请他去汉地的旨意。达赖喇嘛为缔结善缘,接受了邀请。”虽然这是汉藏文献中唯一的记载,但是可以看作是明朝对三世达赖喇嘛优待政策的继续,是完全可能的。云丹嘉措接受了邀请,但是在他真正准备动身之前,于1616年12月在哲蚌寺突然圆寂,时年二十八岁。有人说四世达赖喇嘛是被藏巴汗彭措南杰派人害死的。因为藏巴汗彭措南杰得了重病,据说是四世达赖喇嘛对他进行了诅咒所致,这事被藏巴汗彭措南杰察觉,于是派人将四世达赖喇嘛害死。这只是一种传说,藏巴汗害死四世达赖喇嘛是可能的,但不一定是因为四世达赖喇嘛“诅咒”了他,主要原因还是封建领主之间以及噶玛噶举派和格鲁派之间的政治权力和宗教地位的斗争。这也说明早在四世达赖喇嘛时期,达赖喇嘛即已成为西藏政治斗争中各方都关注的焦点人物,达赖喇嘛的生死存废已经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选编自陈庆英陈立健著《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