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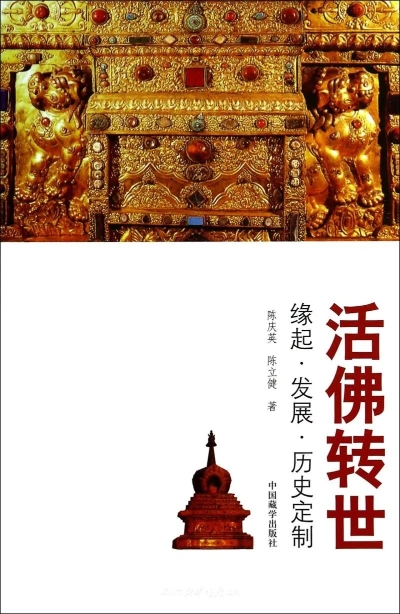
前言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一种宗教领袖的传承方式,从13世纪在西藏出现后,在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在藏族社会僧俗各界的推动下,有许多时候是在西藏地方政权甚至中央皇朝的参与推动下,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为活佛转世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同时,活佛转世本身对藏族社会和蒙古族社会(以及程度不同地对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民族,还有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不丹等国)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近代以来,藏族地区的苯教也仿效藏传佛教的办法,出现了转世活佛。某些时候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产生的影响,会波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在清朝达到高峰,并且在不同的范围里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班禅转世,成为新中国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一个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反观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不仅在世界上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中没有这种传承方式,就是在世界各地的佛教的不同流派中,即使是与藏传佛教同属于大乘佛教而且历史上有过不同程度的宗教交往的汉传佛教,以及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中,都没有发展出这种宗教领袖的传承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在藏传佛教内部,活佛转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藏传佛教已经有了近五百年的历史以后才出现的。在活佛转世制度出现以后,藏传佛教内部各个教派对这一宗教领袖的传承制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就是在同一个教派的内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活佛转世制度施行的广泛程度和社会的认同程度也有所不同。而且藏族世俗社会和中央王朝以及蒙古各部的首领在不同的时期对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也施加过不同的影响。因此,活佛转世制度不仅涉及藏传佛教的各个方面,同时也牵涉到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这些关系在许多时候是相互交叉作用的,往往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就形成讨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的复杂性。
产生活佛转世制度的社会基础之关于“活佛”的认识
我们对“活佛”的本质的认识:“是僧非佛,僭神袭职”、“对佛菩萨的比拟加上宗教社会地位的继承”、“具有特殊身份的藏传佛教僧人”。
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817页对“活佛”一词的解释是:“活佛,藏传佛教名词,藏语称为‘朱古’,意为神佛化现为肉身。后被用于大喇嘛继承制度,通称大喇嘛死后根据转世制度取得寺庙首领地位的继承人,参见‘转世’。”同书633页对“转世”的解释为:“转世,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而设立的一种制度。取佛教灵魂转世、生死轮回之说。始于13世纪的噶举派噶玛噶举的噶玛拔希。格鲁派兴起后,严禁僧人娶妻,亦采用转世制度解决宗教领袖的继承问题,始于达赖三世索南嘉措。通称转世者为‘活佛’,凡活佛死后,寺院上层通过占卜、降神等仪式,寻觅在活佛圆寂的同时出生的若干婴童,从中选定一个‘灵童’作为他的转世,迎入寺中继承其宗教地位。因人选常被上层集团操纵,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规定用‘金瓶掣签’法选定在理藩院注册的大活佛的转世,以防舞弊。其他中小寺庙稍有声望的喇嘛,则可自行寻觅‘灵童’,作为转世,遂出现众多的大小活佛。”这些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宗教学界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基本认识,其主要内容,至今仍然反映我国学术界讨论这方面问题时所具有的基本认识和出发点。
正如《宗教词典》所指出的,“活佛”在藏语中称为“朱古”(sprul-sku)或者“朱贝古”(sprul-pavi-sku),意思是“化现的佛身”,或者是意为神佛化现为肉身。藏文的sprul和sprul-pa是一个古词,在吐蕃王朝的碑文和文书中经常出现,特别是在提到吐蕃王朝的君主—赞普时,常用“sprul-gyi-lha-btsan-po”(圣神赞普)来称呼,sprul有时用来指赞普家族的祖先是从天神下降到人世间的这一神话传说,有时又被用来表示神幻、神变之意。在“朱古”或者“朱贝古”中,sprul应该是梵文动词nirmana(创作、应化)在藏文中的对译,而sprul-sku则是梵文名词nirmanakaya(化乐天)在藏文中的对译,意思是“变化”、“幻化”、“化身”或者“自在转生者”、“乘愿再来者”。“化身”即是大乘佛教所说的佛的三身,即“法身、报身、应身”之一的应身。藏文sprul-sku强调的是“化现”和“身”的结合,而且“身”是一代一代连续在人世间出现的,所以在藏文中又把这种世代化现的转世称为“sku-skyes”,意思是“再生的”,或者称为“yang-srid”,意思是“再次存在的”、“再来的”,这就与活佛一再转世的特点更加符合。在藏文中关于“转世”或“化身”的意思至少有十几种表述的词语。经过元、明、清三朝的使用和选择,逐渐以“朱贝古”一词最为常用,通常又将“朱贝古”简称为“朱古”。不过,通常“朱古”一词只在文章典籍中或者正式的场合中为了准确说明转世活佛的活佛身份时使用,平时人们在口语中对活佛使用“仁波且”作为尊称,“仁波且”(ren-bo-che)本意为“宝贵的”、“珍贵的”、“大宝”之意,这个藏语词语从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开始出现,开初是对高僧大德以及有地位世俗尊贵人物的一种尊称,后来在社会上约定俗成地只用来作为对具有转世活佛身份的僧人的尊称。除了用“仁波且”这一广泛的尊称外,对于一些掌管一个教派、一片地区或者一个著名的大寺院的活佛,还有一些专门的尊称。例如在格鲁派中对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最高等级的活佛常用“唐杰钦巴”(thams-cad-mkhyen-pa,意即“遍知一切”)、“兖色钦波”(kun-gzigs-chem-po,意为“遍见一切”)等本来对佛的称呼。“唐杰钦巴”、“兖色钦波”原来在一些教派中也用来指一些学识渊博的高僧大德,例如元代后期夏鲁寺的住持布顿大师就有“唐杰钦巴布顿仁波且”的称号。在格鲁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后,“唐杰钦巴”一般就只用来称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另外对历代达赖喇嘛则有一个专称“杰瓦仁波且”(rgyal-ba-rin-po-che,意即“佛宝”)。
对于一个活佛转世系统,通常都有一个专门的佛号,人们在相互交谈时提到某位活佛时,称他的佛号再加上“仁波且”,人们就知道指哪一位活佛。例如,人们在交谈中说到“热振仁波且”,就是指现在的热振活佛,如果说到“热振仁波且第三世”,就是指第三世热振活佛。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有时在活佛佛号的后面加上“仓”(tchang)来称呼活佛,“仓”是藏语“家”的意思,因为一个活佛在寺院中往往有自己单独的住所,被称为“拉章”(意思是上师、大德的住所),并有一些随从人员与他居住在一起,类似在寺院中的一个单独的家,所以称为“仓”。例如提到热振活佛,也可以称为“热振仓”。藏文中还用“zhags-drung”(汉文音译为夏茸或者夏仲、沙布隆等)来称呼中小活佛,例如上个世纪青海的著名藏族学者才旦夏茸,是青海民和县才旦寺的活佛,所以被称为才旦夏茸。“zhags-drung”意为足下,本来是对高僧大德的尊称,犹如对官员贵族尊称阁下,后来就在前面加上寺院名或者扎仓名,用来指该寺院和扎仓的活佛。此外,在一些地方还有对活佛的特别的称呼,例如在安多和康区一些地方,还把活佛称为“阿勒黑”('a-lags),在提到某位活佛时则在“阿勒黑”的后面加上佛号,就可以知道是指哪一位活佛。关于这一称呼的来历,没有见到明确的解释,我们推测“阿勒黑”来源于在尊贵的人物讲话时表示赞同、恭敬和接受的应答语“阿勒黑索”,大概是因为在活佛讲话时,弟子信徒常常以口称“阿勒黑索”('a-lags-so)来表示敬意和赞同,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对活佛的专门称呼。在云南藏族地区,还习惯用“guru”,即梵文的“尊师”来称呼活佛。
转世活佛的佛号往往是依据该活佛转世系统的第一世所建的寺院、出生的地方、居住的寺院或者是管辖的地区,甚至是第一世活佛的名字而起的,如热振活佛、第穆活佛、章嘉活佛、土观活佛、贡塘活佛、帕巴拉活佛、俄·勒贝喜饶活佛、俄·洛丹喜饶活佛等;有的是依据所属的教派而起的,如噶玛巴活佛、达隆活佛、主巴活佛、止贡活佛等;有的是用该活佛转世系统被认为是什么佛菩萨的转世来称呼的,如多吉帕姆活佛、嘉木样协巴活佛;有的则是依据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起的,如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的佛号来源于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赠给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尊号“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的佛号来源于固始汗赠给四世班禅的“班禅博克多”和清廷封给五世班禅的封号“班禅额尔德尼”等。实际上,关于活佛的佛号,还有一些与教派的历史和该活佛转世系统的历史有关的复杂的情形,如噶玛巴活佛,开始是噶玛噶举派的祖师都松钦巴、噶玛拔希、攘迥多吉一系被称为噶玛巴活佛,后来攘迥多吉的一个弟子扎巴僧格又传出一个活佛转世系统,也被称为噶玛巴活佛。为了区别,以噶玛拔希曾经得到元宪宗蒙哥汗赐给的一顶有黑边的僧帽,而称他们这一系为噶玛巴黑帽系活佛,而将扎巴僧格的一系称为噶玛巴红帽系活佛。俄·勒贝喜饶活佛和俄·洛丹喜饶活佛是昌都察雅县的两大活佛,以人名为佛号,据说是噶当派著名高僧俄·勒贝喜饶活佛和俄·洛丹喜饶活佛伯侄的转世,在康熙末年清军入藏时,因支援清军而受到清廷的册封,成为呼图克图,被称为察雅呼图克图,以察雅大呼图克图和察雅小呼图克图相区分,藏语称为察雅切仓活佛(察雅大呼图克图)和察雅穹仓活佛(察雅小呼图克图)。历史上,俄·勒贝喜饶(生卒年不详)是阿底峡的弟子,1073年在拉萨河南岸的桑浦地方建立桑浦寺,而俄·洛丹喜饶(1059-1109年)是他的侄子,幼年以俄·勒贝喜饶为师学习佛教,后来到克什米尔学习梵文和佛教,成为著名的译师,对桑浦寺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一个是桑浦寺的创建者,一个是发展桑浦寺的人,按理,俄·勒贝喜饶的转世应该是察雅切仓活佛,即大呼图克图,俄·洛丹喜饶的转世应该是察雅穹仓活佛,即小呼图克图。但是最初在察雅传播格鲁派教法的扎巴嘉措被认为是俄·洛丹喜饶的转世,而继承他事业的弟子桑结扎西被认为是俄·勒贝喜饶的转世,因此扎巴嘉措一系被称为察雅切仓活佛,而桑结扎西一系被称为察雅穹仓活佛。类似的一个寺院或者地区有两个地位差不多的活佛的情况,还有止贡寺的切仓活佛和穹仓活佛两个活佛转世系统。止贡噶举派在开初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采用活佛转世,直到止贡寺的第二十三任法座仁增却扎才开始实行活佛转世,仁增却扎的历辈转世被称为止贡穹仓活佛,而止贡寺第二十二任法座官却仁钦的转世官却赤列桑布开始的历辈转世被称为止贡切仓活佛。由于他们同时又是止贡噶举派的领袖,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止贡噶举的穹仓法王和切仓法王。
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播到蒙古地区以后,格鲁派的活佛转世也广泛传播到蒙古地区。在蒙古,对活佛的称呼有来源于藏文的“喇嘛”、“格根”(藏文 dge-rgan的音译,意为教师、老师)等,格根在藏文中只是对寺院中给青年僧人教经的低级僧职的称呼,但是在蒙古地区却用来作为对转世活佛的称呼。另一方面,一些蒙古语中与转世活佛有关的词语如“呼毕勒罕”、“呼图克图”、“诺门罕”、“扎萨克喇嘛”、“达喇嘛”等,又经过蒙古和硕特部统治藏族地区和清朝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的历程,传入藏族地区,为藏族地区的寺院和活佛、僧人所接受,并进入藏文词汇中。而且在蒙古地区出现了一些蒙古词语的活佛佛号,如内蒙古的乌兰活佛、青海地区的察罕诺门罕活佛(有时又用藏语称为夏茸尕布,意为白佛)、土默特扎赉特旗的内济托因活佛等。这就使得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的佛号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了解这些佛号的意义、熟悉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和传承的历史,并由此掌握各个活佛转世系统之间的关系,几乎成为一个有学识的活佛和藏传佛教高僧应该具备的专门知识。
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从一出现就与中原地区发生了联系。噶玛拔希和攘迥多吉、若必多吉等噶玛噶举最早的三辈活佛相继到元廷活动,元廷也了解他们之间的转世关系,但是由于当时元廷依靠的藏传佛教僧人主要是萨迦派款氏家族的高僧,因此三代噶玛巴的转世关系并没有受到皇帝的特别注意。例如元文宗图帖睦尔给攘迥多吉的迎请诏书:“依仗三宝护持的大福德,皇帝圣旨。赐攘迥多吉。因如来教法将由北方诸帝王弘传之授记之法力,(北方诸帝)对佛陀教法生起胜解。此后,薛禅皇帝(即忽必烈)依止和尊奉众多高僧大德,使佛陀之教法在此方弘扬,显明一切。朕亦愿对佛法善为护持服事,闻得你听闻多广、功德殊胜,故遣巩卜等人为金字使臣前来迎取你。如果你以其他借口推脱不来,岂不犯了使信仰者灰心失望的过失,沾染不愿离弃自己富足处所之恶臭习气,毁坏广利他人之善愿,造不为佛法着想的罪业,种下不顾有情众生苦痛之业障?又岂不会因为违背朕之法度大诏命,使朕心中不乐而使佛法受到损害?故此,望你为以朕为首的有情众生着想,而尽快前来!到此之后,佛法之事业都将照你的心愿完成。羊年春三月十三日在大都有的时分写来。”诏书中的语气与元朝帝王们招请各种宗教领袖人物的诏书完全一样,甚至有攘迥多吉如果不接受皇帝的邀请就会造成业障、违反皇帝的诏命等威胁性的语言。而且诏书中提到了忽必烈尊奉高僧大德的事情,但是丝毫没有提到攘迥多吉的前世噶玛拔希和元廷的关系,由此可见元文宗还没有特别重视攘迥多吉是噶玛拔希的转世的说法,而着重强调的是他本人“听闻多广、功德殊胜”。明朝初期到朝廷活动的三大法王中,噶玛巴·得银协巴是噶玛噶举派的转世活佛,但是萨迦派的大乘法王和格鲁派的大慈法王都没有转世活佛的身份。因此明廷封授三大法王时并没有像后来清廷封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那样当作转世活佛来封授,对他们的封授只是对其本人的,他们之后的法王职位的继承是用转世的办法还是师徒传承的办法,并不是一个特别看重的问题。
汉文中的“活佛”一词,产生于明代中后期。明代典籍有万历年间俺答汗往西海迎“活佛”的记载。《明史》列传二一九《西域三·乌斯藏大宝法王》记载:“(大宝法王)正德元年来贡。十年复来贡。时帝惑近习言,谓乌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考永、宣间陈诚、侯显入番故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刘允“·····越两月入其地。所谓活佛者,恐中国诱害之,匿不出见。将士怒,欲胁以威。番人夜袭之,夺宝货、器械以去。”又说:“嘉靖中,法王犹数入贡,迄神宗朝不绝。时有僧锁南坚错者,能知已往未来事,称活佛,顺义王俺答亦崇信之。万历七年,以迎活佛为名,西侵瓦刺,为所败。此僧戒以好杀,劝之东还。俺答亦劝此僧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牟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僧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这里的“僧锁南坚错者”即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可见明朝的文人在开始时对“活佛”的认识限定在知道前生后事和有特别能力的高僧,是在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见面以及允许三世达赖喇嘛入贡后,才对“活佛”的意思了解得清楚一些。对活佛转世的意义了解得更为详细的是《夷俗记》中的记载:“曩俺答在时,往西迎佛,得达赖喇嘛归,事之甚谨,达赖喇嘛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数年后有佛出焉。后达赖喇嘛卒,不一年,至万历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尝在腹中有声,众僧曰:“此当客生佛。比产时,儿果自言曰:“我前达赖喇嘛也。”众僧曰:“此果向者达赖喇嘛复生矣。”达赖生时乘马及经一册,顺义王西还,以此数者示儿,儿果曰:“此我之马也。”于诸物品中,独取念珠与经,曰:“此我故物也。”时时作西方语,惟僧能解之,甫三四岁,言祸福亦辄应,夷人闻之,千里赢粮而走谒之日众,号曰:“小活佛。”上其事以闻。万历二十年,奉圣旨升松木之子为朵尔只昌,异其事也。”这里讲的是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以及被认为是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的故事。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故事已经引起明廷的极大关注,并仔细记录了“活佛转世”中“小活佛”的灵异,及僧俗信徒对转世灵童的信仰等,记录了这个对汉族地区来说还是十分新奇的专门现象。
对于活佛转世,从古到今社会上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认识。信仰佛教的人士和不信仰佛教的人士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信仰佛教的人士内部,其实对活佛转世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把各种相关的观点综合起来,结合活佛转世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简要的说明应该是:活佛转世制度是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西藏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协调起来,在某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或者著名高僧去世之后,由其弟子和寺院通过一定的程序在各地新出生的儿童(在前一世首领去世以后出生的)中寻访、认定他的“转世”,然后接入寺院坐床,并且加以特别的培养教育,使其继承前一世的宗教首领的宗教地位及政治、经济权力。通过这样的继承和延续,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形成了许多活佛转世系统,也就在藏传佛教中形成了“活佛”这样一个具有特别身份的僧人群体。因此,作为一个转世的活佛,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具有他以前的历辈的转世的传承,而且这些转世得到该系统所在的寺院和藏传佛教界多数人的认可;第二,这一转世系统具有明确的活佛名号及其身份,并有延续这一转世系统的经济基础;第三,他本人出生后经过一定的宗教程式,得到寺院和信徒的认可,承袭前世名号、地位等;第四,拥有一些固定的信仰和供奉该活佛系统的信徒,也就是要有世俗的施主;第五,如果是地区和教派中的重要的活佛,则需要得到地方政权或者中央王朝的认可,特别是拥有参与政治权力的重要活佛,得到地方政权或者中央王朝的认可和封授更是一个必须的条件。当然,这些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主要的部分是一致的。总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转世活佛是藏传佛教中一群身份特殊的僧人,是信徒出于对上师的信仰而将其与佛、菩萨比拟,加上高级僧侣的宗教和社会地位继承的需要,因而一些僧人被寺院和信徒承认为前一世高僧的转世,而且这种承认往往还要经过相关的地方政权和中央王朝的认可。每一个转世活佛有自己所在的根本寺院,并拥有自己单独的住所和一些照管其生活、办理事务的侍从人员,有的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庄园和属民,他们或者是该寺的寺主,或者是该寺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具有担任本寺院或者本教派的高级僧职和完成重要宗教使命的备选的资格。他们在自己的寺院和信徒中被认为是佛菩萨的化现,享有崇高的宗教威望。在整个藏传佛教中,转世活佛和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而继承前辈高僧地位的宗教领袖人物是同样被承认的高级僧人,而且往往比后两种传承方式产生的宗教领袖更容易得到僧俗信徒的广泛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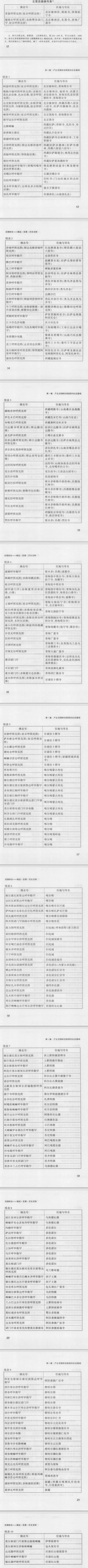
【选编自陈庆英 陈立健著《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