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辅仁(1930—1995),汉族,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族学家、藏学家。1948年入北平朝阳学院学习。1952年燕京大学民族学系毕业后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任教。1956年调至历史系。1961年后任历史系研究生导师。1976年在该院民族研究所任副教授、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民族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民族学科评审组组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藏学事业承上启下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追记王辅仁教授一生的藏学情怀
新一代从事藏学研究的年轻学子,大多会对王辅仁的名字感到陌生,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藏学家和民族学家。他的一生基本是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度过的,他把毕生精力、聪明才智以及积累了四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无私奉献给了中国民族教育事业和藏学事业。遗憾的是他仅活到65岁,还在成熟有为之年便离开了我们。他的早逝,是中国民族学、藏学事业的损失,也让我们这些多年相处在他身边的弟子们,深深地感到痛惜。
01
1930年12月,王辅仁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旧式家庭,父亲曾是冯玉祥将军属下的一名文职官员。抗战爆发后,他父亲离开军界,闭门守志。王辅仁从小即在父亲严格教育下,喜读文史书籍,知书达理。稍长,考入北平有名的四存中学。四存中学是所重视读古书的学校,在这里,他受到了更多文史知识的熏陶。1948年,他考进北平朝阳学院,不久,便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改为民族学系),跟随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学习社会学和民族学。好学的王辅仁此时并不满足系里开出的那几门课程,他还到历史系去辅修中国史,前后上过翦伯赞、翁独健、聂崇岐、侯仁之等先生的课。在当时燕大学生中,能同时获得民族学、历史学两个学科专业教育和训练的人并不多,王辅仁是其中的一个。这为他日后从事中国民族学和藏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02
1952年王辅仁从燕京大学毕业,正值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不复存在,林耀华先生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师、助教和学生十几人被分配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这时,民院研究部汇聚了一批研究中国古代民族文字、文献、史地、考古的专家学者,他们分属于新组建的西北、东北、中南、西藏几个研究室,其中西藏研究室由林耀华任主任,王辅仁归入这个研究室。在这里,他认识了李有义、王森、王静如、吴丰培、苏晋仁诸位先生。他们当中,有的研究藏族历史和文献,有的专门研究藏族的宗教和语言。在同这些老先生的接触交谈中,王辅仁第一次感受到了弘扬藏族历史文化的必要和特殊意义,从而引发他对西藏的关注和兴趣。此后,在这些先生的指导下,他开始检阅前人记述西藏的各种著作,注意收集有关西藏历史文化的资料。知识的不断积累,使他初步迈进了研究西藏的门槛。

王辅仁(左)与著名藏学家李有义(中)、藏语文专家胡坦(右)合影
1954年夏天,林耀华、李有义、宋蜀华几位先生从西藏归来,他们是中央文委最早派往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成员,在进藏部队和当地藏汉干部的协助下,他们在西藏各地对旧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寺院和贵族、平民生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全面考察,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回京以后,中央领导指示他们尽快将这些资料编撰成书,供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参考。林耀华感到事情紧迫重要,把他的亲传弟子王辅仁叫来参与撰写。经过5个人的紧张工作,《西藏社会概况》一书于1955年3月写成。与此同时,林耀华先生把他在西藏东部波密地区的考察资料也交由王辅仁整理,形成名为《波密简述》的调查报告。两部专著先后发表在研究部内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第二辑上,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介绍西藏经济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习俗的民族学著作。由于当时西藏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旧西藏地方政权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还依然保存着,两部著作所记录的内容,资料翔实新鲜,为过去所少见,故一经发表,就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对参与调查和编写人员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表彰。多年以后,当王辅仁先生跟我谈起此事时,仍兴奋地说:“那是林先生对我的栽培,给了我一次难得的写书机会,使我更坚定了研究西藏的勇气和信心。”
03
1956年,王辅仁迎来了进藏的机会。这年春天,由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研究人员参与了这项工作。王辅仁参加了西藏调查组,同李有义、王森先生一起进藏。这是他第一次去西藏做调查,心情格外兴奋。他用在燕京大学学过的社会学、民族学理论知识,把西藏当成一个社区进行观察体验,先是在拉萨、后又转到昌都,深入到最底层的百姓中去座谈访问,不管是亲眼观察到的事实,还是从政府文件中发现的材料,他都细心收集并加以整理。他告诉我,1956年这一年的进藏调查,收获是巨大的,不仅让他对旧西藏的现状有了深刻了解,亲眼看到了贵族们的奢靡和广大农奴的苦难,在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通过调查实践,得到了丰富真实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成了他的宝贵财富。当他从西藏回到北京后,感觉自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去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了。
1956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历史系,这是国家为培养新一代民族史、民族学的研究与教学人才新建的一个系。我是第一批考进这个系的学生。学校很重视历史系师资队伍的构成,聘请了一些校外的历史学专家到系任教,还有一部分老师是林耀华先生从燕京大学带过来的讲师、助教。系里为加强专业培训,特别为我们班增开了一门新课,叫做“中国民族志”。这门课没有现成教材,都是临时由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分别讲解他们熟悉的民族情况。其中的藏族部分由王辅仁承担,他是上课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才二十五六岁,刚被提升为讲师。第一次在课堂上见到王先生,看他满面笑容,浑身充满了朝气。他的讲课内容比别的老师丰富严谨,能把复杂的西藏社会状况和神秘的藏传佛教分析得鞭辟入里,明晰透彻,语言表达又流畅精炼、干脆利落。讲课中还不时穿插些他调查时的轶事见闻,让人听起来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对西藏高原充满了向往。同学们反映,听王先生的课一点都不枯燥,像是在剧场里听一段有趣的评书,不愿意下课。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王先生在上大学时,就是北京曲艺界有名的资深票友,他能字正腔圆熟练地吟唱几十段传统北京单弦,在口才训练和语言表达上早就下过多年功夫,难怪他的讲课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王辅仁的教学生涯就没有间断过。当时,历史系每个年级都要上藏族历史和宗教文化方面的课,校内其他系有相同的课程也由他来上。教学任务繁重,可他从不叫苦,总是热情而精力充沛地接受领导的安排。他常说:“我是个教书的,教好书、育好人是我的本分,只要每堂课下来对得起学生,我就心满意足了。”
1961年8月,我从历史系毕业留系工作。有一天,系副主任林耀华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藏族是个大民族,地位很重要,系里现在只有辅仁一个人搞藏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几头上课,他的教学任务很重,需要增加人手帮忙,系里研究决定,让你跟着他学,做他的助手,并希望你能早日学成登台上课,分担些他的负担”。我虽然对系里当时的安排表示服从,但我没去过西藏,没学过藏语,藏学知识知道的也很有限,心里一直慌慌的没有底。王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你来跟我学藏族史,我太高兴了!知之不多没关系,慢慢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有恒心,把学习方法找对,很快就会上路”。他说,藏族历史线索多,先要理清发展脉络,一以贯之;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看书要勤思索,做到真的理解,辨别真伪,不下苦功夫不行。我记住了王先生这些谆谆嘱咐,按照他布置安排的计划自学,先通读藏族历史和必读的原著参考书,认真做读书笔记,摘录相关史料做卡片,日子一长,日积月累,果然有了不小收获。
王先生盼着我能早日成材,除了让我跟班听他的课外,又想出另一个办法,叫我每周两个下午去他家给我单独授课。这单独授课与跟班听课有很大的不同,采取的是面对面近乎聊天的形式进行。那时,王先生家住在西直门内新街口小三条一个旧式四合院内,进门处有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门房,屋里墙壁四周用报纸糊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堆满了他备课用的参考书和书写的文稿,这就是他简陋的书斋。我每次去就在这书斋里,一边喝茶,一边听王先生谈笑风生地为我授课。授课内容广泛丰富,有他备课时使用的原始教案,其中包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各家评述、对史料记载的研判分析,有时插入大量的资料文献和他实地调查的见闻心得,有时还让我结合他的授课内容谈感受和收获。这种轻松自如无拘束的交流互动,使我获益良多,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师生感情,了解到他平时备课和读书的各种办法。
王先生对待学生一向宽厚大方,每次三四个小时的授课结束,天黑下来就留我吃饭。王先生的经济并不宽裕,夫人没有工作、膝下4个子女均未成年,靠他一个人的微薄工资,生活过得自然很清苦,但先生的夫人是个十分会理家的贤内助,一切家务支出她打理、安排得井井有条,不叫先生分心,而且会做一手好面食。凡去过王先生家的同事和学生,几乎都吃过她做的面条。她和王先生一样乐观豁达,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来访的同事和学生总是热情相待。此后十几年,我一直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夫妇视我为兄弟,几乎无话不谈,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也许是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入室弟子”,王先生在我身上倾注的情谊和心血,在他众多的弟子中恐怕是最多最浓的一个。他是我步入藏学研究领域的引路人和指导者,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
04
凡是接触过王辅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在同龄人中间是博学多才的一个。这是和他常年勤奋好学、持之以恒地博览群书分不开的。王先生常和我讲起老一辈专家学者不图名利、潜心治学的优良传统和求真务实的学风。20世纪50年代,在西藏调查的时候,他和王森先生、柳陞祺先生朝夕相处。他介绍说,这些老先生讲起西藏的历史、宗教就像是如数家珍,是把知识掰碎了、揉细了一点点地交给你去消化。他们旁征博引把每件小事都分析得透彻生动,是因为他们把书啃烂了、吃透了,所以得心应手。他接着说,读书怕的是不求甚解、浅尝辄止,没有大量丰富的知识积累,怎么敢去课堂上误人子弟。他经常比喻,课堂上如给学生一桶水的知识,你要准备八桶水的知识作后备,否则心里就没底,就不能理直气壮地面对学生。王先生这样讲,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不管白天上课工作再忙,也要挤出时间读书。他读书有自己的计划,主张书要通读,不能自认为需要哪儿就读哪儿,他多次翻阅二十四史,几遍通读《资治通鉴》,认真写研读笔记。文史类中许多杂史、别史、笔记小说,以及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音韵学等专门书籍他几乎都有所涉猎。他对地理方面的知识更是娴熟,每个省、市、县的历史更迭变化、有什么掌故他都了如指掌。他常说,民族学(包括藏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和许多学科都有交叉,只有求得知识面广,才能触类旁通。知识靠一步步积累,资料收集也是一样,只有做到眼勤手勤,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才会有“集腋成裘”的效果。
20世纪60年代初,不像今天许多藏文原典和资料都有翻译出版,那时许多孤本还是靠手抄流传。记得王先生手里就有不少手抄的敦煌卷子藏文文献译稿。他还下功夫把不易得来的30多万字的《土观宗派源流》汉译孤本和王森先生口授、尚未公开出版的《西藏佛教史资料十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作为教学科研之用。
王先生善用各种资料。他能博采众家之长来充实讲课内容,所以即使是讲授旧课,他也尽量想办法补充些新的内容。在编写讲稿过程中,他把容易遇到的问题和学生费解的问题一一标示研究清楚,查对资料加以解释,力争把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信息介绍给学生,使大家对课程常有新鲜感。王先生说,课堂讲课是门艺术,叫人听来必须饶有兴味。他最反对用艰涩冗长的语言,把事情描述得十分深奥难懂去吓唬学生。他主张讲话、写文章要尽量做到简明扼要,让所有人明白,能把纷繁复杂的事物,用最精炼形象的语言概括表达出来才最见功力。几十年的接触,他就是用他那训练有素的语言文字表达功力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要求我们。他说,今后不管是讲课还是写文章,你要切记课堂上不能念错别字,写文章写书不能文理不通。多少年来,我就是按照王先生的嘱托一步步走过来的。
1964年,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上级指令北京各高校师生要分批下乡搞“四清”,中央民族学院也没有例外,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办,历史系的教师和全校700名教职工一起被发往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王先生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时历史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反动学术权威”多,已被“砸烂”取消,教师们只好被安置在新建的研究室(即后来的民族研究所)工作。我和王先生一起被分到研究室西南民族组,继续承担全校各系藏族史课程的教学。
05
1978年年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校园,研究室老师们的精神面貌大有改观,工作热情十分高涨,纷纷在寻找研究课题来做,并翻译出了不少国外研究资料。王先生和我商量说:“咱们师徒二人不能光顾教书,也要花点时间把科研拣起来。”他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社会科学研究陷于停顿,市面上很少看到有社会科学类和民族方面的出版物,我们得尽早动手,把多年搞藏族史的科研成果拿出去。于是我们便利用课余时间开始整理和修订手上的讲稿,做写书的准备。就在这时,西藏人民出版社派人来北京找到王先生说,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要出版社出版一本揭露西藏封建农奴制度黑暗和反映西藏和平解放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书给群众看。现在西藏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叫他们到中央民族学院来寻找作者。王先生听后有些犹豫,担心承接写现实题材的书,写不好会遭到批判。经过几番推脱商量,最后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王先生为了锻炼我,决定他来写封建农奴制度的部分,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变化部分由我来完成。他说这样会大大节省时间,我们就可以很快交稿。接下来我们开始分头执笔,不到半年时间就写成了书稿。出版社给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西藏社会的飞跃》,一次印刷了2万册,送西藏各地书店发行,书很快告罄。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自然很受鼓舞。想不到,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写了这本为现实服务的小书,竟得到藏族群众的欢迎。欣慰之余,很快就听到圈内有人反映,说“飞跃”这本书是个应景作品,算不上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王先生听到后,叮嘱我:“不要管别人怎么议论,只要你自己认为行得正、做得对就坚持,现在我们就再写一本本行业务的书给他们看。”其实,写一本藏族历史的通俗读物,“文化大革命”前王先生就有这样的打算,这次受到激励,很快他就拟好了一个编写大纲,把藏族历史上经历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划分成几十个专题,基本涵盖了藏族历史的发展轮廓。他说:我们写这本书,是给那些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广大读者和学生看的,所以要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不搞考证,叙事不宜冗长。他叫我先把熟悉的藏族近现代史部分写好交给他看,然后一起讨论修改。就这样,在王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很快就把书稿全部写完。1981年,《藏族史要》一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藏学研究在全国各地刚刚起步,民族院校和普通中专正处在民族历史教材紧缺的情况下,《藏族史要》的出版,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该书连续再版了3次。1984年6月,中国历史学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根据全国专家会议评议,联合授予该书“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很快把它译成英文向国外发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藏族历史著作在国外发行最早的一部书,受到了国际藏学界的重视和欢迎。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藏学已成为一门受国内外关注的学科,各地高校都在相继成立研究机构,中央民族学院也在此前后,开设了古藏文进修班和硕士藏学研究班,吸引了一批基础好、有上进心的年轻学子前来深造,校方还特别成立专家指导组,专门为这批学生指导授课。王先生承担了这些班级藏族历史、西藏佛教史等课程的教学,和这批藏族学生展开了频繁的互动。

随着藏学研究事业在各地的勃兴,这时,校外来邀请王先生讲课的单位也多了起来。他先后应邀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化书院,以及四川大学、西藏民族学院等校讲授藏学课程。他开设的课程门类也在增多,除了讲藏族史、藏族民族志、藏传佛教史以外,又增添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蒙藏民族关系、西藏古代文化等专题研究。一时间,王辅仁成了中央民族学院老师中开课门类最多的一位。
06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是王辅仁先生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取得双丰收的年代。除了教学,他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同样得到了同行们的赞许。在完成讲课任务之余,1982年,他撰写了《西藏佛教史略》一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他又和陈庆英合作,完成了《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一书的编写,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他帮助张云侠完成了《康藏大事记》校注。在这期间,他还参与了《民族词典》《藏汉大辞典》《中国名胜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历史卷、宗教卷)等大型辞书中有关藏学词目的编写。在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他把多年在藏族史研究中形成的学术观点和理论认知融入其中,比如当时学术界经常争论“西藏是何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他明确提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并非自元代派官设制才归入中国版图,这就有力驳斥了那些别有用心的国内外分裂分子鼓吹的西藏自古就是“独立国”的谬说。再比如,如何来考察藏族形成的发展史,他坚定地说:“必须把它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既看到藏族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更要看到它的发展必然受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他的这些观点和认识,今天看来也许会感到浅显不值一提,可是放在藏族历史研究的初期,能大胆表达这些观点和指导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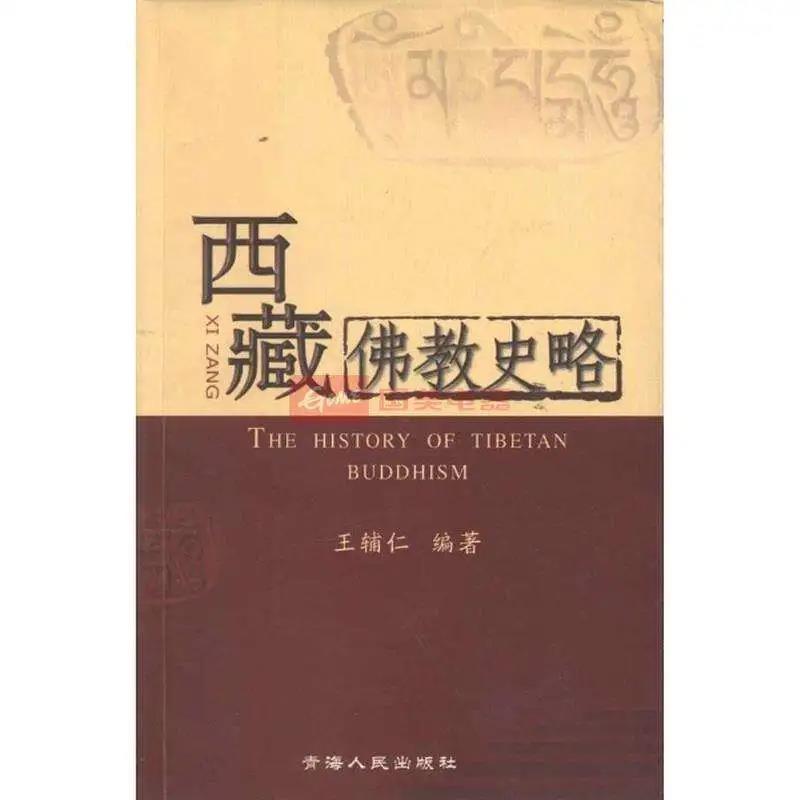
198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民族学系。这是老一辈民族学家和学校经过多年努力促成的一件大事,第一批招进来的二十多名学生全部是少数民族。校方十分重视民族学系的建设发展,选出最强的教师为该系学生上课。为了加强对这个重点学科的领导,1986年6月,院领导把原民族研究所和民族学系两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改组合并成一个,任命王辅仁为民族研究所所长和民族学系主任。这对王先生来说,是他教学生涯中的一次角色转换,让他有些始料不及。但王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奉公守律的学者,对领导的决定只能遵从,自觉挑起这份重担。虽说没有工作经验,可是他头脑冷静、自律精神强,工作中处处谨慎小心,有了困难和难解问题就找大家商量或找前辈师长求教,有了好事先礼让别人,对单位内持不同意见的群众都表现出善意宽容,不摆领导架子,谦和待人。在他任所长和系主任期间,民族研究所和民族学系形成了平静、和谐、宽松的气氛,有了自由读书和研究的环境,大家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教学和科学研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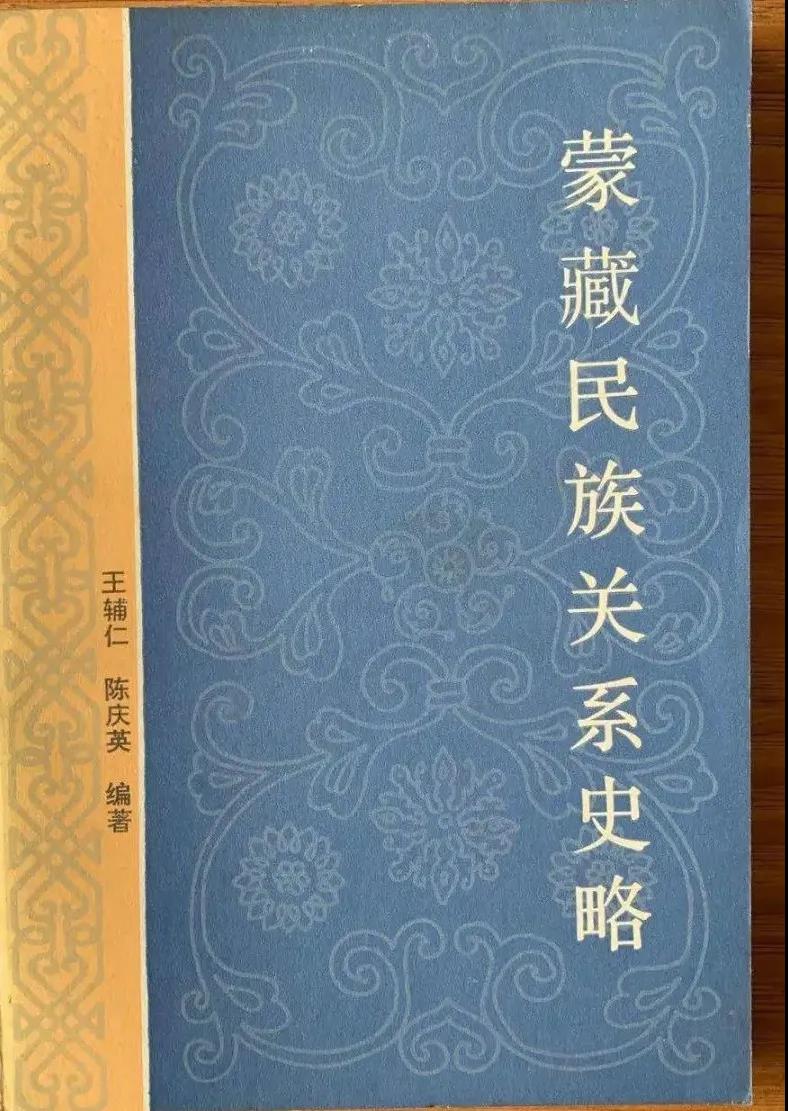
由于王辅仁先生多年在科研教学上的成就,他被学校推荐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开始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民族学科评审组组长。在校外,被聘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西藏佛教研究会、避暑山庄研究会理事,以及四川省藏族研究所学术委员、四川省藏族文化研究书院院务委员等职。这些不断加在他头上的职务光环,给淡泊名利的王先生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为了藏学事业,为了完成好领导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他必须付出更多的心力,身体和精力已不如从前。私下里,他不止一次向我倾诉:“现在身份变了,头上顶着这么多的帽子,已经没有多少我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这些年,很遗憾,我没写出什么东西,作品很少,可白头发却长了许多。”我很理解王老师的无奈心情和处境,只能奉劝他保重身体,工作中注意劳逸结合。1995年1月,他随团去台湾参加海峡两岸蒙学藏学学术讨论会,会间他突发胃出血被送医院抢救。病榻上医生叮嘱他说,你病情还是很严重,回去后一定休息静养,不能过度劳累,如病情再次复发,就很危险。王先生对医生的嘱托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心里想的仍是他的教学和对学生的培养。回京后一天都没有休息,继续上班。这些年,他对自己培养的藏学研究生有难以言说的特殊感情,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他从1961年起就开始带研究生,学位制度建立后,先后又培养了22位硕士和4位博士研究生。他对每届考进来的研究生都平等坦诚相待,尽心竭力启发和挖掘学生的潜能,创造各种条件提携他们。他常说:“学生中有许多好的见解和意见,搞科研教学不能以‘资格’论高下,应该教学相长,吸纳和发扬学生的长处,通过实际工作锻炼让他们早日成才。”为此,他提倡与学生共同写书,让学生和老师一起整理教案,帮助学生一起拟定论文写作大纲。每次学生赴涉藏地区实习,他都跟随下去在实践中耐心指导学生如何观察和体验事物,如何收集资料。他这种仁爱开明,以宽广胸怀无微不至的真诚帮助,给他带过的所有学生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随着王辅仁先生在藏学领域学术地位的不断提升,许多单位和高校都相继派人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王先生对前来求知进修藏学的同事,无论是在职教师,还是专业行政人员,一律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把自己多年积累掌握的藏学知识和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学到本领和知识满意而归。今天,活跃在国内藏学研究领域中年以上的学者,许多都聆听过他的课,在西北、西南各省区各类民族院校和研究机关都有他的得意门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辛勤园丁,是我国藏学事业承上启下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直到病逝的前一天,他还带病坚持给硕士生和博士生上完了毕生最后一堂课。他的这种精神风貌和对事业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虽然先生离开我们已有25年的时光,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长在。
王辅仁先生一生对中国藏学事业的振兴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今天重新追忆缅怀先生一生的藏学情怀,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在他身上那种严以律己、勤奋乐观、不计荣辱、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用他的风范和品德,激励和鼓舞我们在学术进步的道路上继续攀登。藏学事业是有传承性的,相信会有更多的后继者循着前辈们开拓出来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为藏学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创造出更辉煌的业绩。
(选自《中国藏学》2021年第1期,原标题《追忆王辅仁教授一生的藏学情怀》,注释、附录从略。作者索文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北京民族文化宫研究员)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