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森(1912—1991),汉族,河北安新人。现代著名藏学家、宗教学家、因明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职。
回忆王森先生
文 /邓锐龄
(选自《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
1950年,我在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部读书时就知道王森先生大名,先生在东方语文系任教,常常携着一件内装书籍的小包袱在红楼里走来走去,听说他教授梵文,精通佛学,虽然认识,却无缘谈话。1952年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先生分到中央民族学院(以下简称民族学院)研究部,我同年毕业,也服从分配到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因工作需要,想知道清初西藏第五辈达赖喇嘛与蒙古固始汗的关系等问题,一次就贸然到民族学院研究部去拜访请教,他和蔼地接待我并给予详细的解答。8年后,1960年,我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以下简称民研所)工作,先生也在这所,可以说欣然再遇,我印象里先生面貌神态自此一直没有显著变化,头发浓密,只是白了更多。
真正与王先生相识,是在1962年。当时民研所领导决定我参加藏族历史研究工作,可以说与先生在一个行当里了,这一组内还有李有义、柳陞祺两位前辈,而其他分组内老先生较少,或仅一位,所以藏族组在全所里是配备最完整的。三位先生从面容上看,年纪似相差无几,实际上先生最小。
约在1963年,在所谓三年困难之后,国民经济逐渐恢复,运动减少,民研所接受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要求提供有关西藏佛教史、西藏佛寺内部组织结构等资料的任务,其中王先生承担的一项完稿后,先生谦逊地名之为《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实则写成了一部有体系、有卓见的通史型的科学著作。
先生在领受任务后,就要求常凤玄兄和我听他口授,为之做笔录,每周一或二次,在民研所二楼东南隅先生的办公室内,在一长桌边,先生与我俩分据一隅,他缓慢地说出,显然章次段落文句都已是腹中底稿,我俩用当时市场供应的粗糙的绿格纸记下。我十分惊讶的是先生言语结构的逻辑极好。在需要回忆前文时,竟一字不差地从容道出,又感到他的记忆力极强。初次遇到,十分惊羡而自觉不可及。先生往往携带藏汉史籍来,随时复查,尤其注重史事的年代。他在罗列赫(G.N.Roerich)英译《青史》、吴燕绍《西藏史讲义》、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等书上,用工整的小楷批注几满。

在这样工作约达7个月多的期间,先生曾要我留心国际上名家如佐藤长、石泰安(R. A.Stein )等关于古代西藏的社会经济的观点,选择重要论文和章节译出供用,并把他自己写的《宗喀巴传论》、民族学院王尧兄译出的《萨迦世系•帕竹世系》和我译出的野上俊静、稻叶正就《元代帝师考》作为《十篇资料》附录。
这部书稿最早是内部铅印大字本,不公开发行,据民族学院教授王辅仁告诉我,他为了自己学习及教学用,曾手抄全书20多万字一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先生撰写前言并改书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前后用心学习,读过多遍。其中关于元代卫藏十三万户、明代卫藏地方内部情况及明室以安抚为主实施多封众建的方针、格鲁派的兴起及清代达赖喇嘛与固始汗系的关系等难题,先生融会史料,严密论证。全书超轶前人,实为创造之作。而文笔尤其雅洁流畅,显然可见寝馈于古典的功夫甚深。民族学院教授蒙古史专家贾敬颜对我说:“要问国际水平的作品哪里有?读这部书就是。”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藏史专家王忠也对我说:“《宗喀巴传论》写得极好,王先生将重要的史料都用了。”但是,若干年后,民研所学术委员会评定职称时,听说有位委员批评这书正文中不注出处,故不似学术著作。殊不知当时写作只备统战部用,故不采考据论文的形式,也毋须详注,且此书改名后已补上主要参考书目,若再加注,恐王先生力不能及了。从此流传说有常凤玄兄和我的写作在内,事实全部是王先生著作,我俩不能著一词,仅在他口述时,间或帮助他选择斟酌用词,补制藏传佛教各派高僧世系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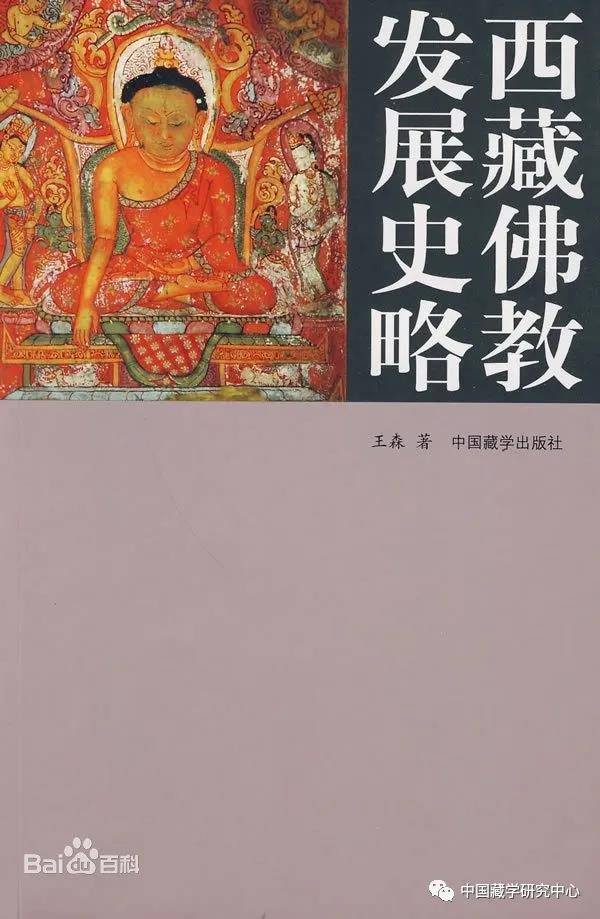
《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森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先生此时稍闲,即要我陪他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阅有关因明学书籍。我曾代他缮写致西藏工委办公厅一函,请协助了解各大寺现存梵文佛经并拟借阅梵文《因明入正理论》,又拟一电稿复西藏档案馆,请代抄录萨迦、哲蚌两寺所藏贝叶经目录并惠寄等。
从1963年起,到上世纪80年代,我常去民族学院宿舍大院王先生家谈工作,求指示。民族学院宿舍是由梁思成先生设计的,他住在一个小单元平房里,进门就是书房兼作客厅,桌上乱放着书籍、报纸和临写过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字纸,王先生就终年坐在极平常的一支椅子上伏案用功。那时很少人家能安设电话,我们都是贸然造访,先生回首见客人来,就立刻中断研究。谈工作之外,多话及学术。从这时才知道他专攻因明,用梵文、藏文、汉文互校佛经,但我于此学,迄今是外行无知,也就不懂得他于此嗜爱之深。他谈到《因明入正理论》《正理滴论》等,我只能勉强记住书名,完全不知其内容。一次向他请教读佛经的入门书,他指示应读《肇论》,我遵命展卷,仍觉义理艰深,未能读竟。他曾说玄奘译梵文为汉文极精确,藏族学者译梵为藏也信实,但在表达佛家义理方面不如玄奘。对汤用彤先生(1893—1964)、吕澂先生(1896-1989)在佛学上的造诣很推许,且说汤先生心如明镜一样,洞悉世事,只是不多说话。告诉我禅学当推马一浮先生(1883-1967)理会最深。说季羡林先生(1911-2009)应充分发挥其梵文的专长,减少旁骛。称誉周叔迦先生(1899-1970)在解放初出资救济生活无着的僧尼的善行。他在回忆北大旧事时,说汤用彤先生把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曾送给胡适先生(1891—1962),胡适竟一夜读竟并提出己见。胡先生在课堂上讲佛教史到禅宗时,有同学站起来批评说,您说了外行话。他用寥寥几件事就表达了当年北大洋溢着老师间、师生间探讨学问、尊重真理的校风。
他神态安详,说话缓慢,对求教者,有问必答。
如同其他老辈一样极少谈自己,记得他说过是河北安新人,曾离家出走,只身来北平(今北京),考入北大哲学系读书。与何其芳同班。汤用彤先生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曾做助手,遂遍读魏晋南北朝正史。又说年轻时好与人辩论,后来才戒掉。说体质荏弱,青年时曾患便血之疾。我虽去过他家多次,极少遇到来客,先生总是在读书。临写王羲之兰亭序似是唯一爱好。但自谦说,字写得乱。他没有其他业余娱乐。与人也不语生活上的事。言语也乏幽默,只有一次谈到熊十力先生(1885-1968),他莞尔一笑说:“取这名字也太我慢了(佛经讲佛具有十种智力。“慢”意为固执自我、傲慢自负)。”那时听重要的政治报告,都要记录,我在自己的记录上写“畏吾村民精校本(畏吾村为今魏公村旧名)”,观者说:“未必精校”,先生说:“这名字,我用,倒更合适。”
此后,1964—1965年我与常凤玄兄等下放山东黄县劳动兼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春返京。“文革”飓风袭来后都被迫接受审查。王先生历史无可议之处,言论无可指摘之处,亲友里无任何问题,对同事只是平淡之交。如此清白无疵,却因是老知识分子,也难免受严厉的诘责,如怀疑他在抗战期间参加过北平菩提学会,问为何这学会那时日伪未加封禁?又问他的人生观是什么?王先生说,这难回答。一个人一生有许多阶段,遭遇不同,思想也随时变化,对人生看法也是如此。至于菩提学会,他说明那是一个学术型松散组织,没有政治性质。“文革”中长时间大家集中住宿,起居集体化,斗争会不断,夜中我思考明天如何发言,往往难眠,或作呓语,先生夜夜酣睡。后来集体下到河南信阳县明港,他也随众前往。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学部更名为社会科学研究院,虽说此时大家已有时间可以从容研究,但研究所的重要图书,因战备需要,还寄存在外省。政治学习,机构整顿,公益劳动占用研究人员不少时间,而久已搁置的《藏族简史》《辞海》藏族史词条却要求恢复重写。1978年2月我再度回到藏族组,年底“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自此,院、所交下的工作纷至沓来。《藏族简史》的撰写工作要我参加。1980年王先生出任民族所民族史室主任。他多次主持藏族组会议,组织大家一起讨论《藏族简史》的写作提纲和《辞海》词条初稿,实际上就是连续开小规模学术会议。李有义先生会后评论说,借此温习旧知,启发思考,收益不少。而我作为初学者,有幸从这里听到先生对藏史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见解。后来先生有时把会场移到家里,让中央民族学院有关科系的同志也来讨论。我想,这是先生有意培养后进的实验,只不过不立名称,不事张扬罢了。
一次,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同志寄了一篇关于近代西藏史论文给社科院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刊物编辑转致民研所征求意见,王森先生就召集全组细致地研读讨论,命我将集体的意见归纳一文答复。后来听说该刊物主编等从此文看出这个不具名的集体,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曾打听该组成员有谁,并记下姓名。
先生曾对我说,我们科研部门应该先组织撰写百科全书,而后再写《辞海》,因后者可藉前者写得简练准确。这个意见,换个说法,就是写长篇易、写短篇难。《藏族简史》早从1958年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开始写作的,那在我到民族所之前,据说1958年一1959年时,先生就讲需广搜史料,加之以审核考据,然后动笔。对此,同仁里也有异议,听说与另一位先生在拉萨还出现争执。平心而论,作为科研的程序,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但也应立足现实,多考虑社会对各民族历史知识的渴望。况且简史如出版,其修订再版,甚至重写,也不是难事。总是要求完美,将会长期延宕,适与上级的剋期成书要求相左,不知何年能够完工。1975年《藏族简史》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内。“文革”结束后民研所领导要求我们在旧稿上重新编写。组里分配每人各应写的章节,其中李有义先生担任藏族的社会经济史部分,王先生承担中古(宋代)的藏族史部分,各有造诣,众望所归。关于中世纪青海藏族情况,我听王先生说他写出了《青唐录》会校本,关于中世纪西藏众教派的形成又有先生《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的著作在,应该不难。李先生初忙于译书,后忙于准备去美国讲学。王先生初慨然允诺,且召集大家每周开会一次研讨全书提纲,长达3个月,后来就是不屑执笔。我不能催促,也木知是何原因,十分为难。如先生要口述,命我如前那样笔录,我再忙也会竭力帮助。但先生不提出任何要求,终于不写。他遗留的封建割据局面与藏传佛教各派的兴起部分,由常凤玄写出;李先生原承担的经济史部分也由常凤玄与黄颢分别补足。可是先生对《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关于藏史的几条重要条文,却是亲自动笔,条条优质。此后,《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版印出后,主编谭其骧先生要求修订,西藏诸幅出于王忠先生之笔,王忠患重疾卧床,所收集的材料又难于搜求,就委托我延请王森先生和民族学院洛桑群觉、民族所常凤玄、黄颢、祝启源一起阅图,先生欣然许诺,会议在城东北隅和平里举行,先生不辞劳累从西郊前往,提出修订意见。因此我想,先生不肯为《藏族简史》落笔,或有其他原因。《藏族简史》迟至1985年才印出。
1983年后我又奉社科院之命,帮助翁独健先生筹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同时还兼民研所的工作,事务繁重。劳作三年,乏善可陈,原来的科研工作几乎搁置,因此请求调离社科院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庶几不忘旧业。
1987年4月我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先生5月患急性胃肠炎,休克4小时,不省人事,住入医院,因无床位,竟卧在过道中等候空床4天,我知道时,先生已病愈,我去民院宿舍看望,他仍然对初诞生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藏研中心)殷切地提出建设意见,说中心应该及时筹备资料,如搜集影印刊布古藏文抄本和梵文贝叶经;及时培养人才,他本人就愿意带学生整理梵汉藏三种文本《集量论》等,我后来向藏研总干事多杰才旦转达。藏研中心聘请他为兼任研究员,指导编辑藏研中心所藏西藏梵文贝叶经缩微胶卷目录,他自己还对法称著作进行过整理研究。
此后我一度应日本帝京大学邀请到那里教书,1991年春准备离开日本时,2月20日接到马大正同志一信告知王先生已逝世了,怅惘难名。从此无缘再见到先生,聆听教诲,成为毕生的遗憾。
王先生对我也说过,他自己不爱动笔。许多同事对他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只知道先生在《文史知识》某期上还发表过一篇解释玄奘西行图上的行装名称的文章,但他并非“徒然的笃学”,因为很愿意把所知尽量告诉别人,我虽没有听过他讲课,但认为他是以传播知识为自己的天职的。如先生与我谈明初藏史,偶然言及当时汉僧的文集可能流传到日本,这启发我在日本教课余暇,访问公文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等图书馆,搜寻史料,得以写出关于克新、宗泐二僧事迹的文章。前面说过先生如何诚心诚意培养后进,他带过唯一的研究生祝启源,后来果然成为藏史学者;他汲引人才,如想将黄明信、王尧等藏学家调来民族所,可惜未能如愿。
若干年前,读藏学大家伯戴克(L.Petech)悼念《卫藏道场胜迹志》的首译者费拉丽(Alfonsa Ferrari)女士的话,说:“她的严格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无情的自我批评习惯,也许是多产的阻碍,却保证了她愿意发表的几篇文章,无一不具备最高的学术水平。”我想起这适用于先生。
先生谢世后6年,1997年冬,我才读到张中行先生的散文名作《流年碎影》,其中《同学点滴》一篇内,也提到王森先生。说先生性格“沉静温厚”,在自己的友人里,讲学问,说得上“实在”两个字的,只有他一位。又说“他专精的都是凡人不懂也就不会用到的,肚子里装得很多而很少拿出来”。这让我想王先生高深的品节学问,终其一生,寂寞无闻,只有这一段,仅490字,或能藉此为世人所知,未免太遗憾了。但张中行先生文章开头就把王森先生与其大学同系同班的何其芳先生对比,说,王与何不同,王“不只早年,是直到盖棺论定,也没改行”,对我却是极大的启发。我才悟到王先生的特立独行。他从大学读书到离开尘寰一直坚持因明学的研究,只要一息尚存,就穷究不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干扰,经济生活的困窘,人际关系的紧张,自己的体弱多病,都未能丝毫动摇其志愿。他很少交游,不求闻达,安于寂寞,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的才学和业绩,连发表过及写过什么文章也不对人说,竭力维护一个略微安定的小环境,节约有限的时光,在一冷门学术上深造极诣,远绍清儒校勘考据的实学,承继五四以来科学研究的传统,以发扬中华的博大精深文化为己任。如此,就须“有不为而可有所为”。前面说的他未执笔写《藏族简史》有关章节,除体弱难于坚持又新加指导研究生任务外,或与他在这方面考虑有关。
回想我从1960年到民研所后同先生在一起的短暂时光,他与许多先生都对我这样一度以言语获罪,名载另册的后学,向无歧视,而当史学界广泛地流行关于民族的定义、汉族形成时代等理论问题的讨论时,蔚为时尚时,所内有人讽刺我年纪老大,“什么也写不出来”,王先生却说:“你们要给他时间,容许他逐步走上藏学研究的道路。”为我解释,希求谅解。这样蔼然仁者之言,任何人听到都会心存感激,何况我这样在追求学问一途上历经曲折的人。先生嘱咐我要学好藏文,但不要以为在藏文文献里有像《资治通鉴》这样的著作;在我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工程中,业余自修了德语,先生听了我自述,说,“要是继续学藏文就好了”。他还对我说“做学问贵在能有疑惑,发现问题,这就走上深造的途径,但于某领域内知识基础不广阔不牢固,也不能发现问题”。这些告诫在我这样移情杂学泛滥无归的人身上竟未多起作用,晚年才认识先生专一不舍的治学是我早应效法的楷模,然良时已逝,何可攀援,每想到这里,就觉得十分愧对先生。
2016年5月25日
【作者简介】邓锐龄,北京市人,满族,1925年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研究员。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